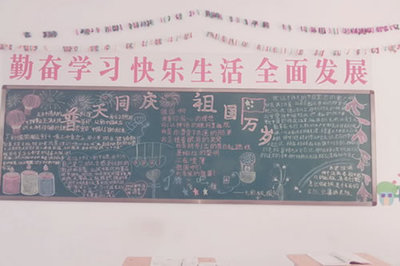不可一世的袁世凯第一次领教到“国会”的威力时,他的大总统头衔前面还加着“临时”两字。 1912年4月29日,北京宣武门西侧的象来街上人流如织。两年前清廷为“预备立宪”而成立的资政院里,将要迎来的是改天换地之后,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的开幕礼。 除了全国各地的75名议员,同时到来的还有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一个月前刚刚从孙中山手中接过权杖的袁世凯,一身戎装,腰间佩剑,志得意满地进入议会大厅。不曾料想,议长林森迎上前来,第一句话竟是:“袁大总统,参议院是立法的最高机关,是一块神圣之地,例行是不得携带武器进入的,请大总统阁下解除军刀入席,以崇法制。”惊愕了片刻的袁世凯回过神来,随即解下了佩剑。 《国会现场:1911-1928》一书写道,“这一幕被在场的人看在眼里,无不激动万分,以为一个民主法治的时代真正来临了。”在作者叶曙明看来,“国会”是破解民初政治迷雾的关键,“是各种政治矛盾聚焦之处”。而很久以来,即便在近年来的“民国热”中,除了少数一些学术著作,也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个“国家政治的缩影”。 的确,为人们所忽略的是,国会是民初政权建设的中心。从约法、政府,到孙中山、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无不是临时“国会”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或草拟批准的。当时的立宪派、革命派都梦想着建立一个类似美国这样的民主合众国,在此背景下,国会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一年后的1913年4月8日,在离资政院不远的原财政学堂里,礼炮齐鸣,军乐奏响,第一届国会( “民元国会” )正式成立。这次典礼的规模要大得多—参议员177人,众议员500人,而且,“今日国会诸议员,系由国民直接选举,即系国民直接委任,从此共和国之实体藉以表现,统治权之运用亦赖以圆满进行。” 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的美好和充满希望。但,梦的破灭,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权力很快就从笼子里出来,并且把笼子毁了。1914年1月,挫败孙中山“二次革命”的袁世凯,继驱逐国民党议员之后,干脆宣布解散国会。 “宪政之父”宋教仁之死 其实,中国坎坷的宪政之路,早在国会成立的一个月之前,就遭遇了一次巨大的挫折。1913年3月,被称为中国“宪政之父”的宋教仁在南京遇刺身亡。12年后病逝的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嘱为世人熟知。但曾经与孙共同创立同盟会的宋教仁,在离世之前给袁世凯的信里写的是,“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两种不同的遗言,革命与宪政,恰恰代表了这两位当年的同志,在以暴力革命推翻清廷之后的巨大分歧。 叶曙明说,宋教仁是革命党里的“异数”,他的理念是,民国成立,革命就结束了。不可能一边革命,一边共和。因为所谓共和,就是要实现民族和解、社会和解,全社会在宪政的基础上,得以分享权力。分享权力不是一个虚的口号,它要有实际的、可操作的方式,而宋教仁尝试的方式就是政党政治、代议政制。 宋教仁对政党政治的最大贡献,就是把同盟会从一个从事秘密暴力活动、带有会党色彩的革命团体,改造成一个公开参与国家政治的现代政党。他希望以国民党这个大党,主导国会,制约总统,把党派对立引导入正常的政党轮流执政轨道中。中国幸运之处在于,不仅诞生了一个宋教仁,还诞生了一个梁启超。两人所曾经代表的敌对两派—革命派与立宪派,在民国以后实现政治和解,建立起政党和平竞争机制,从而在中国民初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政党政治的实际标本,而不仅仅是理论的探索。

而孙文的选择是要继续革命。接受临时大总统一职时,同盟会还坚决抵制内阁制,主张总统制,但随着参议院改选袁世凯为总统,立即改弦易辙,要求实施内阁制。在宋教仁去世后,孙文立即指责袁世凯指使暗杀,并且说此事“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经理型领袖”宋教仁之死,“革命型领袖”孙文重返舞台,意味着许多弯路势必要走,许多事情又要从头再来。而在一些史家看来,“二次革命”是因宋案而起,但追根溯源,则是因孙文让位于袁世凯而起。 依旧热爱暗杀的同盟会 宋教仁并非与国会历史相关的暗杀案的第一个受害者。和宋案的扑朔迷离相比,刺杀福建参议员林长民未遂的凶手,当时就已被证实为同盟会“同志”。 1912年1月下旬,各省的参议员陆续抵达南京,组成国会正式成立之前的“代理参议院”。但林长民刚到南京,便险遭暗杀,好在刺客枪法欠佳,才有惊无险,避过一劫。刺客不是革命对象的“满清余孽”,而是革命者自己。中部同盟会湖北分会负责人居正承认,刺客“乃系福建同志”!而杀人理由十分直白—“以林(长民)素反对革命,今来投机,恐与吾党以不利,故欲除之。” 民初一系列的“暗杀案”,很多似乎都与国民党脱不了干系,包括1918年的“汤化龙案”。叶曙明指出,暗杀传统与同盟会的政治基因有关。同盟会在反清时代,基本上是一个秘密会党组织。由许多小的会党组织联合而成,它有自己的盟誓、暗号、门规,与一般会党没有太大分别,它主要争取的对象,也是会党分子。孙中山成立同盟会时,曾估计全国的秘密帮会中,大概有3500万会员会追随他的革命事业。革命时期,借助江湖的会党力量,无可厚非,但如果以他们为主力,会有许多的后遗症。这些后遗症,在辛亥革命之后,显现得十分清楚,中国迟迟不能进入真正的民主共和时代,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第一届国会成立之前,宋教仁努力推动同盟会政党化,就是想清除掉血液里的会党因子,为国民党通过国会竞选,成为执政党做准备。走议会道路,首先是要确立分享权力的观念,在这一点上,宋教仁与梁启超已达成了共识。但后来宋教仁被刺身亡。而二次革命后孙文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实际上是回到秘密会党的老路上去,秘密会党的性质决定了它的排他性,是没有分享权力的观念的。 暴力的“暗斗”始终未能让位于国会的“明争”。叶曙明在《国会现场》中写道,“宋教仁死的时候,中国离宪政还有十里路;到汤化龙死时,已是百里之遥了。” 革命党转型不成功,当然其领袖难脱干系。《国会现场》并非为孙中山“祛魅”的唯一一本书。在史学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除华人学界以外,全世界研究中国史或者是汉学界的学者认真研究孙中山的人并不太多。法国学者白吉尔的《孙逸仙》一方面告诉西方的史学家们,其实孙中山还是值得注意的,但另一方面也试图提醒中国的学界或者是传媒界不能“神化”孙文。 而史扶邻在《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中写道,“孙中山领导全国的能力,从未受到真正的检验。诚然,这无疑使他去世后更易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倘若他的寿命长些,他将发现,社会革命和现代化诸问题,不可能像他先前断言的那样容易解决。”而近来两岸中国人的研究也同样如此,李吉奎、俞辛醇、桑兵、杨天石等运用详细史料来还原一个更加全面的孙文。 代议制不适合民初的中国? 尽管从1913年到1928年,民初国会的命运多舛,但叶曙明认为,国会在民初政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议员们的选票一再改写中国历史”。他描写民初政治舞台上的议员、政客,试图再现这段历史,重温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这一幕,是如何从万众期待、精彩纷呈的戏剧高潮,最后跌入可惜、可恨、可悲、可怜、可笑的收场的。 1913年10月,民元国会在短短几个月内交出了一部“天坛宪法草案”。可惜生不逢时,因宋案发生,二次革命起,国会议员停止职务之令下,代议政制遭到致命一击,凶手不是“程度不足”的选民,而是政治舞台上的官僚政客。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恢复,重启制宪,但因部分条文内容各党派争持不下,扰攘经年,在督军团的粗暴干涉下,国会再度解散。而孙文则在广东发起护法战争,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其后国会时开时闭,忽而广东,忽而上海,忽而四川,忽而云南,颠沛流离,有时一个国会也没有,有时多至三个国会,其合法性早已荡然无存。而国会也沦为行政的附庸,其功能变成单一的制宪机关,除了议宪,几乎别无所务。 从1913年一直到1924年,十年有余,国会勉强制出一部宪法。这部宪法经过这么多年的深耕细耨,就内容而言,可以说是最接近完美的了。但却是出自一批收了曹锟支票的“贿选议员”之手,结果纸墨未干,又被推翻。国会也做了曹锟的殉葬品,“吾与汝偕亡”了。 叶曙明说,“只有了解这段历史,才明白中国宪政之难,难在哪里。不是民众程度太低,而是官僚程度太低;不是民众不想要宪政,而是官僚不想要宪政。” 在《民国初年的国会》一文中,台湾学者张玉法也颇为惋惜地说,“由于党争激烈,各党派太重党派利益,缺乏协调,使得法案的制定,多如牛步;另一方面,政府常争取舆论同情,多方对国会加以丑化,而为息事宁人,又对国会议员多方收买利用。在这种情形下,清末被视为神明的国会,到民初既有国会之后,竟成了是非的渊薮、罪恶的泉源,国人多不再对国会抱热望。” 被革命摧毁的“联省自治” 民初国会制宪的“血泪史”中,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上世纪20年代,在南北分裂、国会破碎、立宪无期的悲观空气笼罩下,国内一股“联省自治”的风潮平地而起。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后来被众多的大陆、港台史书定性为革命的“叛变者”—陈炯明。在叶曙明看来,陈炯明是除了宋教仁之外,革命党中的另外一大“异数”。他的失败,不过是和孙中山不同路线的失败。 自治是共和的基础,没有自治就没有共和。陈炯明的政治理想,是由“底层设计”,自下而上的,先实现村自治,然后是县自治、省自治,然后实现联省自治,循这样的途径,逐步夯实共和之基,最后全国在宪政基础之上实现统一。 宣统以后,对实现君宪,朝野已达成基本共识。但辛亥革命爆发,君主倒下,共识的基础一瞬间消失了。这个弯转得非常急,很多人茫然不知所措。整个北洋时代,都是中国人在寻求新共识的时代。经过十年的摸索,到上世纪20年代,新共识的雏形渐渐浮现了,那就是联省自治。翻看上世纪20年代初各地的报纸,不难得出这样的印象:联省自治不仅呼之欲出,简直已成不可抗拒的潮流了。 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中国的未来完全改变了。叶曙明说,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有一种强烈的焦虑心理,总想找出一剂良方,可以一次解决中国所有问题。当时在知识分子中,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十分盛行,他们是联省自治的有力支持者,当俄国革命爆发后,他们几乎集体转身,改为支持革命,至少是同情革命。失去了知识阶层的支持,是联省自治运动迅速式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会”和宪政梦的破灭,不啻为中国政斗的一个标准样本。这样的剧本,百年来反复上演。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