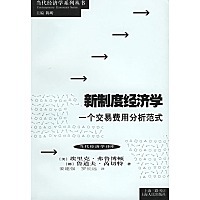--一般概念、功能或特征及其本质
叶行昆
一般地说,制度是构成统一整体的各个项目相互依存或相互影响的有机综合体;其特点是具有规则性、系统性或规律性。所有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思维的、人为的产物;它既可以是虚构的,也可以是真实的。例如,托马斯·莫尔(1478—1535)于1516年在其代表作《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中所提出的“乌托邦”思想,就是虚构的社会制度的概念,“乌托邦”是拉丁文(Latin)Utopia的音译,来源于希腊文(Greek),“乌”(ou)是“没有”(not),“托邦”(topos)是“地方”(place),“乌托邦”就是指一个“没有的地方”(nowhere),是一种空想和虚构,是不可能实现的;先秦儒家提出的“大同”、“小康”(《礼记·礼运》)思想亦是如此;然而,金融的或垄断的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则是真实的或现实的经济制度的概念。所有的制度,都有发生作用、发挥机能或运行的结构和方式(mode);它们可分为静态的和动态的。静态的制度是机械的或均衡的制度,而动态的制度则是进化过程或发展的综合。
新制度经济学(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认为,人类行为的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们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制度在塑造人类这种双重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因此,制度是为适应人类行为的要求而产生的。所谓“没有规矩则不成方圆”。从深层结构分析,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制度,都是当时人们的利益及其选择的结果。博弈论(Game Theory)就认为:制度是N人经过N次博弈的均衡解。舒尔茨“将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Schultz, Theodore W., “Institutions and the Rising Economic Value of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e Economics, 50—December 1968) 诺斯也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P.225) 制度是由三个基本因素组成,即被社会习惯和习俗(habits and customs)认可的非正式约束(Informal Constrains)、国家法律和法规(laws and regulations)所规定的正式约束(Formal Constrains)以及实施机制。此三者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制度的结构。
非正式约束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并构成历代相传的文化沉淀的一部分,它既是被社会所认可的行为规则和又是在组织机构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它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在非正式约束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而且,就降低提供其它制度安排的社会成本而言,意识形态又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或国家而言,意识形态有可能取得优势地位或以“指导思想”的思想的形式构成正式制度安排(或正式约束)的“理论基础”和最高准则。所以,它对于探讨一个国家的制度思想的形成与演变具有启发意义。这一点亦可以在我们进行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制度思想时得到验证。
正式约束是指人们有意识地创设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它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各种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一种等级结构;它可以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乃至个别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其中“政治规则并不是一定按照经济规则中的效率原则发展的,它会受到政治的、军事的、社会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等的各方面的约束。因此,完成有可能,一个民族长期地停留在低效率的经济制度中”。(诺斯语)这一观点有助于我们进行经济制度的比较研究。就人类历史的发展而言,正式约束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约束相互作用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
实施机制是制度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判断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不仅要看这个国家的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是否完善以外,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国家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完善;而检验一个国家的实施机制是否有效或是否具有强制性,主要看其违约成本的高低。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约束便形同虚设。实施机制的设定基于下列原因:
1)交换的复杂性;
2)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行为动机;
3)合作者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而容易导致对契约的偏离。所以,强制性的实施机制是任何契约能够实施或各种制度得以运行的基本前提;而制度实施机制的主体一般都是国家。国家是制度的最大供给者。然而,在古代社会中,国家如何行使其实施职能,它在制度安排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又是什么样的,这也是一个颇值探讨的问题。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虽然有无数次的争端或战争,但是,就经济生活而言,人们通过合作方式来解决争端或战争所达成的经济效率总是最大的。而制度起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设法解决个人理性(personal rationality)与集体理性(collective rationality)之间的冲突。因此,制度的最基本功能便是为人们实现相互之间的合作创造有效组织的运行条件,以求合作得以顺利进行,从而达到预期目标。广而言之,制度的功能又可细化为:
1)降低交易成本(科思语),
2)为经济提供服务(舒尔茨语),
3)规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4)提供激励机制,
5)有利于外部利益内部化,
6)6)抑制人的机会主义动机及其行为。(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P.61,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
正如弗雷徳里克·普赖尔所言:“确切地定义‘经济制度’的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财产和产业组织》,P.337,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的确,几乎每一本关于经济制度的著作,就有一种对于经济制度的定义。笔者无意标新立异,只取一种较为折衷的说法。“所谓经济制度(economic system),就是国家组织经济活动的各种制度的总和,其目的就是配置资源,以实现国家目标。”或者说,“一种经济制度就是在一个既定的地理区域内,有关制定和实施生产、收入与消费决策的一套机制和组织机构”。“广义地说,各种机制、组织形式和行为准则,凡有助于作出和实施关于稀缺资源配置决策的,都包括在经济制度内”。(Paul R. Gregory / Robert C. Stuart: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0; 葛奇 许强译,P.6,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它包括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果的所有机构、组织、法律和准则、惯例、信念、观点、价值标准、禁忌以及由此引路的行为方位”。(弗雷德里克·普赖尔:《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财产和产业组织》, P.337)无疑,国家是在经济制度中的起主导作用。简而言之,一种经济制度就是一个国家借助其来配置各种稀缺资源以实现各种目标的一套机制和组织机构(institutions)。或者说,“经济制度是各个参加者的组织发展的复合体,这些参加者是同分配稀缺资源以满足个人和集体需要有关的”。(Allan G. Gruchy: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Second Edition, b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徐节文等译:《比较经济制度》,P.1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此外,经济制度是“社会制度中许多次级制度之一,与其它次级制度有相互依存、配合、影响的关系”。(Vaclay Holesovsky: Economic Systems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P.27, 1977)“经济制度必须被视为历史演进的整个社会制度之综合的一部分”;“经济制度又必须被视为历史的范畴而为意识形态、惯例、传统、技术发展以及物质环境合并之结果”。(Horst K. Betz and E.K. Hunt: “The Methods of Comparative System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29, October 1970, No.4)
一般说来,形成经济制度的因素有以下若干:
1)人们的思想、欲望以及行为的历史文化渊源;
2)自然资源,包括气候、环境等;
3)人们所推崇的哲学思想;
4)人们过去及现在对于如何实现其所选择的理想与目标的理论的建立;
5)人们在追求其经济目标时所经历的尝试与错误。(William N. Louchs: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 7th ed., Chapter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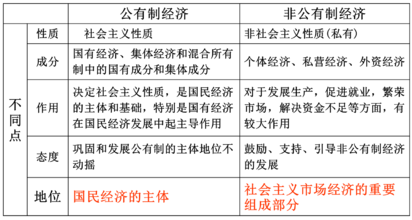
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环境条件下,形成一种经济制度显然不能不受其它社会或国家的影响,这种外来影响可分为二类:
1)主动地吸收引进,即以自身的现实条件为主而选择性地吸收引进相对先进国家制度的优点,(如唐朝时日本之求学于中国,近代中国向西方国家学习等—笔者注)有人称之为“引致性发展”(Derived Development)。
2)强制性接受,即可能被迫放弃其自身的条件而成为某一种制度之附庸,尽管其自身的条件仍然存在,但所起作用甚微,(如早期的殖民地国家,二战后的东欧国家等—笔者注)(Nathaniel Stone Prest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Power, P.31—35)
经济制度是多维的(multidimensional),其属性特征在于:
1)决策组织的形式;
2)提供信息和协调的机制:市场和计划;
3)财产权:支配和收入;
4)确定目标和促导人们行动(即激励)的机制。(Paul R. Gregory / Robert C. Stuart: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 Chapter 1, b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0)
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或人们经济目标的实现,并非受制于自然的或超自然的规律,而必须通过设置经济制度来予以解决。然而,经济制度的安排与变迁则必须通过国家的法律程序、权力机构颁布的命令,人们相互之间的契约协定,以及社会风俗习惯的认可等才能完成。所以,经济制度本质上是人为的、可变的,并且具有高度的适应性。
纵观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的发展史,影响经济制度本质的重要因素,是其历史和文化的状况。每个国家,都是历史和文化连续的统一体。这种连续的统一体,构成国家经济制度的总框架。而有助于确定国家经济制度本质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是其思想体系。所谓思想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观念、信仰以及价值标准的复合体;它引导个人和集体努力去适应自然和文化的环境。思想体系,在其性上可以是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也可以是宗教的。它为人们说理他们周围的世界、确定自己的目标提供框架,因而是人们行为的准则。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凡是为涉及制定一种经济制度的安排与变迁的思想,便能成为有关经济制度思想的研究范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