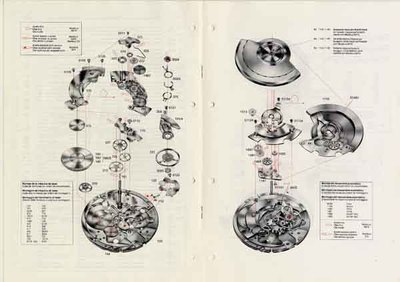经济学家们正陶醉于“显学”的荣耀时,一股“妖魔化主流经济学”的阴风骤然吹起并渐呈席卷之势,经济学界顿感风雨飘摇。面对公众对经济学家的道德拷问,我想起了配第和萨伊。

威廉.配第是经济思想史上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思想家之一。出生于贫穷的裁缝之家的配第仅上了两年小学就不得不外出打工谋生。凭借卓越的天资和顽强的毅力,通过艰苦的自学,成为医学博士、解剖学教授、音乐学教授、历史学教授和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经济学家。配第最重要的历史影响来自其对经济学方法的贡献。配第提出的“政治算术”实际上是数学和统计方法、实证主义方法、归纳法和科学抽象法的结合。通过与亚里士多德“不生产”的“三段论法”的决裂,配第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奠定了方法论基础[1]。务实的配第还将经济学研究扩展到众多领域,其研究涉及价值、价格、货币、工资、利息、地租及经济增长等方面,确定了经济学初步的研究领域;而且,配第的劳动价值论还成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最初来源之一。对配第的卓越贡献,马克思给予了慷慨的赞美,称配第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2]和“最有天才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家”[3],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4]。
配第不仅仅是一个学者,甚至,配第首先不是一个学者。“配第是个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人——他是内科医生、外科医生、数学家、理论工程师、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商人——他是那种精力充沛、几乎任何事都能成功、甚至能转败为胜的人。”[5]配第医术高明(据说配第曾经救活一位因谋杀亲子而被判绞刑的妇女,并写了《一个生者对死者的访问》自我吹嘘),并借此结交上层人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拥护革命,并担任英国驻爱尔兰侵略军总司令克伦威尔的侍从医生。后来被任命为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负责分配英军在当地掠夺的土地。配第利用获得的报酬进行土地投机,短短几年内成为拥有5万英亩土地的大地主。配第在政治上也颇有建树,165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660年,封建王朝(查理二世)复辟,配第由于曾经依附克伦威尔并发财致富遭到政敌攻击。为了保住其财产和地位,配第公开效忠复辟王朝(配第在爱尔兰期间就结识了查理二世),并被授予骑士称号(配第死前他的夫人被授予终身女贵族称号,他的后代曾经担任英国首相)。配第在政治上的无原则遭到了马克思的批判,“配第是个轻浮的、掠夺成性的、毫无气节的冒险家”,[6]他“既能在克伦威尔的盾的保护下掠夺爱尔兰,又能为这种掠夺向查理二世跪求必要的男爵称号”[7] 。不过,配第的行为与其“经济学的非道德化”主张倒是一致的。“配第方法的另一个要素是他试图把道德同科学分开。按照配第的看法,科学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处理道德问题,它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得到仅仅在人类应用科学进行选择时才会出现。”[8]
同生前风光无限,死后也无限风光的“轻浮”的配第相比,萨伊不仅生前也命运多舛,死后也倍遭冷漠。
最初接触的萨伊,总是与“庸俗经济学”联系在一起。萨伊是斯密经济学在欧洲大陆最早的系统的传播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说法,斯密研究方法的二重性决定其思想中科学与庸俗的并存。在传播斯密思想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萨伊舍弃了斯密思想中的科学成分而将其庸俗成分系统化,因而成为第一位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于是,萨伊的名字总是与“辩护”、“平庸”、“浅薄”等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得到的认识。在系统学习经济思想成长的历史时,我重新认识了萨伊。
萨伊早年从事商业活动。在英国接受商业训练期间阅读了斯密的《国富论》并成为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坚定的信仰者和传播者。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萨伊参加了革命。但是,但雅各宾上台后,其不宽容的极端政策与萨伊的自由信念发生冲突,萨伊第一次离开政治舞台,进入学术领域,担任《哲学、文艺和政治旬刊》主编。拿破仑执政期间,萨伊在《旬刊》上发表的经济论文得到拿破仑的赏识。萨伊再次进入政界,被委任到财政委员会工作。实际上,拿破仑并不接受萨伊的自由主义主张,而萨伊也不愿意放弃他对拿破仑保护关税政策的持续批判。1803年,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出版前,拿破仑要求他修改关于关税政策的某些章节,萨伊拒绝了。于是,在《概论》出版的同时,萨伊被解职。拿破仑知道如何惩处一个不驯服的学者。他查封了萨伊的一切著作,禁止萨伊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并委派他担任海关税收征管员。倔犟的萨伊并没有屈服,他又回到商界,去经营纺织厂。正是萨伊的不屈从,才保证了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欧洲大陆的传播。如果考虑到斯密原著的晦涩和结构的凌乱,萨伊的贡献其实是世界性和历史性的。
至少在现代微观经济学中,萨伊是除马歇尔以外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萨伊是斯密思想在欧洲大陆最早的系统阐释者,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欧洲大陆的最早的传播者;萨伊最早明确界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独立的学科地位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萨伊系统阐述的效用价值论不仅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重要来源,而且是现代微观经济学价格理论的重要基础;萨伊对“生产”的界定拓展了以“财富生产”为对象的古典经济学的认识领域,其“生产三要素理论”成为现代经济学“生产理论”的核心;萨伊对企业家职能、素质及收入性质的界定是企业家理论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并成为现代企业家理论的重要源头;萨伊的“三位一体”分配理论不仅是收入分配理论的较早的系统阐述,而且成为现代经济学分配理论的重要构成内容;“供给自动传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不仅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信念,而且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兴起的供给学派的几乎唯一的理论基础;……带给现代经济学这一切的,实际上是萨伊的独立的人格和学品。
但这位对现代经济学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萨伊,不仅被马克思斥为“庸俗”,被李斯特鄙为“无知”,被熊彼特讥为“浅薄”,就是在主流的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也很少得到正视。经济思想史著作家们在评述历史上经济学家的贡献时,对萨伊的吝啬表现出罕见的一致。在埃德蒙.惠特克近500页的《经济思想流派》[9]中,介绍萨伊生平和思想仅用了2页;斯坦利.L.布鲁的《经济思想史》[10]中,对主要是政治哲学家的边沁的介绍用了5页,而留给萨伊的也仅仅2页;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的《经济思想的成长》[11]相对慷慨一些,给了萨伊7页,但给马尔萨斯的是17页,给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是25页; 最吝啬的莫过于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和罗伯特.F.赫伯特,在其洋洋500多页的经济思想史巨著《经济理论和方法史》[12]中,居然没有对伟大的萨伊进行专题介绍。
我无法理解思想史对萨伊的几乎一致的冷漠。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萨伊作为学者的独立性的崇敬。
我们经常会感慨,学者的腰很难是硬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说明了陶潜公那种文人的铮铮铁骨的稀罕。经济独立是学术独立的前提。对于一个学者而言,由于作为其生存基础的学术活动不具有直接的生产性,服务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成为其生命个体及学术生存的无奈前提。当然,我们不否认目的和手段对正义性诉求的差异。我们允许并愿意接受“正义的目的”和“非正义的手段”的并存,我们不需要为手段和目的的道德冲突而内疚。在学说史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无奈和屈从。当然,像配第那样的极端并不多见。具有独立禀性的学者往往选择沉默、孤独。但是,只要我们还对一个道德的理想的世界怀有希望,我们就会期待一种精神楷模。在萨伊身上,我们首先看到的不是学术,而是学术精神,是学者作为独立的人的道德境界。
[1] 熊彼特称配第的“政治算术”为“鼓舞人心的启示”,“富有启发性的纲领”。——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一),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P319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P255
[3] 同上书,P257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P302
[5]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一),商务印书馆,1996,P317注①
[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P44
[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P37
[8] 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和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57
[9] 【英】埃德蒙.惠特克:《经济思想流派》,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10] 【美】斯坦利.L.布鲁:《经济思想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11] 【美】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 【美】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和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