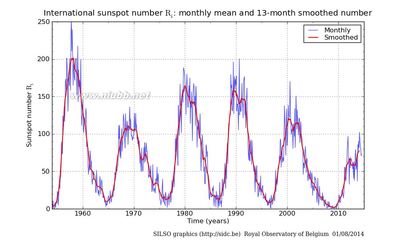达尔文进化论在解释社会进化和人类行为时所面临的挑战,需要我们重新回顾华莱士与达尔文之间关于人类进化的“独立证明”分歧。人们都知道华莱士是进化论的独立发现者,他的自然选择理论框架曾经加速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但一直存在这样的争论,即华莱士的原创性是否一向被低估了。事实上,当我们对制度演化的讨论涉及到关于意识参与和人脑进化的问题时,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适用原则”与“华莱士的独立证明”观点的讨论就是不可避免的。从经典的进化论在解释人类进化和社会进化问题时面临的尴尬起点开始,达尔文和华莱士的分歧正是这一困难的最初反映。
其实,华莱士和达尔文都敏锐的感觉到了人类智慧的特定结构和精密程度是有别于其他生物的,但自然选择似乎难以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他们都试图通过各自的方法识别出这一奇特的进化现实,但似乎都没有成功。尽管华莱士的努力似乎更为大胆,他试图对人类进化的事实给出一个“独立于自然选择的证明[1]”,但最终还是陷入了窘迫的境地。其主要的困难是:早熟和过渡发达的认知技能看似对史前人类的生存需求相关,但需要说明的是,在进化的各个阶段中人类智力的这种更为高级的能力有何用处呢?关于这一问题,达尔文和华莱士都没有找到既合理而又符合自然选择的解释,包括华莱士“独立证明”思想所提供的也只是一种处于酝酿中的、似是而非的答案。其实除了关于人脑进化的悖论之外,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在很多人类进化的事实面前都缺乏说服力。哈伊姆·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中列举了以下事实:例如,火的驯化、石器时代的工具制造及原料运输、人体器官功能的结构分化与灵长目动物的差异、化石记载的艺术创造、商业贸易、耕作行为以及人对动植物的驯化等等(第3-6页)。
显然,达尔文在论证从动物到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连续性时所遭遇的困难直接与人类的智力相关,这显然是个费时费力的领域。对于达尔文来说,事实上也是对任何想要从进化的观点理解人类的人来说,核心的、困难的任务就在于解释人类迥异于其他生物的、高度发达的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具体来说,人的抽象能力、语言能力、社会性、道德性、甚至包括人类活动中的宗教性和精神性活动,这些如何解释,如果这些禀赋不是来自于上帝,那么来自何处呢?但达尔文坚持认为,人是一种自然物种,人类的许多素质都可以在其他生物的进化中得到辨认,但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差别只是程度的差别,并不存在种类上本质差别。华莱士指出,“要证明从动物到人类的理智和道德能力的连续性和进步性发展,不同于证明那些凭借自然选择发展起来的能力,尽管证明这一问题是坚持达尔文进化论的最根本问题,但达尔文对此显然没有做出任何努力(1889, 463)。”[2]华莱士认为,如果人脑及其派生出的精神产生于自然选择,那么它们应该在史前物种成员的平均水平上,而且还意味着应当仍然存在于现存的人类社会和人种之中。华莱士将人类的精神功能的应用归咎于,对它有直接影响作用的外部社会环境变化所提供的工具性激励。华莱士在1908年的《自传》中指出,关于自然选择这一伟大原则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他和达尔文观点的差别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分歧。适用原则作为自然选择理论的基石说明,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既不会产生有害于有机体的结构,也不会产生比生物进化需要更高级的结构。相反,自然选择不容纳设计和预见。但华莱士同时指出,自然选择是否适用于人类是个可疑的问题。人类历史是不能简单用自然选择来解释的。华莱士将人类精神的进化归类到“自然选择之外的某种因素,类似于首先产生有机生命的东西”,后者带有道德和理智的性质,而不单是生理形式。简言之,华莱士只是意识到了自然选择理论的缺陷在于:如何解释“该理论是怎样在文明存在之前就为文明准备智力的”这一根本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华莱士只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而没有有效解决它。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他既竭力维护自然选择理论,却又愿意部分的把人类进化排除在自然选择之外。
显然,华莱士提出的“独立证明”问题,与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解释难题重合在一起了。比较斯密和达尔文,我们发现斯密似乎错过了进化的清晰概念,而华莱士则错过了人脑进化起源的考察。我们的结论是:华莱士“独立证明”的真正含义不是对自然选择理论的偏离,而是试图指出人类智力的进化受制于典型的表型可塑性。而这种表型可塑性确实在人类精神和职业功能的较广范围内存在,而自然选择理论实际上隐含了而不是否定了这种进化事实。
不管怎样,只要我们将人类的认知进化问题独立于自然选择来进行分析,那么意识和思维的作用功能就必须得到承认和讨论。这将使得人类进化和社会进化的过程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无意识演化”,而还原到现实的“有意识演化”过程。

[1] 华莱士在1889年的著作中,根据对一所公立学校的教师和学生音乐才能的调查发现:人类的天资似乎远远超过自然选择控制的范围。他对此的解释是,这些发现提供了对人类进化进行独立的确认,支持了他在人类智慧方面的有争议的立场,即根据自然选择的法则,人类的这种智能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他把这一发现称为“独立的证明”(P469-472)。
[2] 转引自: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