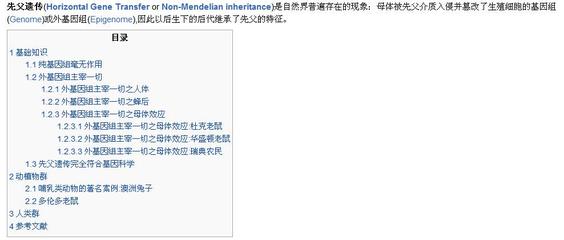本文所使用的“制度演化分析”一词,如同我在引言中声明的那样,它不特指经济学在制度分析领域相对于其他学科的方法论(主要是指演化博弈论)优势;也不倾向于在纯粹“自然选择”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视角下,将社会制度型构的过程视为“无意识演化”的结果。相反,它主张从“演化”这一独特的(而又传统的)视角,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探讨制度型构“在自然选择之外”的动力学因素。因此,制度演化分析在范式上面临第二种转向,即从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无意识演化”转向基于华莱士独立证明的“有意识演化”。
为了区别演化的“看不见的手”的解释和理性设计的制度起源解释,希尔思(1992,43-44)同时给出了“有预期设计过程”的规范描述。他认为,我们可以规定:
规定R是一组行为[X1……Xn](完全)有预期的结果,当且仅当每个行为人[A1……An]有意使他的行为[X1……Xn]产生(或帮助产生)R。并非每个行为人[A1……An] 都有意使其行为[X1……Xn]产生出R(或以R实际出现的方式有意产生出R)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判断R是否是有意为之,在多数情况下还是个程度问题。[1]
尽管纯粹演化的制度观念为制度起源提供了一个比理性设计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自人类进入政府组织的社会状态以来,政府作为一个行动主体参与制度发展与管理的事实同样不容忽视。因此,一旦我们认可社会主体“自我意识”独立于其他物种而存在,那么社会主体有意识参与各种社会过程的现象就需要我们提供一种“有意识行为”的解释。这需要我们在制度演化分析的范式上实现第二个转换:即从“无意识演化”转向“有意识演化”。

2.2.1基于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制度演化分析:无意识演化
进化论最初由拉马克(Lamarck)提出,达尔文为之奠定了科学基础。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和生物进化论的奠基者达尔文,在其巨著《物种起源》中提出了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学说。该学说的要点是群体中的个体具有性状差异,这些个体对其所处的环境具有不同的适应性;由于空间和食物有限,个体间存在生存竞争,结果,具有有利性状的个体得以生存并通过繁殖传递给后代,具有不利性状的个体会逐渐被淘汰(达尔文把自然界这种留优汰劣的过程称为“自然选择”);由于自然选择的长期作用,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同一物种就可能出现性状分歧和导致新物种的形成。他认为现存的生物都是进化而来的,它们有着共同的祖先。进化的方向是:生物种类和数量由少到多,生物的结构和功能由简单到复杂。
达尔文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从其他学科的学术思想中吸取养料,经过多年辛勤的探索和紧张的思考,最终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以此来解释生物进化的事实。自然选择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和谐统一的内容:(1)生存斗争的理论。生殖过剩与生存条件的有限这一矛盾是地球上的物种被淘汰的外在原因之一。(2)遗传性发生变异的理论。虽然变异的机制并不清楚,但普遍发生变异的事实不容否认,达尔文以此说明物种演变的内在原因。(3)适者生存的理论。生存条件一直在变化,如果物种的变异适合于变化的环境,那么就在生存斗争中取得胜利而发展;如果物种的变异不适宜于它当时生存的条件,那么就趋于衰减或灭亡。这样,达尔文基于自然界本身的事实和矛盾,为我们大致描绘了生物进化的机制,各种关键的问题在他这里都有了比较合理的、有事实佐证的回答。达尔文的进化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论”“物种不变论”的传统观念[2],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套渐进式(Gradualism)的演化理论,即自然选择必须靠极度微小并对生物有利的遗传改变,长期不断地累积才能发挥作用。在达尔文看来,每次的遗传改变必须是极其微小甚至是不能觉察的改变,经过漫长的自然选择,动植物才渐渐进化出新种来。因此,高等动物是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生物界全体的关系好比是一棵大树,同出一源,低等的生物好比树根,高等的种类好比树枝,如此这般,进化是连续不断的,渐渐改进的。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的生物学规律影响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在内。人类作为一个独特的物种同其他生物有机体一样,在资源有限这一情形下的数量增长都将导致生存竞争。某些生理和心理特征使个体在生存竞争中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这些特征被选择出来,通过时间在代际间遗传下去,并在适当的时候导致新物种的出现或另一些物种的消亡。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在应用于人类社会时并没有像在生物界那样被广为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由于将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选择原理应用于遭遇了尴尬的难题。他们将人类社会组织视为人类有机体,它像其他自然有机体一样,也经历着发展变化。而这种变化如同自然界的有机体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样,社会也会在一种“功能性适应”的类遗传机制下逐渐分化为彼此独立却紧密联系、依赖的部分。然而在整个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如同自然选择一样,有一种超机体的力量适用于社会。显然,在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的融合中,社会达尔文主义狭隘的接受了达尔文进化理论中关于“基因遗传”是获取能力的唯一来源的观点,但它却忽视了特定社会中权利结构对于能力分布的影响,也忽视了社会主体在生存竞争的过程中习得的能力,以及由某种共生的合作产生的能力提升。
概括而言,社会达尔文主义采用了一种“加尔文式的进化观”。在解释社会进化问题时,他们简单的认为,人类和其他物种是无差别的有机体,他们在使用自然与社会进化的类比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二分法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即他们将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单纯的视为一个“无意识演化的过程”。无意识演化过程中的社会主体,就如同达尔文进化论中的自然有机体一样,只是外部环境变化的被动受体,社会主体竞争在原初形态上类似生物的生存竞争,即任何种群数量的变化导致的竞争都是通过繁殖竞争在漫长的遗传过程中实现的。达尔文认为,有机体器官的微小变化将会通过繁殖而扩大,并经由遗传变异导致新物种的产生和不适物种的淘汰。此外,达尔文还认为有机体生理变异在较小程度上是外部环境变化以及器官使用的“用进废退”造成的。显然,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继承了达尔文使用“基因遗传”来解释进化的一元论调。显然,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解释社会进化时,像他们的导师那样,排除了遗传之外的互动学习、独立思维与交流沟通、以及主动对环境变化做出反映等后天因素。此外,就资源的稀缺问题而言,它也不单是自然作用的结果,资源丰度的变化同样会表现为社会关系(如权力结构、政治体制以及制度架构)的产物。因此,脱离社会主体间性和社会关系而单独求助于遗传机制,来讨论社会进化是明显具有局限性和误导性的。
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类似,现代经济学关于社会秩序进化的早期观点也带有同样的缺陷。如同达尔文进化论拒绝物种选择和群体选择,只承认个体选择一样,经济学中的主体选择单位也是个人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早期经济演化思想基于个体选择的选择论,在解释市场过程中非效率的个人行为和企业组织方式的淘汰方面很有解释力,但遗憾的是,这一思想在解释以下三个问题时实在缺乏说服力:(1)个人在物种间竞争的意义上是不可分割的单位;(2)个体选择必须立足有物种、群体以及共同体的层次上;(3)即使承认个体选择赖以发挥作用的物质立足于单个有机体的事实,自然选择论也无法解释社会主体的认知进化以及创造性思维的事实。
达尔文进化论在经济学中有两个重要代表:一是主流经济学家在捍卫边际主义方法时提出的“市场选择论”;二是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的“经济演化理论”。根据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市场中独立决策的企业和个人都是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行为主体目标函数的最大化被描述为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状态。但反边际主义者根据经验观察发现,现实中的个人和企业并没有严格遵守边际分析所给定的购买或生产策略,边际主义所提供的理论在实际中既没有被采用,也不具有适用性。确切的说,每个企业主和个人都并不知道单位商品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因此,他们认为边际分析的最优化教条是带有误导性的(Hall and Hitch, 1939,113)。针对反边际主义者的批评,早期的主流经济学家马克鲁普指出,惯例性行为并不会使边际分析失效,相反,二者是可以调和的(Machlup, 1946, 524-525)。他说,“就某种行为而言,从一个代理人角度观察可能认为是惯例性的或者是由规则支配的,但从一个理论家的观点分析,可能就是最大化的行为。”[3]根据马克鲁普的观点,边际分析的目的并不是要对企业和个人的行为给出一个详细的预测,相反,它倾向于解释企业或个人行为的趋势。在马克鲁普之后,阿尔奇安、贝克尔和弗里德曼提出了“市场选择论”来捍卫新古典的行为假设。他们试图证明,即使新古典理论关于最大化的假设是错误的,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也会保证新古典的行为理论定理得以成立。阿尔奇安通过建立一个赛车手随机选择路线的“机会主导模型”[4]解释了市场力量的“选择过程”。该模型假定,行为不是深思熟虑或是有意识的,而是由外部环境随机给定的,模型的结果发现:当环境变化时,没有人能使自己适应新的情况,行为主体变成了纯粹的接受者。因此,被环境所接受的幸存者,其行为就被证明是“适当的”。显然,阿尔奇安的选择论基本上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个复制品,他所谓的“市场竞争的选择”变成了对商业过程中稀缺的正利润的筛选。因此,在他看来,在竞争性市场中,选择的是已经实现的正利润,而不是预期的最大利润。无论市场主体是否以正利润作为行为目标,市场竞争的生存原则本身也会将“适应”市场的行为和利润方式选择出来。类似的结论,在弗里德曼的“台球手”案例中得到了重复。不同的是,弗里德曼认为,最大化假设对于单个企业的行为不适用,而更适合于解释产业趋势。(Friedman, 1953, 14-23)简言之,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给出的选择论而言,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1)有一个类似自然选择的力量在发挥作用(看不见的手);(2)预期收益最大的假设预测了这一过程的结果;(3)市场“主体的内在动机”(最大化倾向),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力量;甚至即使市场主体的动机毫无作用,但是(4)真正起作用的力量是,当市场主体不能最大化其目标时,市场中存在一种能自动纠正这一非效率行为的“外部力量”。显然,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选择论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解释,这使得他们的“终极主张”似乎成了这样:即无论市场主体是否致力于收益最大化,市场经济的“自然选择”过程将确保整体层次上关于趋势的新古典定理得以成立。
同样,在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中,他们对于市场选择的过程给予了一个更加接近“达尔文进化过程”的描述。弗罗门认为,纳尔逊和温特的理论更应当被看作是对阿尔奇安和弗里德曼选择论的一个引申和扩展。[5]在演化理论中,纳尔逊和温特将研究重点从“自然选择”过程转向了演化观的基石的惯例性企业行为(Routine firm behaviour)的考察。在他们看来,真正演化的是企业内部的惯例,而不是组织形式。惯例在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中所发挥的作用,被认为与生物进化中基因所发挥的作用是相似的。即他们在解释企业行为演化时将惯例视为基因的“类比物”。他们认为企业内部惯例性行为的一个主要功能在于,把组织内潜在的和明显的冲突保持在可预测的限度之内。此外,惯例还有助于组织内部特定操作性知识的存储。纳尔逊和温特还指出,惯例作为企业知识的存储方式,它无法还原为个体的记忆和认知的加总,它是一种企业内部成员共同分享的信息系统。因此,惯例在企业演进中成为稳定的、不可替代的遗传物质。市场对现存企业的“惯例的复制”是选择性的,而“企业惯例的变异”则是由市场竞争的失败所引起的。显然,企业惯例也由此变成了一个自发演化过程的结果,它并不取决于企业动机和意识倾向上的最优化方向,而只是取决于对外部市场环境的适应。
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都可以认为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与达尔文进化论十分相似,但所不同的是,达尔文进化论是个严格的无意识演进过程。而纳尔逊和温特则声称他们的演化理论是“不加掩饰的拉马克式[6]的”,因为“它既考虑了获得性特性的遗传,也考虑了在逆境的刺激下变异的适时出现” (Nelson and Winter, 1982, 11)。但遗憾的是,我们在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中,似乎无法找到理性和意识的恰当位置。首先,在承认市场竞争是个选择过程时,我们就无法界定何种行为是“最优的”,而只能从结果上说明何种行为是“最适合的”。其次,一个依赖于市场选择的结果,与新古典理论的理性最优决策结果并不会对应。显然,纳尔逊和温特所面临的困难在于,即使将企业视为市场环境的一个受体这一假设,扩大为企业彼此在行为决策上的相互影响也是环境的构成部分,那么在深思熟虑的行为选择与惯例性行为的选择之间也仍然存在一个优劣的权衡问题,更为麻烦的是,权衡的标准到底是“最优效率”还是“最佳适应”似乎很难明确。纳尔逊和温特在演化理论中所提出的“组织遗传学”问题,将我们对制度的演化分析引入了意识是否参与的问题?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无意识演化过程在解释社会进化时面临的尴尬,需要我们对无意识演化过程的缺陷和逻辑有个基本的概念。理性逊er, 1982, 11haviour13
现代心理学关于人类意识形成的研究告诉我们:首先,无意识的演化是机械的、自然的。它自动发生。其次.无意识的演化是集体性的,可是演化一旦变成了有意识的,它就会变成个体的。当演化还是无意识的时候,它是一个机械过程;它没有不确定性。事物按照因果的法则发生。有在是机械的、确定的。但有了意识,不确定性就出现了。通过这种类型的演化.意识逐步发展起来。但是,意识一出现,无意识的演化就停止了,因为无意识演化的目的已经实现了。无意识演化的需要只到意识出现为止。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已经超越了自然。在社会进化中,没有任何集体的、机械的演化会越过人类继续进行.从现在开始,演化已经成为一种个体的进程。意识创造个体、在意识演化以前没有个体。只有种类存在,没有个体。
鉴于无意识演化在解释人类和社会进化过程时所面临的困境,我们有必要将制度演化分析进一步推进到“有意识演化”的层面来探讨这一过程。
[1] Heath Eugene. 1992.Rules, Function, and the Invisible Hand: An Interpretation of Hayek’s Social Theory.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2 (March):28-45。
[2] 进化思想在科学家头脑中的萌发,以及进化论在科学界的确立以及在大众中的传播,都密切地与神学世界观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进化论的发展史,用达尔文的一句诙谐的说法,就是“魔鬼的圣经”代替“基督的圣经”的斗争史。到18世纪,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力学已经从神学统治中解放出来,但是生物学仍然禁锢在神学之中。神学世界观在生物学中具体表现为物种特创论和物种不变论。这两种观点主张:上帝是创造主,一切生物均为上帝所创造,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从造物主那里获得永恒不变的构造与功能,包括生活习性。显然,所谓物种特创论与物种不变论实质上就是搬到自然科学中的基督圣经。当时的生物科学只能是对圣经的注释,是地道的“神学的婢女”。
[3] 参:杰克·J·弗罗门,《经济演化: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4] 参:阿尔奇安,1950年,第214-215页,关于旅行者随机选择路线的模型。
[5] 同注释58,第85页。
[6] 对适应性进化的解释主要有两种,分别基于拉马克学说和达尔文学说。前者认为后天获得的适应性可以遗传,这就是说获得性适应可以改变个体的生殖遗传基因;后者认为获得性适应不能改变个体的生殖遗传基因,但它在一个群体中具有遗传优势,不适应或适应较差的个体特征由于生存能力和遗传上的劣势而在后代中逐步退化或消失。我们可以看出拉马克主义的解释是很直观的,但却要在遗传基因水平上的获得证据。而达尔文主义对物种适应性进化的解释似乎是针对群体中个体之间作用的结果,似乎所有适应性进化都可归结到自然(性)选择之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