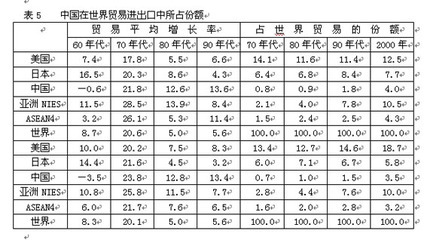韩非子被后人公认为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但其出师于一代大儒—荀子之门,此因应作何解?对此,萨孟武先生认为:“荀况主张礼仪,而尤强调‘礼’字。古人之所谓‘礼’,‘法’常包括在内。” (萨孟武著:《中国社会政治史》(一),P.46,三民书局印行)儒家创始人孔子也曾对制度设置与制度环境的重要性有所表述:“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而荀况则云:“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法,礼之大枢要”。(《荀子·王制》)“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荀子·君道》)又云:“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大略》)“礼、法”二者在制度功能方面,均具有外在性与与强制性。
《荀子·礼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可见,荀子已把孔子所谓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的道德内省思想进行了改造,强化了“礼”的经济功能,从而把人对于“物”与“欲”之间的冲突与张力,用制度规范来予以调节。还有,荀子提出的“礼制”思想,既有价值理性的价值,也有工具理性。作为工具理性,“礼制”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控制人的自然性情的自然发展和过度膨胀,把它们引导到一个正当和合理的限度内,使之适度和有节制。
韩非师从荀况,在这方面,韩非又与荀子性恶的思想相衔接。荀子认为人性恶,主张以礼义节制人性,但荀子的认为人性恶,并不是要因为人性的恶而否定人性,而是要用人性的恶来建立以礼义节制人性的前提条件。因为人性恶,所以要设礼义以节制人性;既已以礼义节制了人性,人性就不再是恶的,被否定的,而是可以任其发展,也应该任其发展的了。正因为有了以礼义节制人性的环节,所以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恶,但是又强调尽天下之美,致天下之用,"序四时,载万物,兼利天下"(《荀子·王制》),在礼义的前提条件下尽可能满足人性。荀子认为所以要有礼义,原因之一是要配应天道,原因之二就是为了调节人性。"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荀子·荣辱》),把礼义和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与物质产品的社会分配联系起来。后来韩非"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故民争"(《韩子·五蠹》)的思想与荀子的这一思想,如出一人。荀子说:"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荀子·礼论》)实际上都是有条件地肯定了财富利欲的合理性。
韩非受荀子的影响,也主张人性恶,认为人性好利恶害而自为,同时也承认荀子对人性的认可。但韩非否定以“礼”节制人性,主张用“法”取代“礼”。韩非认为,人性之恶是自然既成的,所以现实政治政策必须是以人性之恶为依据,而不应对人性加以否定。理论要以现实为依据,治国之道要“称俗而行”,要“因人情”。既然人情好利恶害,治国的目的就应该与人情相符,是赏功罚奸,而不是仁义礼乐。《韩非子·八经》:“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六反》:“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
简言之,荀子以“性恶论”为假设前提,推导出“以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而归于暴”;进而提出解决方案:“化性起伪”、“化恶为善”的诱致性制度安排与“起礼义,制法度”的强制性制度安排。“礼法”整合由此而起,“礼法”的制度规范,亦由此阐明。最终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礼法”模型。(如果要创立“伦理经济学”,恐怕中国人最具条件。此乃题外话。)荀子的“礼制”思想,是对孔孟以“性善论”为核心的“仁政”思想的扬弃,而为以“自利心”为内核的“法制”思想进行了铺垫;因为“礼法”具有双重的制度功能。
荀子的这些思想对韩非有很重要的影响。然而,荀况是一个“礼表法里”的儒家;他的“隆礼至法”思想对其弟子影响颇深。加以韩非本性就“喜刑名法术之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于是他尾随其师的“隆礼至法”而将“刑德”联称。弃礼而重法,一步之遥,“礼、法”就分道扬镳了。韩非认为,人之性情好利、恶害而自为,不存在仁义礼义上的人与人的关系。韩非是用法取代了荀子的礼义,但是却继承深化了荀子的“性恶论”。《韩子·奸劫弑臣》:"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韩子·外储说左上》:"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韩子·备内》:"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从荀子的“性恶论”,到韩非的“自利论”,几乎一脉相承;韩非所提出的:“夫安利者就之”、“利所加也”、“利在人之死也”等等,诸如此类的“好利”、“自利”思想,与现代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思想,不谋而合,也可以说是世界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的“经济人”假说;也有基督教中的“原罪论”倾向。因为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仅靠“礼”,是不足以规范、制约人的“经济人”行为的,所以《韩子·八经》:"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子·六反》:"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还有《韩子·六反》:"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这就把法家的治国理论推展到了唯目的、唯实践和极端功利的境地。至此,以法家思想来设计的各种制度思想也就顺理成章了。
荀子曾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天论》)“礼”和“法”同是一种制度,一种秩序,二者的施用本有异曲同工之效,因此“礼”“法”二者可以相提并论。陈柱先生曾说:“法家盖起于礼。礼不足为治,而后有法。礼流而为法,故礼家流为法家,故荀卿之门人李斯、韩非皆流而为法家也。”(见陈柱《诸子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则知韩非“法”的思想曾有荀子“礼”的思想的影响。此外,童书业先生认为:“荀子的思想通过韩非、李斯,颇有影响于秦朝的政治,而汉朝的制度有许多是继承秦朝的。汉朝所谓‘王、霸杂用’的政策,实际上就是阳儒阴法,而荀子便是一个儒家大师中‘阳儒阴法’的人;必须明白这点,才能抓住荀子思想的本质。” (童书业:《先秦七子思想研究》,第173页,齐鲁书社,1982年)
如果说荀子的引法入礼的“礼制”思想,是中国古代制度思想的一大创新的话;那么,韩非对儒家“礼”的扬弃,全面提升了制度的强制性功能的“法制”思想,则是在古代中国由“礼崩乐坏”到“大一统”之际的社会转型期的制度思想的一个里程碑。诚如胡寄窗先生所言:“韩非抛弃了荀子用以防止争乱的‘礼’,主张以法度代之,亦即不依赖伦理规范以防止争乱,而把制止争乱的办法诉诸剥削阶级国家的政治法权”。(胡寄窗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P.46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由此,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思想的二大范式基本确立,从而为以后诞生的“大一统”国家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但是,荀子强调以“礼制”正名以尊王,与韩非重势以尊君;二人在对待“君权至上”的思想方面有相同之处。此外,荀子的性恶论也为韩非的自利人性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尽管二人对如何治国安民,经世济邦的方针政策有所不同,但将设置制度环境,进行制度安排的主体锁定于“君王”,这一点是认同的;由此也可看出儒、法二家制度思想的脉络轨迹。这更是此二家制度思想受宠于历代君王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君主集权专制的制度思想,是由儒、法二家思想或者说是“礼制”与“法制”二种思想之间的相互渗透、彼此汲取、互为表里而共同完成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