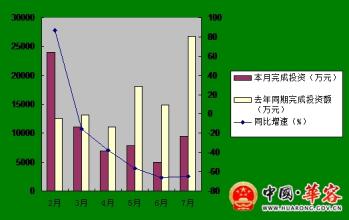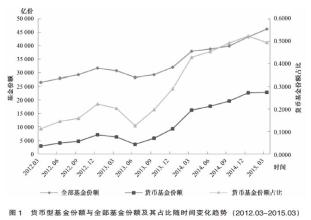一、引言
“三农”问题得到各界的重视。2004年以来,中央采取了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农业、抓好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减免农业税等举措意义非凡,因为农民负担过重正是“三农”问题的历史成因之一。研究表明,我国1949年以后的国家工业化,其初始资本积累主要来自于国内的农业剩余,这对于“三农”问题的形成和强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考察“三农”问题需要历史的纵深和广阔的视野。此时,重新探讨我国1950年代发起的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制度是有意义的。
众所周知,我国历时二十多年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绩效。对此,经济学家的经典解释是,由于集体农业对劳动者和监管者的激励不足,从而挫伤了劳动者和监管者从事集体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而取代集体农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解决了“激励机制”问题。应该说,这种经典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有效的激励机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农民的积极性,是农业生产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而民间流传的“出工像背纤,收工像射箭”一类的顺口溜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工分制”的缺陷。然而,经典理论在讨论集体农业绩效问题时,并没有将统购统销等宏观政策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实际上,统购统销等宏观政策因素对集体农业绩效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1980年代初期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的迅速增加,除了由家庭承包制取代集体农业制度这一制度变迁激发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之外,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缩小城乡产品剪刀差的举措也是重要的原因。
客观上起了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作用的统购统销制度,其实质是一种赋税制度,构成农民负担。一个普遍有效的定律是,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存不存在统购统销制度,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积极性甚至对于集体农业的态度大不一样。因此,就集体农业的激励机制问题而论,既有因为“工分制”等集体农业内部分配制度方面的缺陷所导致的效率损失,还有由于统购统销制度引起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我们通过对集体化时期浙江沿海一个生产队粮食分配方案的分析发现,在统购统销制度下,由于集体农业内部的大部分粮食剩余都被政府统一收购,因此集体农业内部已经很难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为了论证这一观察,作者做了计量研究。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在第二部分,我们将对有关集体农业绩效和统购统销对农业生产影响等方面的文献做一番简单的回顾与评析;在第三部分,我们会报告一份新近发现的集体化时期浙江沿海某生产队的粮食分配分户方案,从中可以发现激励机制的作用空间相当有限;在第四部分,我们将提出一个统购统销影响粮食生产的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并给出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结果以及简单的解释;在第五部分,我们针对回归有可能出现解释变量内生性的问题,用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再次进行验证;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回顾与评析
对于集体农业的低效率,经典理论主要着眼于其内部制度的考察。在文献中,通常借用阿尔奇安、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msetz,1972)式企业理论的分析框架。相对于个体小农的分散经营,集体农业的合作生产具有分工和专业化的比较优势,但是农业劳动的时空特性使得合作生产的“计量”和“监督”十分困难。面对“监督”难题,集体经济的管理者选择实施一个较低的监督程度;而由于“计量”的困难,只好在分配上采取“工分制”。在此制度安排下,农民的理性选择自然是偷懒而不是努力工作(Lin,1988)。此外,集体农业除了对社员努力的激励不足之外,还存在对管理者的激励不足。由于集体农业的监管人不拥有剩余权,因此,这一产权残缺削弱了剩余权激励机制,导致集体农业对管理者的激励不足(周其仁,1994)。而在家庭经营下,原来参加集体劳动的社员现在自己就是“剩余索取者”,因而也就不再需要监督劳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这种制度安排被认为不仅解决了集体农业内部由于“工分制”所造成的社员偷懒问题,而且避免了对监管者激励不足而导致的无效率。
这种经典理论影响深远,也颇具解释力。因为,主要以年龄、性别和工种来评定工分的制度安排违背了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但是,影响农民积极性的除了“工分制”这一内部分配制度之外,还有统购统销一类的外部政策因素,后者决定了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关于统购统销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直接影响,经典理论还分析得不够。
拉迪(Lardy,1983)认为,中国集体化时期农业生产率之所以下降,是由于中国自1953年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尤其是大跃进时期,地区粮食自给政策开始加强,指令性的播种面积计划经常要求并不适合耕种粮食的地区也只好播种粮食,这导致各地区不能按照地区比较优势安排生产。
对此,林毅夫和文贯中(Lin and Wen,1995)用计量方法得出,1952年到1990年间,统购统销制度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有时正有时负,而不管是正或是负的影响,大小从来没有超过3%,因此统购统销的推行或取消不是人民公社和生产队时期农业生产率低的主要原因。
我们认为,拉迪所指的地区粮食自给政策只是统购统销政策的一个方面,他考虑的是地区比较优势的丧失,并没有论及统购统销的其他后果。而林毅夫和文贯中得出的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统购统销造成的后果很难做精确的量化分析;其次,从逻辑上说,统购统销毫无疑问对农业生产造成了负面影响。
统购统销政策本是权宜之计,然而路径依赖法则和意识形态的偏执使得这一政策被长期制度化了。在统购统销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政府总是想方设法从农民的手里多拿些粮食,经常出现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挤占农民口粮。为防止征购“过头粮”,1955年中央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办法,由各地根据当地农村的生产水平和消费状况,规定农村口粮、种籽、饲料的留粮标准,作为划分余缺、计算购销的依据。然而,正如珀金斯(Perkins,1966)所说,尽管“三定”政策的目的是让农民有足够的余粮,但是实际上农民所拥有的余粮是非常可怜的。
粮食统购的数量和价格都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或批准的。统购的粮食和农业税(公粮)加在一起称为“征购”。杜润生先生说,“集体化20多年当中,国家只要多购1/10就会挤占农民的口粮”(《新华文摘》2004年第8期)。集体化早期,粮食的收购价格通常要比市场价格低20%-30%(Perkins,1966),后来收购价格虽有所提高,但仍低于市场平均价格。就其实质而言,统购统销与其说是一种农产品流通体制,不如说是一种赋税制度。
表1:一些年份粮食收购与零售混合平均价格:(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470、478页。
统购统销政策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形式控制着农业剩余的分配。据一些学者估计,1952—1990年间我国农业通过剪刀差方式为工业化提供了高达8708亿元的资金积累,平均每年223亿元(冯海发、李溦,1993)。有学者将统购统销制度称为“倒定额”(武力,2004)的赋税制度,因为除按照政府规定的消费标准留用的粮食外,其余都以税收和征购的方式由政府拿走了。这种竭泽而渔的政策表面上最大限度地提取了农村的剩余,实际上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三、一份生产队时期材料的启示
由于国家通过统购统销政策拿走了生产队的大部分剩余,所以很多生产队分配时不得不主要按人口平均分配以保证生存,余下的极小部分才按照劳动工分进行分配。在此情况下,生产队内劳动的激励机制应该分成两个层面:一是通过搞好生产争取在口粮标准之上从国家手里多拿到人均二三十斤粮食;二是在生产队里,通过工分制比其他社员多获得一二十斤粮食。所谓“激励机制”的作用范围不过如此而已。
最近,作者收集到一份浙江沿海象山县一个生产大队完整保存的1960-1970年代的分配材料,发现在农户的粮食分配中基本口粮与工分粮的比例平均在4:1以上(见表2)。由于当地的村民坚称在当年的生产队里他们就是严格按照分配分户方案来进行分配的,因此数据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表2:浙江省象山县贤庠公社红建大队某生产队1965-1979粮食分配情况
数据整理自:1960-1970年代浙江省象山县贤庠公社红建大队某生产队季(年)度社员分配分户方案,最后两列数值由作者根据前三列数据计算得出。注:1968年生产队由原来的26户增加为40多户,到1979年增加为64户。1969全年只有其中23户的数据。
基于以上数据,我们有理由推测,农业集体化时期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这一点,主要不是由于集体农业内部分配制度的缺陷所造成的,更多的是因为国家和农村之间的畸形分配结构造成的。在统购统销制度下,农民生产再多所得也不过是口粮,因而在集体农业内部采取了“应付”、“维持”、不多生产的策略,严重压抑了生产积极性。下面,我们试图通过计量工具来分析统购统销政策对集体农业生产的影响。
四、模型设定、数据说明和估计结果
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包含气候、土地、种子、化肥、水利、农用机械以及精细的管理。由于气候、种子与水利没有系统的数据,本文不将它们归入解释变量。而在我国农业劳动力普遍过剩的背景下,农用机械不是影响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本文也不予考虑。管理精细与否取决于劳动的努力程度,基于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的普遍原理,劳动的努力程度又是工资的函数。
假设粮食生产函数是Cobb-Douglass型的,即有:
(1)
其中表示劳动数量,表示化肥施用量,表示粮食播种面积,ε表示其他影响因素,α、β、γ是参数。为粮食生产效率,它与劳动的努力程度有关,可以假设:
, (2)
其中是农民的人均收入。假设生产队只生产粮食,那么农民的人均收入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其中之一就是农民分得的粮食实物,另一部分则是从生产队分得的现金,而现金主要来自生产队将粮食出售给国家所得的款项。设国家统购统销的粮食数量占总粮食的比例为,则国家统购的粮食数量就是,生产队的留粮就是。假设粮食的统购统销价格为,粮食的市场价格,通常。
因此以实物计算的农民收入为:
, (3)
上式可以转化为:
(4)
可见,再由(1)式和(2)式可知:
(5)
根据上面的简单模型,我们能够推出一个可经检验的理论假说:粮食总产量中国家收购的比例越高,收购的价格越低,粮食的总产量就越低;反之,国家收购的比例越高,收购的价格越低,粮食总产量就越高。如果这一假说得到证实,就意味着统购统销对粮食生产起了消极的影响。
基于上述的理论分析,我们建立如下的计量模型:
(6)
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和农林牧渔部计划司1983年编的《农业经济资料(1949—1983)》。由于粮食生产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因此需要对粮食播种面积进行一番调整。我们参考石磊(1998)的做法,调整后的粮食播种面积(TZMJ)为:,其中,LSMJ为本年度的粮食播种面积、ZMJ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CZMJ是成灾面积。
我们采用了逐步回归的办法,将不显著的变量逐次从模型中剔除,然后分别进行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3。
表3: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为log(Y))
注: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标准差,***、**、*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
在回归结果(1)中,我们发现log(PG)和Log(LD)两个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在剔除log(PG)之后,我们发现在回归结果(2)中,log(LD)的系数仍然不显著。再将log(LD)剔除,我们得到回归结果(3),此时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作为比较,我们在剔除了log(r)之后得到回归结果(4),发现调整后的决定系数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初步判定log(r)对log(Y)产生影响,而其系数为负值(-0.354),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们前述的假说。
劳动力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一现象大有深意。在集体化时期,农村除了执行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由政府主办的供销社和粮站之外,几乎没有其它商业单位;又由于1962年经济调整时期国家规定人民公社内部的非农就业不得超过5%,生产大队以下禁止搞非农产业,因此,农村过剩劳动力不可能向非农产业转移(温铁军,2000, 第224页)。因此,从资源合理配置的角度来看,比起其他资源(土地、资本、技术等)的投入,集体农业内的劳动投入必然相对过多。在此情况下,单纯刺激劳动投入必然会出现劳动的边际报酬严重递减甚至为零,导致集体农业的“过密化”(黄宗智,1990)。这是集体农业禁锢劳动力所带来的恶果,同时也证明了经典理论的局限,这种理论强调集体化时期的问题是由于“工分制”导致的对劳动投入的激励不足。
粮食收购价格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国家收购价格的变动并不能解释粮食产量的变动。这一点或许是由于,我国集体化时期,农民生活始终濒临温饱边缘,农村商品和其他物资极度匮乏,货币分配与实物分配比相对不重要。而粮食收购比率的回归系数相当显著,这一点跟我们理论模型的预期一致。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因为作为解释变量,粮食收购比率本身可能是粮食产量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原因,也就是说存在粮食收购比率内生的可能。下面,我们尝试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办法再次进行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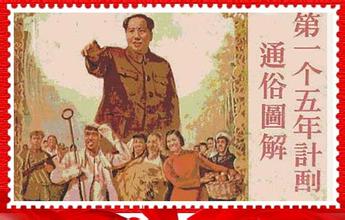
五、因果关系检验
这里的研究主要考虑以下三个变量:粮食总产量(y)、粮食净收购量占总产量的比重(r)和粮食收购混合平均价格(p)。采用的数据为1953—1982的年度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同上。为了研究的方便,考虑到通过对数化以后并不改变变量的特征,所以对变量y、r、p都取自然对数,从而得到新的变量序列,分别记为logy、logr和logp。
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必须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时的滞后长度通过AIC准则来确定。
表4:ADF检验结果
注:由于序列logy具有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因此logy的ADF检验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其他变量的ADF检验既不包含常数项也不包含趋势项,ADF统计量后面括号内的数为检验方程中包括的滞后阶数,加入滞后项是为了使残差项为白噪声。
从表4可以看出,水平序列logy、logr、logp不能拒绝单位根假设,而其一阶差分序列拒绝了单位根假设,说明水平序列logy、logr、logp都是非平稳的I(1)序列,而其一阶差分序列△logy、△logr和△logp都是I(0)序列。
由于logy、logr和logp都是一阶单整的,因此我们能对其一阶差分变量△logr、△logp与 △logy 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滞后阶数选取根据VAR系统整体的AIC与SC信息量综合确定,最后滞后阶数定为1。
表6: △logr、△logp与 △logy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lags=1):
注:最后一列Probability表示原假设(Null Hypothesis)发生的概率,其值越小,表示拒绝原假设的概率越大。
表6表明至少在95%的置信水平下△logr是△logy的Granger成因,即净收购率的提高,会导致粮食总产量的降低;反之,净收购率的降低,会导致粮食总产量的提高。这一检验结果与前述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可见,农民对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做出合乎理性的反应。在统购统销制度下,农民很难有生产比定额更多粮食的激励。因为口粮标准是固定的,农民也知道这是一个不会让他吃饱或者只能勉强吃饱的制度,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分配和激励机制的问题。另外,△logp不是△logy的Granger原因,表明粮食产量的变动不能由国家收购价格的变动来解释,也与前述的回归结果相吻合。
六、结论性评论
从上述两种经济计量的研究可知,统购统销政策的确对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在统购统销制度下,农民口粮以外的粮食剩余几乎都被政府的粮食部门低价收购,因此就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而论,这是一种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相一致的扭曲的激励机制。政府独享剩余的控制权以及几乎全部剩余的索取权,而农民被排除在剩余分割的谈判之外。在政府通过统购统销制度提取了集体农业的大部分剩余之后,集体农业内部更难以建立按劳取酬的激励机制,致使集体农业的经济效率低下。
我们的研究也证实了黄宗智(1990)的观点,即我国集体化时期存在着农业劳动的“过密化”现象。这一点主要是由于,统购统销制度与农业集体劳动制度相结合,极大地限制了农民耕种经济作物乃至从土地中脱离出来从事非农产业的自由,导致集体农业中劳动的过量投入,边际产量递减严重。
本文分析的尽管是个老问题,却不乏现实意义。过重的直接或间接税负会使得农民从事农业尤其是种植业无利可图。在统购统销制度下,粮食等农产品价格被人为压低,农民的间接负担十分沉重,辛劳终日只能得温饱,因而生产积极性低下。现在,虽然中国不少农产品价格在国家保护下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市场价格水平,但由于各种农业生产资料的垄断性经营,其价格要远远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农民收支相抵后所剩无几,从事农业没有收益似乎成为“共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且,农产品征购权,像政府的其他权利一样,很容易被滥用。在消弭愈演愈烈的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为核心的“三农”问题之时,政府角色的恰当定位相当重要。数十年来国家对乡村的不公平待遇,现在当是扭转之际了。近来,中央一再强调增加农民收入,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因此局面的扭转是可以企盼的。但是,建立城乡协调发展的机制,尚需各界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Alchian,A., and Demsetz,H. (1972),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 777-795.
2. Granger, C.W.J.(1969), “Investigating Causal Relations by Econometric Models Cross Spectral Methods”, Econometrica, 37, pp. 424-438.
3. Lardy, Nicholas R.(1983), 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Lin, Justin Yifu.(1988),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36 (April): S199-S224.
5. Lin, Justin Yifu and Guanzhong James Wen(1995), “China’s regional grain self-sufficiency policy and its effect on land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19.
6. Perkins, Dwight H.(1966), Market Control and Planning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7. 周其仁(1994):《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管理世界》1995年第3、4期。
8. 冯海发、李溦:《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数量研究》,《经济研究》1993年第9期。
9. 武力:《试论1949年以来农业剩余及其分配制度的变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0. 黄宗智(1990):《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
11. 石磊:《中国农业组织的结构性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年。
12. 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