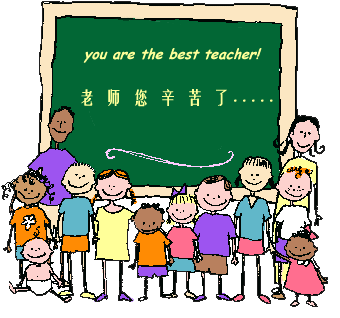春天并不是一个会让我特别期待的季节,与小学课本里所讲授的春姑娘飞来飞去的美好场景不同,在北京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春姑娘已经有若干年不曾光顾,取代她的是不知道哪个童话中的女巫。对于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来说,春天不谈一谈风沙的问题,似乎就没有真正地体验过生活。环境问题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政府苦心经营若干年的号称全世界最大的防护林工程在前进的沙漠面前好似薄纸一张,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我们多年来防沙、治沙和经济发展的思路与做法。我们的草原、河流、湿地、湖泊甚至山川都面临着相同的尴尬局面——人类行为的足迹已经使整个自然环境伤痕累累。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现代经济学所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当理性的个人需要集体做出有关的决策时,可能就会出现非理性的局面。当然这种非理性的具体表现可能会同决策的方式有关。比如,在集中决策时,计划者必须面对信息的收集与鄄别问题。要做出对全体成员都有利的决策,决策者需要收集与整个事件有关的信息,而且必须分清楚哪些是对决策有用的信息,哪些是无用的信息。但是,这样的信息恰恰是无法准确收集的——比如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收集所有信息所用到的成本几乎是无法计量的。失败的组织和计划是造成环境恶化的第一根源,在传统的集体决策方式中,决策层赖以做出决策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它未能包括决策将为社会带来的所有成本,或者说决策者只考虑了部分成本,而将更多的成本推给了未来,由他们的下一代来承担。科斯认为
,只要可以在所有的利益方进行平等的谈判,决策的社会效益就会最大。但是,当成本是在代际之间传递时,这种谈判变得没有可能性——后人在前人带来的成本面前没有谈判或选择的权利。 此外,决策者所收集到的信息往往是滞后的。一项决策出台之前,决策当局需要首先花费大量时间收集与之有关的信息,当决策做出之后,来自于个体的信息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因此决策的供给会落后于个体的需求。就像计划经济的商品定价永远都落后于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一样,集中决策永远都无法达到均衡状态。需求的不满足会通过体制外的行动表现出来,当这些行动已经使得原有的决策再也无法推行时,决策者会根据新的情况进行调整,遗憾的是,调整往往是在社会已经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阿玛蒂亚·森[3]在深入研究了饥荒问题之后得出一个令人深思的结论,饥荒的形成往往不是生产力落后的结果,而更多是与社会有关粮食生产和分配方式有关。换句话说,在一个并不十分落后的国家,不恰当的决策制度会给社会成员带来巨大的损失。在前苏联的社会实践中,至少在60年代以前,其经济的增长率是居于世界前列的。而饥荒和环境大规模破坏正是发生在苏联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旗帜下,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得不到食品而挨饿,而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也在当局的掠夺式开发中受到破坏。集中决策的另一个重要的弱点在于,它只能选定所有目标中的一个作为主要的决策目标,其它目标必须服从该目标,社会与生活的多样性受到压制——剥夺个人的选择权是一种重大的社会损失,因此这样的增长是建立在极大的隐性成本基础上的,而这些成本会因为众多复杂的原因被人为地忽略掉。
按照前面的分析逻辑,仿佛只要将决策权分散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事实恰恰相反。经济学家们描述了一种分散决策的失败模式:在一个大家共同行使产权的草原上,每一个牧民都按照自己的利益设定产出数量,他的最佳选择是最大限度地增加牲畜的数量而不去管草原是否能够承受。由于草原产权的公有,每一个人都无须考虑自己的产出对其他人所造成的成本,收益的内部化和成本的外部化为草原提供了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人们都被锁在一个迫使他们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这种状态被称为“公共地悲剧”。公海捕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有的国家都鼓励自己的国民到公共海域作业,因为即使你不这样做,其它人也会如此,结果就是海产的数量急剧下降,结果谁也捕不到足够的鱼。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渐渐减少,但草原的破坏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反而愈演愈烈。获得了生产经营权的牧民开始了它们对草原新一轮的掠夺。随着人口的增加,有限的草原必须养活更多的人,在没有管制的条件下,每一个牧民都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设计自己的最优产量,以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公共财产的草原便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局面,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草原在人们的掠夺中消失并不是一种危言耸听。
必须指出的是,以上所讲的公共草场的悲剧并非不可避免。但加强宣传力度、企求人人自律也许是迄今为止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中最失败的一种。因为大自然一旦把道德与生存对立起来,绝大多数人将立刻选择生存。草原上的人们一直以来需要的是改变他们危险的生存方式,但社会并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选择机会,这充分暴露了我们这个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或许是无意的排斥与歧视。牧民之所以继续在贫瘠的草原上期盼未来,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找不到更加有利可图的谋生手段。由于社会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设置的种种障碍极大地提高了劳动力流动成本,贫瘠的草原对牧民来说已经是最好的选择。在很多地区,个人创业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鼓励,社会对不同经济成分的不同待遇使私营经济始终无法同公有经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由于创业成本高,放弃畜牧业对牧民来说显得无利可图。此外,牧民缺少足够的资金来源,在土地产权集体所有的条件下,个人要想通过抵押土地产权来获得资金是不可能的,而畜牧业本身又难以依靠自身的积累扩大资本规模,因此,从畜牧业进入新的产业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约束。社会资源的交易程度不足,导致牧民可选择生产集合缩小,降低了放牧的机会成本,落后的生产方式非常容易维持。
解决目前的问题可以说有若干种思路,其一就是建立合适的退出机制,解除牧民对草原的人身依附,同时为牧民进入城市地区和其它产业扫清一切障碍。当然,解除人身依附有诸多办法,假定我们不对现在的生产方式做任何调整,牧民的逐渐破产将是最自然的解决办法,但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牧民有权利在一个多元化的市场上进行自由选择,如果其它市场的进入成本降低,如果牧民可以通过现有的资源筹集到创业资金,继续放牧将是牧民机会成本最高的选择,这样一来,多余的牧民退出畜牧业,减少牧场的负担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思路之二是政府适当介入。过度放牧、草原退化的根本原因是牧民所付出的成本与获得的收益之间严重不对等。除了牧民自身以外,广大华北地区的居民也成了受害者,如果不考虑交易成本,受害居民有可能以一定的价格去购买牧民的放牧权,以阻止环境的继续恶化。但是,要求华北地区上亿居民同所有牧民达成协议是非常困难的,巨额的交易成本使得自发的市场秩序无能为力,此时需要政府出面予以配合。事实上,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在部分地区推行了退耕还林的试点,由国家财政出面补偿由于农民退耕造成的损失。这相当于改变了原来的比价关系,使植树造林比毁林开荒更加赚钱。换一种角度,这相当于政府将城市居民由于拥有在户籍、劳动用工、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垄断权而获得的额外收益重新分配给牧民(这些收益原本应由双方共有,只是因为不合理的社会分工才被城市居民全部占有),因此,补偿本身还具有社会收入再分配的效应。
但是政府介入并不是一种完全有效的措施。政府必须解决好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确定赔偿的数额,在这种确定机制中牧民是否会被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如果牧民继续把自己的命运寄托给好心人的施舍,我们就不能说这将是一种有效的制度;二是政府的层级代理系统在补偿金的发放上是否具有效率,从政策到现实之间会有多大的社会福利损失。
思路之三是重新分配草原的产权。当印第安人的猎物越来越少而使得部族之间必须通过激烈的竞争才能找到猎物时,产权就出现了。他们开始圈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建立排他的使用权。产权分配的原因是要将放牧的外部效应内部化,也就是说,在没有产权分配的条件下,私人自己享有放牧的收益,而成本却由社会来承担,当产权分配到家庭或私人手中的时候,所有的成本都由产权所有者承担。如果牧民对草原能够享有足够长时间的产权,他们就会有信心对草场进行投资,相应地,短期行为也就减少。如果牧民拥有大片草场的所有权或稳定的经营权,而且能够自由流动,那么经营牧场的牧民就有可能通过交易的方式将未来收益资本化,[1]
短期行为和掠夺式开发将不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经营方式。同时,激烈的竞争可以随时淘汰没有能力经营牧场的经营者,把资源配置到有能力的牧民手里去。思路之四是引导社区或协会自治,建立畜牧业自我约束机制。传统的经济学对公共地悲剧的解决办法只有两个:政府介入或者是充分界定的私人产权,但这些并不带有任何必然性。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面临公共地两难处境的人们,可以通过协商确定他们自己的体制安排,来改变他们的产出数量。
这一体制安排可以通过社区自治或行业协会来进行,重要的是协会要得到该行业的承认,协会可以对行业进行管理,安排放牧牲畜的数量,牲畜数量减少所带来的损失部分地由畜产品价格的提高来补偿,另一部分损失则因为草场的使用期限无限延长而慢慢地得到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分散而非集中经营的经济中,行业协会的建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对于单个生产者来说,要同整个行业的人进行联系是一件成本高而收益少的事情。把协会挂靠在政府的名下,由政府协助组织也许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但也是风险最大的一种方法——如何保证它不会成为一个公开出卖放牧权的寻租机构,将是对所有人智慧的真正考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