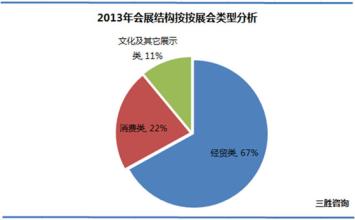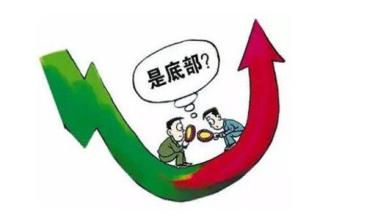一、靡然向风:惊乍人心的学者“下海”潮
§学者“下海”现今是时髦事,马恩不也曾设想未来社会的职业变换?
学者“下海”,在当今中国社会,有如POPS音乐一样流行,巴黎时装一样时髦。当有人说“我下海了”,你难道不能品味出他那惬意、张扬的情绪?如果有人说“再痛苦也得下”,这是否意味着正在“商人”与“学人”双重灵魂的撕扯中徘徊,作市场原则式地“两害权其轻,两利择其重”的选择?对于学人来讲,下与不下,远不是对与错、是与非的问题。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利益取向,他不仅有理由,而且有权利,作选择与再选择。除非他自愿,谁凭什么强迫一个人终身于一种职业,在“一棵树上吊死”?
然而“下海”成为一股风潮,却迫使人反复地想,这件事究竟意味着什么,给社会一种什么预示?这无疑应当从多角度来进行透视,而经济学感兴趣的是,这股风潮背后深层经济关系的嬗变。
§如今庸才平步青云加冕教授却不新不奇,学者“下海”倒惊乍人心
如果有消息称,某个极其平庸的人平步青云,抑或业已“加冕”教授桂冠,你大可不必愤愤不平,我以为这在如今既不新奇也不富于剌激性;但是当我听说一位研究有素的学者不得不弃学经商时,却令人感慨万千。我首先想到的是,是什么力量使得他神使鬼差地要去“下海”?
凡事岂能一概而论,其间自有个中缘由。在过去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生活中,全国劳动力是作为一个总的劳动力来对待的。每个人,都只是社会经济大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所谓“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种体制抹煞人的个性与特长,计划式地对劳动者进行工作分配,用一种单向的、迹近独断的社会选择完全地代替了个人选择。作为个人选择,可能有双重含义:一种是理想价值取向,一种是功利价值取向。个人的职业选择,究竟是哪一种取向,人与人的个体差异之大,有道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与个人选择相对应的社会选择,在大一统的体制下,是作为革命事业的需要而实现的。究竟什么是革命的需要,它是否确切反映了革命事业的实际需要姑且不论,社会选择与个人选择的不一致乃至冲突,在改革前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才流动”,正是对通过改革来消除这一社会冲突的一种描述概括。人才之所以可以流动,在于人从“部件劳动者”转变为“自主劳动者”。有了自主性,他才可以流动。这样,选择就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社会选择个人,个人也在社会的多元中自主选择。一当这种选择场合从行政机关挪到市场的时候,双向选择便真正的名副其实,变得规范化和富于现代气息。这就是为什么一搞市场经济,就有那么多“下海”者的内在原因。市场经济给人们提供了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对于改革以前参加工作的人来说,真千载难逢的良机,有多少人愿意错过呢?
从某种意义来讲,“下海”潮是一次专业大“归队”,干哪档事得哪档钱,这总比吃着“皇粮”赚银两更光明正大得多。[1]
§从旧有人材中革面洗心,是没有办法的好办法

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尽管在过去工作的年份中表明,或许他并不存在社会选择与个人选择相冲突的状况。但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市场的选择与再选择中,他可能会碰到最优或者创造出最优来。如今,谁能对这种富于创新的生命活力说三道四?更何况,市场本身还会魔术般地变幻出新的社会需求来,因而要求劳动者不断地重塑自己,以适应市场的选择。年轻,就是可塑性的同义语。因而,市场总是更多地将年轻人作为再塑造的最佳人选。
一个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体制,社会对于与市场机制相关职业的突然需求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社会本来并没有为市场经济准备这种人材,而现在又必须立即有,除去迅速培养(如同市场经济扫肓或曰扫“商盲”)外,在过去社会为计划经济培养的人材有人“下海”,转变身份,改换面貌,是最为经济的办法。书记变厂长,局长变经理,现今不是司空见惯吗?人们大可崐不必对此非议,这可能是没有办法中的好办法。
§说开了,学者墨客也确有难言之隐
客观地讲,失灵区内商品化骚动绝非无缘无故,学者墨客也大有其难言之处。其一,不平则动。社会财富分配天平的失衡,体脑倒挂,以至知识价值贬值,是骚动的本因。其二,滥用商品经济原则。如要求学术刊物自负盈亏,实行公共部门企业化,将职称与上缴利润挂钩,官商、官倒在增无已。其三,法律不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是法制管理,它既有市场经济区内的,亦有失灵区内的法律法规。其实,从失灵区的骚动中,人们也不难听到一些弦外之音:首先,这不是精神生产劳动者在呼庚呼癸吗?健全的社会应当对此迅速作出反应。其次,现今已不是对商品与货币刻木为吏期不对的年月,“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文化人何尝不可在变革中跳槽,重作选择,变幻角色,去“潇洒走一回”呢?最后,精神生产劳动者的人格、品位,也是不断变化、不断创新的,是否会在改革中塑造一类新的人格形象,出现一些“先商后文”人、“先文后商”人、“文商人”、“商文人”,乃至“文化经纪人”来呢?
二、社会评估:学者及其思想的轻重是非
§“下海”人群多于鲫,恐怕可以说是论非吧!
问题就出在这里。是否任何人“下海”都无可厚非的?任何行业中任何数量的人“下海”都理所当然?我大不以为然。
学者“下海”是一个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如果他是一个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不一致的“牺牲品”,他一直勉为其难地在工作(出学入商,对他来讲,可能是“归队”),是一回事;如果他是一个可望在市场经济中有更大发展的奇才,是一回事;如果他要在理想与利益中重新调整自己的取向,拟或旨在逃出学界“有形的手”造成的不平环境,而入市场寻求“无形的手”给予平等竞争的机会,也无可指责。这是在经济生活是对自己重新定位的一类人,我要说的是另一类型的人,他们热爱自己的职业,惜时如金地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辛勤劳作,如今因种种原因“下海”了。
§少一个学者,多一个企业家,是件好事吗?
面对这种现象我想问:少一个学者,多一个企业家,在当今中国社会是一件好事吗?
当然会有极端现象。如果少一个平庸的学者,多一个“红色资本家”,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反之,多一个平庸企业家,少一个出色的学者,恐怕问题将其为大问题。
说到学者,在人们心目中大凡有个区别,即社会科学家不能与自然科学家相提并论。对于自然科学家,人们似乎还是认同的。但是对于社会科学家,人们的认同感却是大打折扣的。[2]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社会科学是否能成其为科学,也是大可怀疑的。产生这种认识的原因确非虚拟。
§过去的年代中,中国的社会科学算是丢尽了脸
首先,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社会科学可说是丢尽了脸。撇开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不成熟不说,在近代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即科学性历来是人们批评的焦点。社会科学各门学科,都有不同程度的辩护色彩,都有自己的御用史。“御用文人”的概念何以家喻户晓?它不知多少次地亲手给统治阶级的种种行为披上了所谓“科学”的外衣。同样一个问题,今天可以说红,明天可以说黑;同一个人,他可以毫不脸红地东倒吃羊头,西倒吃猪头。所谓“随风飘扬”,成为他永远走红、总也正确的秘诀。[3]
其次,与上面一点直接相关的,是人们通常指责的社会科学明显的非科学性。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特点,使得人的主观性很容易渗透其中。利益取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是一个难以治愈的顽症。科学是不为任何集团利益服务的;然而社会科学有明显的服务性。特别是在其具有阶级性的时候,更是说不清道不明。研究方法和语言表达上,社会科学也留有许多可被指责之处。
至于说到令人眼花缭乱、层出不穷的“新学科”,简直叫人啼笑皆非。某个时期,甚至到了有个什么新词儿,就有什么新学科,就有什么新报刊杂志,就有什么新研究团会的地步。有人陈述过这样一件事:当一位“老大粗”领导干部手捧一本有关什么“领导科学”的书时,激动不已,他对人们讲,这下好了,干了几十年都不知道,原来领导就是“科学”,现在我们领导也有了“科学”。而工人却想,如果我们有权有钱,照样可以有“工人科学”、“群众科学”?这对中国学科建设中的不严肃性或曰“儿戏化”倾向之讽剌,可谓入木三分。如果在现今的专业户名称中加上一个“学科创建专业户”的话,大概是可以反映中国学术界的一些现实的。
§不敢说还是没想到?影响世界走势的,其实是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
尽管如此,这并不证明社会科学不成其为科学。更不能说明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其作用小于自然科学。当然,这里有其不可比因素。如果将自然科学比作社会经济发展的硬件的话,社会科学则是其软件。谁能区分出,是硬件更重要还是软件更重要呢?恰似科学技术中,由于硬件直观、具体,技术便于保密,因而其市场价值便于体现也便于实现一样,软件往往不直观、抽象,技术也难于保密,因而知识产权成为当今市场经济中的一大难题。社会科学自它的生命开始,就没有建立与个人利益的联系。在我个人看来,社会科学恐怕与产权概念是相矛盾的。这倒不是因为产权概念的生命史要晚于社会科学的缘故。这主要是,社会科学从一开始便以人类社会为对象,并对其服务的。社会科学的生命之源在于社会、在于人类,这是一个与整体、与宏观从而仅仅与“人之类”相系的科学。人类社会到今天,有了自己的类语言、类文化、类道德、类规范、类意识等等,有了指导人类各种行为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政治思想等等,有了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等等。这正是社会科学独擅胜场,任何自然科学无法替代的划时代功劳。试设想,世界如果没有社会科学,那将会变得怎么样。行文至此,我想起一位曾经影响了经济世界进程的经济学家的一段话:“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的奴隶。”[4] 这着实引人深思。
有人过分地夸大了权力的作用,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说破了,“权”只是一种“力”,一种特殊的社会力,而思想理论则是权力的内在机制,正是它指引着力的方向,引导着社会的运作。毛泽东得到一种思想,因而在中国搞起了人民公社;现在人们明白了,这不过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或曰中国特色的乌托邦思想。
三、唯利是图:会不会轮上人类文化自身?
§“市场经济万能论”是对“计划经济万能论”的报应
如果将过去那种大一统计划经济的能耐概括为“计划经济万能论”的话,我以为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然而近来另一种时髦的极端论调应运而生:即认为商品经济愈发达,市场经济原则就愈通行、商品价值观就愈普及。我看,这倒是不折不扣的“市场经济万能论”。“文革”以来的“极端”文化之风,不是那么容易挥之即去的。对于长期以来用计划原则代替一切,排斥商品、市场的观念,市场万能论算是一种报应、一种“以牙还牙”式地嘲弄。
然而这种报应一旦从认识走向现实,另一种与计划体制相反的不幸便会进入我们的经济生活。经济的庆幸,各有各的欢慰,经济的不幸,对老百姓来讲感受都大体一致: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同样一张“大团结”,不知是被“无形的手”还是“有形的手”抠走了一块。如果对市场功能期望过高,在改革中继续滥用市场原则,我们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市场失灵理论”聊备一说
产品并不生来就是商品,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好理解;但是自进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后,也并非一切产品都要着上商品的盛装而入市。产品的商品化之风,最先流行于第Ⅰ、第Ⅱ产业。第Ⅲ产业的兴起,劳务也加入商品的行列,在产业的历史嬗变中,不仅物质产品而且许多精神产品也变成商品。然而崐,并非所有产品都要乔装入世。以往的经济史昭示:商品经济愈发展,商品生产的规范愈完善,产品转化为商品的界限亦愈明晰。现代经济学中有一种“市场失灵理论”,可谓这类现象的崇议宏论。兹举要简述荦荦大端,以正视听[5]:
——一个国家的公共部门不通行商品经济的选择、定价、资源配置诸原则。
——公共部门一般包括:政府、国防、基础理论与尖端科技研究部门、文教卫事业、公共福利事业、自然资源、命脉通讯交通、医疗保险、部分住宅与城市更新、国际关系等。当然,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包括项目也不尽相同,有些项目还可能具有双重性质。
——公共产品之所以不通行商品经济原则,因为一是不芘懦飧鋈硕运膷
消费,它也不能待价而诂,须由政府经营;二是市场定价量不出正确的产品水准,即市场导向偏差;三是这些产品(特别是文化产品)是类存在的基础(如类语言、类道德、价值观),市场原则会损害它们。
——失灵项目不仅因大气候变化而变化,而且从国家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失灵的涵盖面、内容也是不同的,形成多层次的失灵区。在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管理既科学又严格,各种法规卷帙浩繁,尽力把人们限制在规定的跑道上去进行公正的商品经济竞争。对于僭越、“犯规”者,严加惩处。
我想,只要认真琢磨一番,不难悟出某些东西来:即令在市场经济社会,也有特定的不通行商品经济原则的市场失灵区。环顾现实,却不禁叫人瞪目结舌:商品经济原则如溃堤洪水冲击着昔日平静的市场失灵区。置身于这片区域中的文人学者、专家教师、干部领导、公职人员,多有被五光十色的经济利益撩拨的骚动不安的。说来不可思议:迄今经济运行还相当大程度地未入商品经济轨迹,许多物质产品还仅具有“半商品”资格;而本不进入市场交易的公共产品,却日益被商品化着。有时想来也叫人难以琢磨,为什么一种好端端的经济形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运作,总是漫画式地呈现出来。莫非在经济生活中有某种经济关系之谜至今未解?
§人类为了钱,卖了“实”的卖“虚”的,先卖“污染”再卖“无污染”
大约在十八世纪初叶,当人类社会的一门叫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崭露头角的时候,曾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认识:凡一切可以垄断的、并且具有稀缺性的资源都有价值,都可以成为商品进入市场买卖;那时,学者们通常用的例子是,阳光、空气和水是不稀缺的,而且也是不可能垄断的,因而是不具有价值的。这是经济学说史上的经典例举,后人毫无警惕地不断引用。正当经济学家们重复这一例子的时候,它的经典性受到了挑战,中东地区的犹太人正在悄悄地变着法地将阳光转化为鲜花,在西欧市场倾销。[6]现今时代,水资源的商品化势头,恐怕是人人都感受到了的。下一步利益的竞技场,会不会是眼下人们尚能自由呼吸的空气呢。多一份忧患并无大害,世人尽可拭目以待。人类污染了大自然,先卖着“污染”,现在又燃起返朴归真的渴望,于是又有了卖“无污染”。对此,也许我们可以从“自然公园”的举措中看出端倪。
§这一回,是否轮到卖人类文化自身?
我不是在兜圈子,我是想说,在产业的分化中,人类文化也正在进入“垄断”的范畴,因而正在形成一个产业。先是有了垄断,才会形成稀缺;而稀缺,在经济学上理解为价值与利益便无大错。一如艺术家的声音、形象,在过去是无法固化垄断的,而今则不同,它可以变成录音带、录象带,变成商品,从而进行买卖。前几年,人们面对市场化取向还不无揶揄地调侃道,如果知识可以商品化,那么领导的讲话、政策文件是不是也可待价而沽?曾几何时,还真言重了。在腐败行为乃至犯罪活动中,透露某些领导的讲话精神或思想动态、某些会议决议,偷盖公章,假用某个领导名义,等等,是明码标价的。即令在冠冕堂皇的场合下,诸如盖公章、某些签字、某种名义字号等等,不也是有偿服务吗?但愿我的下述担心是杞人忧天:当前这种人类文化的产业化,究竟会将人类引向进步,还是诱使其倒退?假如人类文明发源初期,从呀呀学语到文字创造,从学习生活本领到模仿行为方式,都是一种付费关系的话,人类至今恐怕不是还蜷伏在洞穴之中便是攀援于树干之上吧!对于一个民族来讲,知识崐文化的商品化会不会是一个陷井呢?
我看,担心在前比悔恨在后要好。
§大劫难有两种,精神泯灭式的劫难更具破坏力
在人类文化史上,大劫难有两种。一种是物质摧毁式的(如“焚书坑儒”,楚霸王咸阳火化“阿房宫”),一种是精神泯灭式的(如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统治,文化大革命)。物质摧毁式的文化劫难,多发生于战争、动乱和自然灾害中等等。而精神泯灭式的文化劫难,则多起因于专制、暴政和民族奴役等等。几乎每个民族都曾遭受这两种磨难,中华民族受难更甚。如果把历史理解为进步与落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史的话,与这两种大劫难的斗争总也是历史进步的主战场。
大劫难不仅摧毁物质文明,对于人类文化的精神文明的破坏,尤其不可估量。而有的东西,则是一旦失去,将永远地失去了。特别是精神泯灭式的劫难,其破坏性的社会广度与历史深度,是物质摧毁式的劫难不能比拟的。
殷鉴不远。及早担心人类文化市场化取向的消极作用,我看绝非杞人忧天。“狼”已经来了,而且已经有“亡羊”,还没有精神准备,实在是不可理解。你纵怀空手套狼之绝技,
四、孰高孰低?交易费用之于学者与企业家
§个人可以无所谓,但社会必须自问:学者与企业家哪个社会费用高?
尽管这远不是个经济帐,但经济帐还得算。无论是学者还是企业家,其实谁心里都有一本帐,局外人何偿没有一本帐。撇开极端情况不说,有人粗算,在一般情况下,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家需要花3-5万人民币,而个人则需С-3万人民币。培养一个硕士乃至博士,其费用如数加1-2倍。他成其为一个学者,个人得投入大量智力和精力,在各方面尚需作出超常的牺牲。受到一定教育并不一定成为学者,个人天赋,意志品质,努力与机遇等等,都将成为成材因素。并不是说学者有多么了不起,只是说成全一个学者的条件是十分苛刻的。恐怕在诸多职业中,学者的成材率是最低的,而淘汰率则是最高的。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劳动价值论时,把智力劳动看作人类劳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看作多倍的简单劳动?[7]相比之下,经济生活对企业家教育水平的要求却要宽松得多,企业家的成功率也要高得多。我这样说,绝无厚士此薄彼之意,也绝无轻看企业家之意。君不见,在“先富”群中,低学历者可说是比比皆是。企业家也要有特定的素质,特定的文化素养以及成为企业家的种种条件,也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其为企业家的,也并非是个学者就能变为出色的企业家的。但是,古今中外的实践反复验证表明,企业家变为学者的比率远远小于学者变为企业家的比率。
那么是不是说,我们的民族文化学术水平过高,以至于文人学者过剩?人们对这个问题已经反反复复地作过否定论证。而且我们也已经知道,我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学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都是很低的,相反文盲和半文盲率却是相当的高。
结论十分清楚:我们也缺少企业家,但却更缺学者。如果学者变企业家,抛开由此产生的深远的历史性损失不说,抛开对社会价值观的嘲弄不说,也是一笔极大的经济损失,或曰社会必须支付更多的交易费用。
§社会受惠于学者的文化思想,谁人想到这种恩惠的份量
其实,学者的价值,从其成材的昂贵付费上看,远非主要之点。
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一种思维方式对于社会、对于人类的影响,是金钱与物质财富无法比拟的。辩证法对于社会进步产生的推动力,恐怕是同时代任何科学发明都是望尘莫及的;相反,形而上学对于社会禁固产生的反作用力,即令“暴君”、“独夫民贼”,恐怕也只能望其项背。
东方世界的产生,概因一种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社会阵营,长达半个多世纪地存在,迄今为止有哪一种物质力量能同其相提并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能有今天,离开了思想与理论必将一事无成。
当影响西方社会的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问世时,几乎是崐同时,东方社会也有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兰格思想——来到人间。凯恩斯主义引起的凯恩斯革命,将政府干预引入经济管理,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放任纳入规范运行轨道,计划机制也为之采用。后来有人将其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大营救”,凯恩斯也随之成为这类社会的第一大社会“名医”。但世人忘记了兰格。这位东方的经济学家当时面对东方社会的弊病,提出了一个与凯恩斯相对应的思想:市场社会主义。他主张必须把商品、价值与市场引入社会主义,建立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如果”这种思想当时能得到与凯恩斯主义相同的待遇,掀起兰格革命,那么历史必将改写,世界又何至于此。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经历了多少是是非非,我们才再来重新发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这笔账无论正面算还是反面算,都证明一个道理:思想理论的力量与价值是无与伦比的。难怪中国的贤人有“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之说。
中国眼皮下的这类例子,多得简直腑拾即是。如果50年代我们采纳了马寅初先生关于人口的思想理论,中国的人口、国民经济水平与居民生活质量都大大高于现在。这岂是几百个亿乃至几千几万个亿能弥补的损失?如果毛泽东当年不用一种乌托邦思想搞出人民公社,如果没有“庐山会议”,又何来“三年灾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不仅可以减少几千个亿的直接经济损失,而且国民经济在世界上的位置也不至于从后往前查。
世间纵然吃不了“后悔药”,但可以有“预防针”。拈量学者的思想理论的价值与份量,就是注射“预防针”。
§章未警言:问问“我”是什么?
我的感触是,每个人先自问:我是什么?是学人,是商人?是双重灵魂撕扯中的“文商人”还是“商文人”?是灵魂变异中的“先商后文人”还是“先文后商人”?是帽子就戴在头上,是鞋就穿在脚上。如果用一块金丝绒去擦鞋,尽管造价颇高,却远不及廉价的擦鞋纸。
注
[1]对这一问题作者另有专文,参见《学者“下海”的交易费用》(《经济体制改革》1993年第3期。
[2]科学家理应包括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然而在人们心目中后者与政治说教者大体相似。究其原因,主要不是人们衡量尺度失真,而是社会科学本身的非科学性造成的。
[3]如果把有些社会科学家的论著观点用编年史的方法展示出来,其御用性和自相矛盾性便跃然纸上。
[4]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26页。
[5]参见(美)L·雷诺兹《微观经济学》第二部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6]参见拙文《别有洞天:以色列乡村公共集体经济》,《经济纵横993年第8期。
[7]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2-58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