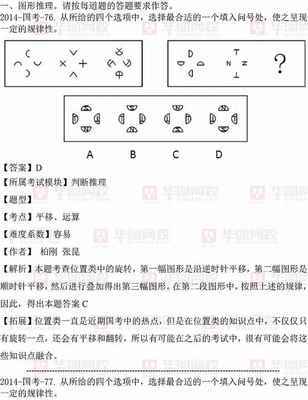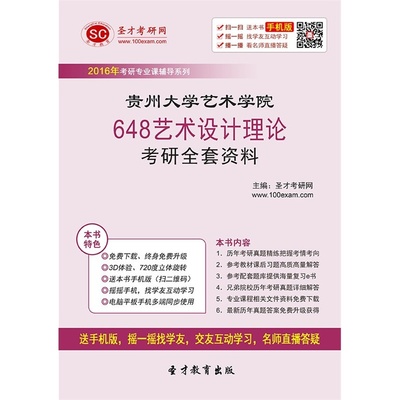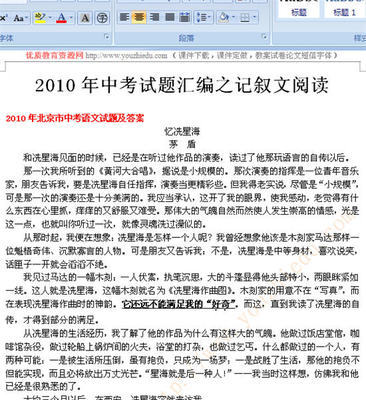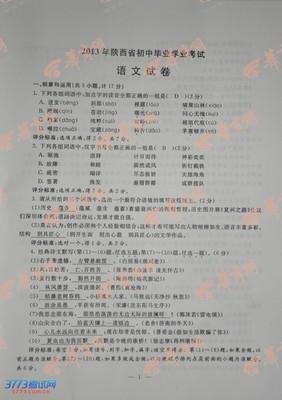微软案的正反双方都认为应该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谁是新经济的胜者和败者。司法部及其支持者只是说微软干扰了市场力量,而微软的支持者争辩市场的力量足够强大,能够阻止任何公司成为支配市场的力量。哈耶克认为,无论是否打击垄断,市场竞争取向的目标不能违背,“除了使法律架构具有鼓励竞争的特点之外,再采取特别措施打击垄断是否必要或可取,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肯定回答,那么古代普遍从法律上禁止相互勾结以限制交易的做法是一个基础……但是由于通常会因此而授予行政机构任意的权力,这同古典自由主义理想并不十分协调。”(《自由主义》)
律政司署反垄断部的助理律师乔·克莱恩认为,反垄断的基本观正是亚当·斯密在两个多世纪以前所描述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带来了经济发展、创造了财富和消费者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政府监管缺位的情况下市场不会总是保持自由竞争的状态。所以,反垄断即是关于企业的市场权力(可以理解,这是每一种经济都需要的)和确保企业能够获得、保持和拓展这种权力的种种限制”。有两个重要的控制装置必须提到。其一,正确的反垄断政策并不认为大就是坏或者成功必须受到惩罚。恰恰相反。在成功来源于技术、远见和勤奋时,消费者权益得到改善。当然在某些时候,反垄断政策的执行看上去似乎与此观点相左。例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分拆被认为是一种恰当的方法,以市场为基础的反垄断分析赞成“大的本质即坏”的哲学。但是这种观点几十年前就过时了,而且几乎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其二,既然我们相信自由竞争的市场使得创新和消费者的权益得以最大化,我们便会倾向于反对管制,这是被普遍认同的解决市场权力指控的有效方式。实际上,正在进行的管制是一种永远都没有效率的反垄断政策,因为它在遏制反竞争行为的同时,也能被抓住机会的对手利用来妨碍正面的市场竞争行为。如此以来,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寻求对于严重的市场竞争问题的结构性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些方案意味着是消费者,而不是政府代理机构或者现存的垄断者将最终决定长期的垄断什么时候能生产出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
克莱恩的观点与1973年哈耶克在《自由主义》一文中所讲极为相似,“要想使自由企业制度发挥造福社会的作用,仅让法律符合过去制订的消极标准是不够的,还必须使它们具有积极的内容,使市场机制可以令人满意地运行。这需要一些具体的规则,使竞争受到保护并尽可能限制垄断状态的发展。”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2000年6月撰文,从解散大公司来看不仅对消费者有利,而且对被肢解的大公司本身也有利。解散后的AT&T事实上仍然在蓬勃发展,未被肢解的IBM的市场份额和市场价值反而在急剧下降。垄断不是加速技术变化的必要条件,被迫拆分AT&T对贝尔系统是一剂良药,在信息革命加速时代,它为该公司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竞争力,为电信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格里高里-曼昆说,政府分拆微软的建议会制造出两个生产互补产品--操作系统与应用系统的公司,一个卖“左鞋”一个卖“右鞋”。过去微软使视窗维持低价是因为它刺激了计算机及其应用程序的销售。同样地,它保持应用程序的低价位是因为这么做带来了对操作系统需求的增加。但是一旦公司被分拆,每个部份都会有提价的动机。司法部声称两个公司最终会开发出新产品并且相互竞争。这种结果其实是很难确定的。一个更好的解决方式是让这两个公司从一开始就生产可替代的产品。每个公司都有权销售自己的视窗版本。其中一个会最后成为市场的主宰者,因为操作系统的市场也许是一种天然的垄断。但是至少竞争会在产业内启动。解决方案是让微软放开源代码。如果视窗由公众掌握,新的公司就能提供各自经过改良的版本。
加里·贝克和凯文·梅菲说,对于“企业和市场结构受哪些经济因素制约”的问题,经济学家其实知道得很少,法官知道的就更少了。他们基本上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这些结构,才会增进而不是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克灵顿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是通过强行实施结构性改组来推行“市场工程”。杰克逊法官对微软案的判决,有诸多令人不安的地方,其中最蛮横无理、最具毁灭性的,就是将微软分拆为两部分的建议。号称反垄断的结构性改组,其实质,就是用“某些经济学家专业证人的判断”和法庭的判决,取代由市场所决定的结果。当具体落实到企图改变一个企业的规模或一个市场的结构时,这种做法就显得格外不妥。
在此,“市场工程”实质是批判哈佛学派结构主义政策,这与哈耶克1952年《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一文对巴黎综合理工学校的批判如出一辙。1794年,法国在大革命时期成立巴黎综合理工学校,由最具恐怖权威的公安委员会为校训一言定鼎,“不要学者,要工程师!”由此,培养了大量科技专家,并形成了主宰社会文明进步的社会工程学、社会几何学,多少精英人物“舍生取义”企图描绘社会蓝图,并强制性地对社会作“活体解剖”。哈耶克在此文中批判了巴黎综合理工学校对社会的副作用:工程技术知识面对的是单一的具体目标,而社会目标却是多元分歧的,而正是这种社会工程学及其政治制度以明确的理性知识压抑了分立的个人知识,以小部落群体中那种受单一目标支配的秩序取代大社会自发的秩序,使人们无法以各个方向上尝试演进,必然压制社会知识的涌流、增长与运用,最终必定扼杀文明社会的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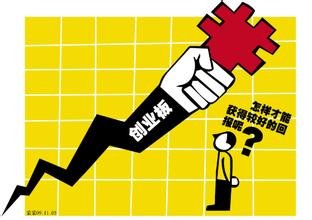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