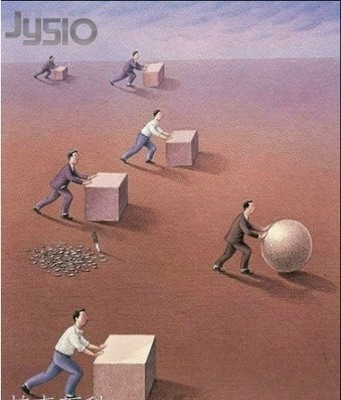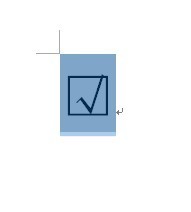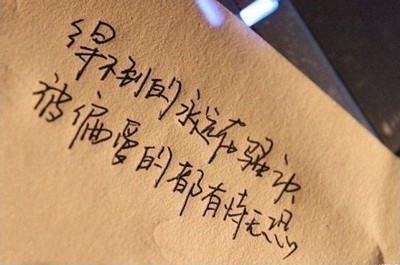郎咸平引发的争论,其涉及的范围和所具有的意义,远远大于“国资流失”这一话题本身,本文认为应该梳理一下主要论者的观点,试图为讨论的深入尽一点微薄之力―― 郎咸平通过对几个改制企业进行财务分析后向社会大声疾呼,国有资产正在大量流失,正在被合法盗窃;他因此呼吁国企停止民营化,并相信通过强化经理人信托责任仍可以把国有制企业搞好。他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对国企的进一步改革,不应该采用产权变革的方式,而应该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途径来实现。 张维迎的回应,应该说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不过就是“要善待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要有学者的独立精神”和“不能媚众”(大致的意思)之类的话,倒是引来一些“屁股、脑袋”之类的回响。笔者以为,在这场比较重要的争论中,主流经济学家们能与各界展开一些对话当属好事,他们没有因“话语权”不同而淡漠或旁观,对推进这场讨论是很有裨益的。因为,大家都看到,这场讨论远远不只是经济学范畴内的事。 相比之下,周其仁的回应更有个性。他逐一就三个案例反驳了郎咸平的诘难,其新制度经济学的修养和造诣跃然纸上;其逻辑的力量、辩论的技巧和语言的功力让人耳目一新;其长期跟踪和调研国企改革状况,也使他讲的东西更容易让人感同身受。在稍后接受新浪网采访时,他更详细地阐述了他对三类国企应该如何采取不同改革措施的看法。在这里,周已经不是只从“效率”的层面谈问题,而是谈到了改革中的“公正”问题。他的这些看法和说法,至少在参与讨论和关心这次讨论的人看来,远比只在“经济学”范畴内讲话要好得多,也客观得多。 中国搞市场经济,至今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这样说不知是否合适?我们运用的都是从西方引进的经济理论。西方几百年从私人企业到家族企业再到股份公司,实现了财产从私人所有到社会占有的一系列变革,什么交易费用呀,财产权利呀,公司治理结构呀,等等,在他们那里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自然的过程。而在我们这里所要面对的,却是与西方相反的过程――我们要对数额巨大的一块属于“公有”的资产重新廓清其“所有”。这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西方经济理论的直接套用会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我们的问题?再比如:有些问题是否只用“效率”的逻辑就能涵盖和解释得了?等等。

所以,周的回答,已经超出了郎的高度。虽然他们都谈到了“公正”,都差不多把讨论的话题界定为“国企改革”,但周的更明确、更深入一些。特别地,远比郎“不反对国有制”的笼统说法清晰和先进(先进一词似乎不确,姑枉用之),这也是本土研究者的优势使然。如果说郎主张国企改革不触及产权而专门借助治理结构的完善,那么周则是主张在分类区别对待的基础上坚持产权改革的方向。 郎咸平讲话以来,关心和讨论此事的人很多很多,我们看不完他们的观点,因而也不可能全面概括从那以来这件事的进程和现况,因为每天甚至每时每刻大家都在发表着自己的看法。但是,对此最权威的、也是本文认为“走得最远的”(最与众不同的),便是秦晖先生。第一,他不是只用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来参与这次讨论,举凡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等等等,他都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并且处处留有余地,所以本文认为他是讨论这个话题比较有发言权者之一;第二,他不是在今天,不是在发生了由郎咸平引起的这次讨论之后才来加入这些话题的,与此类似的话题他早在十多年前就讲过了(当然讲过的人很多很多,但与这次话题极类似的却相对少些,所以说秦先生很有这方面的发言权)。秦的观点涉及到政治体制,政党制度,经济伦理等诸多领域,可以说是研究中国此类问题的独树一帜者。本文思考不深,恐言不及意,甚至误解了别人,或者望文生义,那反倒不利于这场讨论的深入了。还是想想自己究竟“是‘天平’的两头呢,还是‘尺蠖’的两端?让我们先设法走出‘尺蠖’的轨迹,再继续争论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