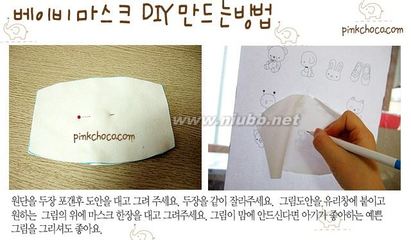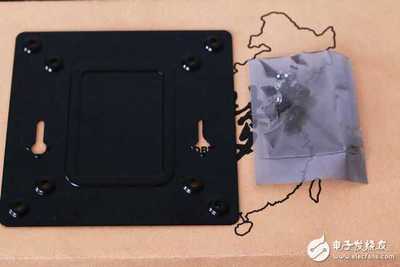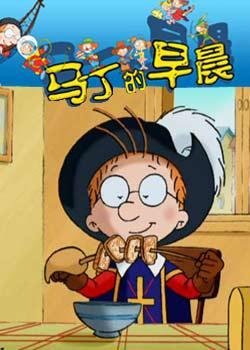欲续22年前缘反遭滑铁卢,骂声一片中,《新编辑部的故事》首播结束: 5月9日,36集电视剧《新编辑部的故事》在北京、东方、深圳三大卫视的播映画上了句号。这部脱胎于1991年经典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的“后续之作”,由原作总策划、《甄嬛传》导演郑晓龙执导,“戈玲”吕丽萍留守演出。 开播之前,《新编辑部的故事》曾被认为是2013年最值得期待的剧目之一。毕竟,22年前,前传《编辑部的故事》曾引发过历时一年、以北京为中心又涵盖全国、涉及意识形态极广的大讨论。然而,播出后的反响让现有主创们无言以对。 前传的前传:从《渴望》说起 1991年9月,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艾知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论述电视剧现状:“一方面,电视剧产量已达到千余部(集),而其中优秀作品太少,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平庸乃至低劣的作品;另一方面,由于近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其他错误思潮的影响,电视剧创作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性问题,再加上引进的大量外国的和我国港台地区的电视剧,其中也确实带进了值得警惕的某些资本主义文化糟粕和精神垃圾。” 此前一年,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录制的“我国第一部大型室内剧”《渴望》,是这个大环境中既得到官方认可,又深受观众由衷喜爱的佼佼者。 先后担任北京青年报副总编辑、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的张永经曾写道:“在诸种复杂的社会心态中,电视剧《渴望》播出了。它写的是‘大环境,小家庭;身边事,儿女情;真善美,双灵魂’。它的时代背景是人人都经历过的‘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十年的重要时期。” 有《渴望》引路,1991年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不仅沿用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为《渴望》因陋就简租用的室内剧摄影基地(香山脚下原八一体工队篮球馆),也延续了《渴望》在电视剧中反映现实的方式方法。电视剧播出后,跟着出版的《编辑部的故事?精彩对白欣赏》一书,披露了编剧们在动笔之前的对话:“不触及社会生活中的热门话题吧,观众不爱看,说深了吧,不定哪句话捅了娄子”;“没有人物命运勾着观众,全靠对话上有彩儿”,“我们把住一大原则,只触及社会问题”;“对,咱们是善意的,把住这一点,就不会被枪毙。” 根据片头署名,《编辑部故事》的总策划是郑晓龙,“策划”是朱晓平、王朔、苏雷、魏人、葛小刚、冯小刚、李晓明七人。其中,王朔、郑晓龙、李晓明是《渴望》的“策划”,李晓明是《渴望》的署名编剧。 张永经说:“这几个人,都亲自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时期,有着较丰富的人生体验”、“在创作初期,他们没有什么固定的框架模式,他们没有想写重大题材、具有深刻哲理的艺术精品;也不想玩大、玩洋、玩深沉。他们只是想到要写当代,写北京当代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和普通感情,写人物的命运和经历。” 《编辑部的故事》:是窗口还是大毒草?

据郑晓龙回忆,当年众策划侃出的40多个“编辑部的故事”,最终选出30个写成了剧本。但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搬家时,这些“良莠不齐”的剧本不慎全部遗失,只得由王朔、冯小刚凭回忆从头写过。 1991年12月,《编辑部的故事》在北京台首播。除了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和台词,观众们也能在剧中找到反思历史、反映当下的切口。譬如《谁主沉浮》一集中,陈主编笑着回忆:“说起被挽救的对象,我们这儿的都有一段痛苦的经历啊。那个时候牛大姐经常写个诗,有一次写了个‘心花怒放’,好,让‘造反派’给逮住了,审问:心花为什么要怒放,替谁怒放?你是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那个批判会,我到今日是记忆犹新啊。” 刘书友接茬说:“当时啊,牛大姐让人剃了一个阴阳头,站在台上,您就站在她旁边。” “四人帮”倒台、三年自然灾害、上山下乡等历史情节,都被编剧先生们融入了《编辑部的故事》。 在《编辑部的故事》中,六位主人公和客串演出的其他角色,均带有强烈的、略显夸张的代表性。当年有时评说:“通过《人间指南》编辑部六位编辑与社会各层面接触的过程,打开了一个了解当代中国人生活和心态的窗口。”仅仅一年间,《编辑部的故事》在全国各省市电视台的总播出(包括重播)次数累计达140多次。“作为一次媒介热潮和一个文化现象,这情景甚至使若干年前的《渴望》、《新星》相形见绌。” 伴随着热播的,是争论的升温。与《渴望》风格、结构全不相同的《编辑部的故事》,并未获得如《渴望》那般一边倒的赞扬。《北京晚报》时设“编辑部大家谈”栏目,十天收到三千多来稿,连续20天内刊发了四十余篇观点截然不同的文章。“有人认为这戏很假,不合情理,难道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的吗?”也有人觉得它太真实,“连灵魂的隐私也统统搬上荧幕,我们反而感到不自在和不习惯”。 作为《编辑部的故事》的推手和“艺术顾问”,张永经说,播出后,有老同学给他打电话,称剧中“有些内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拿政策开玩笑,是一棵大毒草”。由于争议过大,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曾奉命向中共北京市委汇报情况,张永经与冯小刚皆是当事人。在获得了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的点名肯定后,《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长达一年的质疑和争论才算尘埃落定。 1993年,《编辑部的故事》获飞天奖、金鹰奖和“五个一工程”等8项大奖。 《新编辑部的故事》:Out的,太Out的 时隔21年,2012年2月,《新编辑部的故事》在北京开机,依旧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出品,依旧是六位主人公,依旧从《人间指南》编辑部遭遇危机开始讲起,甚至开机时郑晓龙所穿的皮衣款式,都与他在1996年筹备以“编辑部的故事”为基础的贺岁电影《万事如意》时一模一样。 郑晓龙说,他续拍《编辑部的故事》的念头从未断过。继执导《北京人在纽约》与《金婚》后,2011年他的最新代表作《甄嬛传》大热荧幕,甚至登陆了美国主流电视台。随后,郑晓龙着手让《编辑部的故事》重出江湖。 担任《编辑部的故事》总策划时,郑晓龙38岁。执导《新编辑部的故事》时,他已近花甲。20年间,中国社会变化之大,观众口味更新之快,让郑晓龙倍感压力。他选择的解决之道是,让《人间指南》“变身”为《WWW》时尚杂志,让《新编辑部的故事》既“保留语言的幽默”,又一股脑地“将各种各样的喜剧元素都放到这个戏里面”。除了郑晓龙自己所说的“无厘头、黑色幽默、载歌载舞、相声贯口”之外,观众们还能在《新编辑部的故事》中时刻遭遇双簧、戏曲、话剧式独白,跳入跳出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抖包袱。 郑晓龙甚至特意设计了很多“新招”,譬如使用多个摄影机位,随时捕捉不同演员的表情,然后用拼接的方式在荧幕中呈现出来。又比如在每一集(章节)的结尾处,都会出现一个“画外音”与角色对话,再由拳击赛中的Show Girl举着下一集(章节)的片名走到摄影机前。在郑晓龙看来,和瞎编的“雷剧”不同,《新编辑部的故事》“情节都是合理的,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上是有意思的”。一开始并不能适应这种表演方式的演员们,最终选择了相信导演的判断,吕丽萍说:“这一次我觉得确实是,大家都解放了。” 但大多数观众并不买账。4月20日开播后,《新编辑部的故事》主创们随即遭遇第一波压力,主要指责针对“做作的表演”和“落伍的桥段”。 《编辑部的故事》里的“牛大姐”,在《新编辑部的故事》中也有份客串演出,其扮演者童正维的儿子马良,在微博上毫不留情:“《新编辑部的故事》是我最近这些年看过的最差的电视剧。平时家里没有电视看,只看到网上恶评如潮,今天终于得以观赏,简直差得令人发指。前后对照,这部戏恰如其分地展示了20年时间里中国大众文化的堕落。导演一定觉得自己很时髦,觉得自己抓住时代脉搏了,觉得自己把这种毫无价值的泛娱乐化做到极致了。” 针对新旧版中吕丽萍的表演对比,目前网上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戈玲已死,有事烧纸。” 《编辑部的故事》中,李东宝的自嘲让人印象深刻。《新编辑部的故事》中,新一代人物“何澈澈”这样调侃、数落戈玲:“主编是元老,从《人间指南》到《WWW》,她是承前启后的人物,她热爱我们的杂志,把所有的精力全放在了工作上—可有什么用呢?主编,您这么大把年纪了,岁月他不饶人,您的很多挂念,稍微一不留神就out了。可您呢,您偏不认头啊,还惦记着什么与时俱进,你往哪儿进啊,还愣把自己当个潮人,你往哪儿潮啊?” 这段台词,恰恰和不少针对《新编辑部的故事》的网络评论基调相同。郑晓龙的探索与创新,在这些评论者看来,恰恰是“Out、太Out”的表现。 不可否认,郑晓龙很用心,但《新编辑部的故事》与当下社会的疏离感,是和《编辑部故事》的最大区别所在,虽然也将许多热门话题纳入其中,但《新编辑部的故事》总让人有“隔靴搔痒”之感。 5月7日,人民网发表署名李星文的评论文章,他说 “从‘老编’到‘新编’,是从解构到吐槽,从讽刺到审丑,从扎针到挠痒痒,从动口不动手到动肢体也动舌头的全面转型。1991年的中国,思想界、文化界乃至社会各界,均有‘极左残余思想’和保守僵化意识弥漫,《编辑部的故事》以调侃的方式,将正襟危坐的官场话语加以解构,让观众在语言狂欢中获得了快感,也在讥刺丑陋的过程中解了气。而《新编辑部的故事》所处的是一个解构到无可解构的年代。”李星文坦承,“在一地碎片的时代中,向着更加核心和要害的领域去解构,爬剔历史和现实的真相”,其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专访《新编辑部的故事》编剧巩向东:“就是想让大家高兴高兴”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老版《编辑部的故事》? 巩向东:我基本不考虑原来的东西,因为已是过去式了。我们所说的经典,是在特定时代下,放在特定坐标系里产生的意义。我不觉得它高不可攀,谁动一动就是大不敬。 我很尊重原来的创作者。我也想请大家知道,老版从剧本路子到摄制都是郑晓龙把控的,成为经典,他功不可没。请大家不要忽略这个事实:经典的缔造者郑晓龙,为什么要再做一个挨骂的东西呢?我觉得他是不想停滞在过去的状态,在新时期搞一些创新,恰恰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才愿意跟他合作。 我替郑晓龙说句公道话。能够抛开过去的东西,自我突破,这种创作勇气是当前所需要的。 时代周报:你曾说,郑导觉得你写剧本的路子对,他有没有跟你沟通:对在哪里? 巩向东:就最基本的—他看着本子能哈哈大笑。他看过的本子太多了,能让他笑的太少了。这是我们最直接、最朴素的对风格的认同吧。 时代周报:我看了《新编辑部的故事》的出版原稿,和电视剧相比,文字中的气场要更连贯。你怎么看待郑导的二次创作? 巩向东:我觉得郑晓龙是位很成熟的导演,我们也合作了很多,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怀疑。 时代周报:对网络上的批评,你们有过准备吗? 巩向东:我们想到了有争议,但没想到这么大。家人给我转达的,主要是网友批评演员表演“夸张”的问题。当初我跟郑晓龙商量时,觉得走老版只是调侃的路子没意思,放到现在,也未必讨好。我们觉得做点新尝试未尝不可,加入一些夸张成分,比如漫画式的元素,给演员一个彻底的解放,让他们有充分的空间去享受喜剧。这是我们的初衷。但这其中有个度的问题,这个度怎么把握,是见仁见智的。作为演员也好,导演也好,他们做出的努力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这样颠覆自己的勇气我觉得是值得钦佩的。最终效果的话,就见仁见智了。 时代周报:这些尝试,你觉得是超前了呢?还是没赶上观众的拍子? 巩向东:我倒没觉得没赶上,我感觉跟他们没在一个频道上吧(笑)。片子有争议我们都能理解。但现在一些批评的方式,我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创作是一种艺术,批评也是一种艺术。 时代周报:有人批评说,《www》杂志社窗外的景色是将上海、英国、迪拜等地景色混在一起。 巩向东:批评者说导演就是个大傻帽。这种批评我是不能理解的。我希望他去想想,为什么创作者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窗外景色用了很多特技,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财力。我们用心做这个的目的就是想告诉大家,这是个非写实剧,就是要制造些“间离效果”,但总体效果似乎不让大家满意。 时代周报:这种“间离效果”是你和郑导在《新编辑部的故事》中所追求的吗? 巩向东:有些东西我们都是有意为之的,也是一种尝试吧。但很可惜,有些效果不好。 时代周报:在“度”的把握上出了些问题。 巩向东:对。有人批评说我的桥段follow网络,我其实是个很out的人,对网络很排斥。我的剧本几十万字,靠几个网络用语能撑得起来吗?讨论剧本时,有的演员极力向我推荐网络段子、用语,我是非常不感冒。因为我的剧本有自成一体的叙述语言和风格。 时代周报:关于新版“不够深刻”的批评,你怎么看待? 巩向东:我们没这能力,也不想给影视剧加那么沉重的担子,我们就是想让大家高兴高兴。最初我们就想,入木三厘、微言小义就OK。入木十分,也不允许啊。这个剧直至播出前,还在因为审查的原因在修改,一些话题我们其实都在绕着走。有人说我们没有针砭时弊,怎么针砭呢?大家理解下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