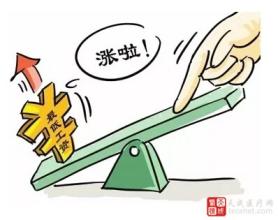内容提要: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既不是没有关系,也不是简单的成正比或成反比或是先升后降的关系。其具体关系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既存在提升国民幸福水平的因素,也存在减少国民幸福的因素,同时,除经济增长以外的其它许多因素也对国民幸福有重要影响。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最终取决于诸因素的合力。当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时,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就是一种正比例关系。当负向作用大于正向作用时,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比例关系。同时,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会随时间而变化,所以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在不同的时间段会表现出不同的趋势特征。另外,国民幸福对经济增长也有反作用。国民幸福的增加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国民幸福的下降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不利影响和负作用。关键词: 经济增长 幸福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甘肃靖远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现为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和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经济理论和乡村发展及中国经济改革等方面。在《光明日报》、《农业经济问题》、《战略与管理》、《中国农村观察》、《经济学家》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150多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专著5部。什么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产出的增加。什么是幸福?从经济学角度看,幸福就是效用的满足或快乐的增加或满意度的提高。经济增长与幸福有什么关系,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1.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水平成正比例。这是人们的一般认识,在现代经济学的标准理论中也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人们的解释是,经济增长增加了产出,从而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这也就增加了效用和快乐。另外,来自部分国家的实证研究报告也一定程度证实了这一结论。“证据有力显示,个人满意度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发展而提高。”(Inkeles and Diamond,1986,p.94)。(参见S.弗雷等著《幸福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82页)2.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人们的幸福度并没有增加,而是有所下降,即当国家变得更富有时,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由于经济学家Easterlin最早研究这一现象,所以这种幸福与收入相悖的现象又被称作Easterlin悖论。对Easterlin悖论的解释主要有三种理论。第一种是“忽视变量”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不仅收入影响人们的效用水平,而且非收入因素,例如健康状况、婚姻质量、就业状态等,也影响人们的幸福。第二种是相对收入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人的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是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也会随之提高,从而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 。人们也称这种解释为参照组理论(reference group thoery)或攀比理论。第三种是前两种理论的综合。黄有光等学者通过建立一个代表性消费者模型,解释了经济增长减少福利水平的可能性。在这类模型中,福利水平的降低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生产产生的环境污染以及相对收入效应。这种解释既包括了非收入因素的影响,也包括了相对收入的影响。在实证研究层面,与经济增长提高国民幸福度一样,Easterlin悖论也在许多国家得到验证,如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很多发达国家都得到验证;同时,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也存在这一现象。3.经济增长与幸福是一种先升后降的关系。田国强、杨立岩在《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经济研究》2006.11)一文中就持这种观点。该文章的结论是: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文中并没有给出实质解释。4.经济增长与幸福没有关系。弗兰克在他的《奢华热》(Luxury Fever,1999)中强调:持续增加的收入和消费与幸福之间没有关系。Carol Graham (2005,p.4)在有关研究中指出:“跨国和跨时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平均幸福水平几乎不相关或即使相关也很小。”(参见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经济研究》2006年11期。)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幸福水平是由遗传和性格决定的,从而任何提高幸福水平的个人或社会行动都是无效的。aihuau.com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某一种观点只是反映了经济增长与幸福在某一时段或某一局部所体现出的关系,或只是反映了二者关系的某一个侧面,而不是全部。应当从总体的角度把握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既不是没有关系,也不是简单的成正比或成反比或是先升后降的关系。其具体关系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既存在提升国民幸福水平的因素,也存在减少国民幸福的因素,同时,除经济增长以外的其它许多因素也对国民幸福有重要影响。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最终取决于诸因素的合力。当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时,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就是一种正比例关系。当负向作用大于正向作用时,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比例关系。同时,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会随时间而变化,所以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在不同的时间段会表现出不同的趋势特征。另外,国民幸福对经济增长也有反作用。国民幸福的增加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国民幸福的下降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不利影响和负作用。经济增长是决定国民幸福的重要条件,经济增长对国民幸福的影响是双向和多方面的。首先,经济增长能提高一部分人的收入,从而将有利于提高这部分人的幸福水平。但相反的作用也存在。一是由于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以来自收入增加的边际效用应当有一个递减的趋势,从而会有可能导致幸福度的提高比例小于收入提高的比例。二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时来自非收入因素的边际效用会表现出递增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边际替代规律的作用。田国强等人的研究结果可能就是这一现象的反映。当人们的收入水平较低时,这时来自收入水平提高的效用较大,而来自非收入水平因素改善的效用较小,所以,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对幸福水平的提高产生较大影响。但当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来自收入的边际效用将小于来自非收入因素的边际效用,这时增加收入水平对幸福水平的提高就不会产生较大影响。三是收入分配不均衡的影响。经济增长并不能保证所有人的收入都能得到提高或较大提高,有些人的收入也有可能保持不变或减少。减少收入会减少一个人的幸福水平。收入没有提高或提高的幅度达不到社会平均水平的,其幸福水平也有可能会减少或不增加。其次,经济增长通过就业对国民幸福水平的影响也是双向的。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结构的调整和产出的增加,这对促进一部分人就业是一个有利的因素,从而也有利于提高这一部分人的幸福水平。但对一些夕阳产业而言,情况并非如此,若国家不能对这些产业的工人采取有效保障措施,这些人的失业将会降低国民的幸福水平。当然,失业者也有一种享受闲暇的正效应,但这种正效应总体上是十分小的。一些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研究结果表明:失业会对国民幸福产生重大影响。(参见S.弗雷等著《幸福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110页)克拉克和奥斯瓦德在针对英国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失业对福祉的影响程度超过其他任何因素,包括诸如离婚和分居等重要的消极因素。”克皮尔针对瑞士研究的结论也是:失业对福祉有一种非常明确的消极效应。失业既减少了收入,也使人感到压抑和焦虑,从而导致自尊的丧失。所以,失业不仅会降低一个人来自收入方面的效用,而且也会降低一个人在非收入方面的效用。当然,如果一个社会的失业呈普遍化,并且人们对失业现象已习惯化,这时失业所产生的负作用可能会有所减轻。第三,经济增长会影响到通货的稳定,从而会对国民幸福产生一定影响。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本身并不会真正影响人们的生活,即便产生影响,至多也是未预见的价格升高所产生的影响。但有关幸福方面的研究更多的结论是:通货膨胀对人们的幸福水平有着明显的影响,不管它是预期的还是不可预期的。不管是对穷人,还是对富人,通货膨胀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这里影响的程度也取决于通货膨胀的程度。通货膨胀程度严重,其影响就严重;通货膨胀程度轻,其影响也轻。通货膨胀对社会运行产生的成本主要有:一是增加了消费者的“皮鞋费”或“往返银行费”;二是增加了生产者需不断改变价格的“菜单成本”;三是增大了不确定性,增加了人们的预期成本和心理成本;四是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五是由于价格信息失真,增大了资源配置的扭曲成本。这些成本的增加最终都会对国民幸福产生许多不利影响。第四,经济增长会深化社会分工,而分工对国民幸福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分工的深化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提供给人们满足消费的产品会更多,这将有助于提高国民的幸福水平。另一方面,分工的深化对国民幸福的增加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一是分工增加了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二是分工深化增加了人们的学习成本。对一个社会而言,人力资源的流动性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分工的细化限制了这一流动性。为了就业和个人发展的需要,人们将不得不进行不断的学习,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是分工增加了投资成本。四是随着分工的深化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商品会越来越丰裕,而商品丰裕会增加人们在选择方面的成本支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商品数量与品种的增加,这时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将会增大,从而人们选择的不确定性也将会增加,这将直接增加人们选择的心理成本;还有,搜寻信息也需要比以前付出更多时间和货币等客观成本。另一方面,随着商品数量与品种的增加,人们选择的机会成本会变大。所谓机会成本,就是指人们在选择某一行为时,所丧失的其它方面的机会。当商品的品种和数量较少时,人们在消费某一商品时,所丧失的机会也较少;当商品的品种和数量较多时,人们在消费某一商品时,所丧失的机会也较多。五是分工会增加人们的精神成本。分工造成了一种人格的片面化和机械化,从而增加了人的一种孤独感与枯燥感。六是分工对幸福水平的影响与分工的发展程度是密切相关的。当社会分工还不发达时,这时分工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分工的深化有利于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但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分工的副作用会越来越大。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写道:在分工的不发达阶段,“分工带来的副作用还离我们太远,以至于我们无法理解和意识到这些副作用的存在。无论如何,只有在分工得到充分发展以后,这种副作用才会显现出来。”(参见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189页,三联书店2004年4月北京第1版)目前,社会分工已达到很高阶段,但仍在不断深化和发展。主要原因是制度创新所产生的正向作用部分抵消了分工深化所产生的负作用,从而使分工在总体收益上表现为正收益大于负收益,促使分工不断深化和发展。除了经济增长外,还有许多影响国民幸福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与经济增长共同决定了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程度。首先,制度是影响国民幸福水平的一个重要变量。一是公平的制度体系对提高国民幸福水平会产生积极影响,不公平的制度体系对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会产生消极影响。不公平的制度体系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绝对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会更多影响到一个人相对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民众具有广泛参与权的制度对国民幸福具有积极影响。有关研究证据显示,参与权指数对幸福具有一种统计显著性的积极影响。参与权指数每增加一单位,平均满意度就会增加0.11个单位,报告非常高的生活满意度的人数比例就会增加2.8个百分点。(参见S.弗雷等著《幸福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159页)三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有助于提高国民的幸福水平。因为健全的保障制度既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物质上的保障,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其次,文化也是影响国民幸福的一个重要变量。人既生产文化,文化也生产人。在某种意义上看,人就是一个行走的文化体。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态度。由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环境,所以不同国家的人就会有不同的幸福观。知足常乐的价值观是提高幸福度的积极因素,而无穷的贪欲只会导致更多的痛苦。另外,严重的平均主义心态与嫉妒心态也是幸福的天然杀手。再次,人口比例的变化对国民幸福也会产生影响。一是不同年龄人口比例。一些经济学家发现年龄与幸福之间是一个U型关系,也就是年轻人和老年人比中年人更幸福。此结论是否准确尚待进一步探讨,但随着年龄的变化,人们的幸福观肯定是在变的。二是性别比例与种族比例构成。有关研究表明,人口中性别构成、种族构成都会对国民整体幸福水平的提高有一定影响。例如,有些经济学家研究幸福时发现,妇女所报告的幸福水平要比男人高一些;黑人不如白人幸福等等。三是疾病人口比例的变化。由于幸福与健康有紧密联系,所以,疾病人口比例的上升会直接导致国民幸福水平的下降。四是婚姻人口比例的变化。亚里士多德将人视为“群居动物”(social animal)以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拥有一种长久亲密的关系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目标之一。拥有朋友、伙伴、亲戚、以及某个团体的组成部分都会对一个人的幸福有所贡献。亲密关系的意义就在于使人具有了一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亲密关系不仅一定程度满足了一个人的精神需求,也具有增加一个人物质收益的重要功能。同时来自不同国家和时间的实证研究与调查也显示,婚姻确实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如Diener等人的著作2000年)(参见S.弗雷等著《幸福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159页)。但存在的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些研究也表明,虽然单身男人和单身女人没有那些已婚夫妇幸福,但差距有缩小趋势,这可能受到其它一些因素的影响。五是受教育人口的比例变化。良好的教育背景未必就是幸福的保证,但良好的教育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与应付生活,因而可以提高满意度。第四,环境因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既有利于身体健康,也有利于心理健康。反之,则反之。第五,社会转型因素。一是转型会导致秩序稀缺;二是转型会导致价值迷失。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会对人们的幸福水平产生重要影响。第六,个人因素。个人幸福不仅取决于外在条件,也取决于内在偏好。偏好既是实现幸福的阶梯,也是走向痛苦的门槛。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最终取决于上述诸因素的合力。当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时,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就是一种正比例关系。当负向作用大于正向作用时,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比例关系。同时,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会随时间而变化,所以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在不同的时间段会表现出不同的趋势特征。另外,国民幸福水平也会对经济增长及其它影响因素产生一定反作用。因为幸福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效率,从而也对经济增长有利。同时,幸福水平的提高,对婚姻的美满、身体的健康、社会的秩序等方面都会产生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所以,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水平具有一定的双向互动性。一方面,经济增长与诸多因素共同决定幸福水平;另一方面,国民幸福水平对经济增长等因素具有一定反作用。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应当是提高国民幸福水平;同时,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也是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条件。所以,提高国民幸福水平,不仅具有终极目的意义,也具有重要的手段意义。第一,国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在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要对社会建设给予更多关注。目前,我国政府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等都是这一战略的具体表现,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第二,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要协同推进。同时,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国家要更加关注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第三,制度建设要立足于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公平是基础,效率是主导。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公平与效率应当有不同的侧重。第四,要适时适地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第五,要坚持科学发展,重视环境和生态建设。第六,以人为本,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第七,大力发展教育。第八,建立更加公开和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体系。第九,保持好社会的稳定。第十,立足于国民幸福度,积极构建和推广更加合理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参考文献:

1.S.弗雷等著,静也译:《幸福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2.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2004年4月北京第1版。3.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经济研究》2006年11期。4.刑占军著:《测量幸福》,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5.弗格森著,徐志跃译:《幸福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作者: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通讯地址: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邮编:730070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