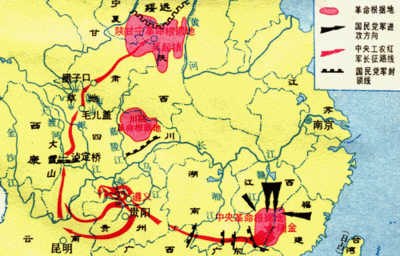“前几日,我听说你丈夫带着两个风尘女子,在万年桥下的舟中畅饮。你知道这事吗?”
“哈哈哈哈。的确是有这件事啊,其中一个女子就是我!”
……
对话中,涉嫌“不检点”的男子名叫沈三白,名复,苏州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36年),年轻时秉承父业,游幕经商,其家境小康,不愁吃穿。更幸运的是,在他的一生中,遇到了一个令林语堂都艳羡不已的女子芸,“芸娘是中国历史和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林语堂语)。
芸,本姓陈,字淑珍,为沈三白舅舅家的女儿,年龄长于沈三白。或出于早熟,在随母亲归宁时,沈三白向母亲直言道:“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沈母亦很果断,当即脱金约指缔姻焉。
沈三白的命运,由此被改写。这是因为,娶得一个如此可爱的女子后,促使他写下了洋洋洒洒的几篇“小小文章”——“浮生六记”。而恰恰是这些可爱的文字,竟让后人永久性地记住了他,并被冠以了“清代文人”的美名。
那是清光绪三年(1877年)的一天,在苏州护龙街旧书大集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人突然抱着一本破烂不堪的日记本,大喜起来,仿若于万千人群中觅一知己!这个疯疯癫癫的人,叫杨引传,自称“独悟庵居士”。他所搜罗到的破烂手稿,就是上文所述沈三白写下的“不朽文章”。
我认为,他应该算作优秀的出版人了,虽然他并不从事出版工作。因为发觉这些文字实在无敌般可爱,闺房记乐,乐而不淫;坎坷记愁,愁而不怨;审美视角独特,文笔轻清秀丽……杨引传便想到了自己的妹夫——在上海申报馆工作的王紫钰。之后,沈三白的旧手稿被编进了杨引传的《独悟庵丛钞》。
这是残本“浮生六记”(仅前“四记”)的首次出版。后来,受“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个性解放”之五四精神的感召,以俞平伯为首的众多新文学青年,以更博大的胸怀,重新认识、解读并传扬了“浮生六记”。
之后,林语堂、潘光旦等人,相继成为“沈三白门下走狗”,均对“浮生六记”赞誉有佳。
我第一次读“浮生六记”,是崇文书局版的《闲书四种》(宋凝编著)。除“浮生六记”外,另有“三种”则分别是:冒襄的《影梅庵忆语》、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蒋坦的《秋灯琐忆》。这不,前不久,我又刚刚阅读一遍,仍时常为文中所记琐事或乐或悲,感慨良久。
“……离余家中里许,醋库巷有洞庭君祠,俗呼水仙庙。回廊曲折,小有园亭.每逢神诞,众姓各认一落,密悬一式之玻璃灯,中设宝座,旁列瓶几,插花陈设,以较胜负。日惟演戏,夜则参差高下,插烛于瓶花间,名曰‘花照’。花光好影,宝鼎香浮,若龙宫夜宴。司事者或笙箫歌唱,或煮茗清谈,观者如蚁集,檐下皆设栏为限。余为众友邀去插花布置,因得躬逢其盛。归家向芸艳称之,芸曰:‘惜妾非男子,不能往。’余曰:‘冠我冠,衣我衣,亦化女为男之法也。’于是易鬓为辫,添扫蛾眉;加余冠,微露两鬃,尚可掩饰;服余衣,长一寸又半;于腰间折而缝之,外加马褂。芸曰:‘脚下将奈何?’余曰:‘坊间有蝴蝶履,大小由之,购亦极易,且早晚可代撤鞋之用,不亦善乎?’芸欣然。
“及晚餐后,装束既毕,效男子拱手阔步者良久,忽变卦曰:‘妾不去矣,为人识出既不便,堂上闻之又不可。’余怂恿曰:‘庙中司事者谁不知我,即识出亦不过付之一笑耳。吾母现在九妹丈家,密去密来,焉得知之。’芸揽镜自照,狂笑不已。余强挽之,悄然径去,遍游庙中,无识出为女子者。或问何人,以表弟对,拱手而已。最后至一处,有少妇幼女坐于所设宝座后,乃杨姓司事者之眷属也。芸忽趋彼通款曲,身一侧,而不觉一按少妇之肩,旁有婢媪怒而起曰:‘何物狂生,不法乃尔!’余试为措词掩饰,芸见势恶,即脱帽翘足示之曰:‘我亦女子耳。’……”

呵呵。想想,有这样的女子在旁,多美!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