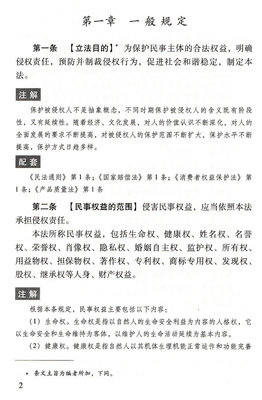1986年10月,香港《Playboy》杂志采访李敖时,有这么两句对话。 Playboy:谈了那么多政治,还是谈回你个人,“未来的李敖”有什么大计? 李敖:我的未来不出写大书的范畴,我要完成《中国思想史》、《北京法源寺》等世界名著的写作。 1991年6月,李敖在“我写北京法源寺”一文中写道:“《北京法源寺》作为书名,是17年前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在国民党黑狱中决定的。”关于《北京法源寺》的写作情况,他这样写道: “1976年我出狱,在料理劫后之余,开始断断续续写了前几章……这十二年间,几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写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误了。十二年中,只断续写了万把字,始终没法完成。 “耽误的原因其实不全在时间不够,而是我心理上的一个求全故障。伏尔泰(Votaire)说过一句话:‘最好是好的敌人。’(Le mieux est I’ennemi du bien. The best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正因为我要写得‘最好’,结果连‘好’都踌蹰下笔了。 “……因此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写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去年年底,快速完成了它。艾维林渥(Eevelyn Waugh)说一部长篇小说需要六个星期才能完稿,我这部书,恰如其说。由于它只是我史诗式小说中的一部,我自不打算用一部小说涵盖所有的主题,所以,它涵盖的,只在400个子题以内,但内容也很惊人了。”
按李敖自己在文中的评价,“《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群已、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经世济民)等等,都在论述之列。这种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内容丰富自是罕见。”
也许意识到了小说中某些“出格”之处,在文中李敖对“小说理论”又来了一番“大清洗”。 “《北京法源寺》在小说理论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视过去的小说理论,也不重视现代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要成为‘清宫秘史’式的无聊小说、也不愿成为新潮派的技巧小说,所以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该赶快‘过桥’的,也就不多费笔墨;该大力发挥的,也不避萧伯纳(G.B.Show)剧本《一人演说》之谶。 “正宗小说起于十八世纪,红于十九世纪,对二十世纪的小说家来说,本已太迟。艾略特(T.S.Eliot)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Flaubert)和詹姆士(Henry James)之后已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代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像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正因为如此,我相信除非小说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它将殊少前途。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很难挽回小说的颓局。”2000年1月底,有消息说李敖已经获得诺贝尔奖提名,而他的《北京法源寺》也正由专人译成英文。李敖与《北京法源寺》再一次成为热点。
在这本书出版以后,李敖自己对它的评价不多,文化和思想界也罕有评论。反而是他老对头的后代,李敖后来的朋友——时任东吴大学校长的章孝慈看完后,给了一句有趣的评价:“《北京法源寺》写得真好!真是一本才子之书,李敖真是有才气。”(《李敖回忆录》)○历史记录与思想自传
李敖自承《北京法源寺》是一本历史小说。然而就小说而言却很难给它定位:书中所写的历史事实大多经过严密的考证与梳理(这一点在李敖的“我与《北京法源寺》一文中已有说明),然而在不同人物的思想与对话中却更多地体现了李敖自己的见解,这恰恰是全书中最精彩、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李敖自己对此并不讳言,在《<蒋介石评传>序》中,他这样写道:“40岁生日前夜,我在牢房里,躺在蜈蚣与白蚁出没的地板上,构思我的小说——《北京法源寺》,就想到小说中的主角康有为,正该影射我自己;而另一主角西太后,正该影射蒋介石……”
然而在真正写作时,李敖的注意力却更多地被另一个人物——谭嗣同吸引了过去。许以祺在《钟声无恙我将归——李敖二度出狱有感》一文中写道:
“1980年再去看他时,他说他正在写有关谭嗣同的历史长篇。他滔滔不绝地讲谭的满腔热血,他的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胸怀,以及谭的文学造诣。戊戌政变失败后,谭不愿逃走,宁可以死酬国,在菜市口被清廷斩首时毫不畏惧从容就义。李敖当时讲得很激动。这种事本来说是使人感动的,但对李敖,却不止于此。你会觉得他是在身体力行……”

毫无疑问这里所写的正是《北京法源寺》中的华彩章谭嗣同就义一段。
正是这种写作时间上的拖延与急就、写作过程中的角色投入与转换和写作目的的宽泛与集中造就了《北京法源寺》这一奇特的文本形态:就小说而言,李敖自己解释说是有意的“破格”,但更多的,实际上是保存了作者在写作小说时的原始心境和情态。
正因为如此,要研究李敖,就不能不研究《北京法源寺》,尤其是其中许多看似枯燥无聊,实则呕心沥血的长篇对话(即李敖所谓“不避《一人演说》之谶”者)。
与此相应的,则是李敖凭借其深厚的史学素养所钩沉出的种种清末史料与史实,足以为研究维新变法史的学者提供一段有益的历史资源——在一次接受访谈时,李敖曾自信地说自己的文章剔除了情绪之后全都是经得起考证的资料与史实,而自己在这两方面的运用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意如此)。
《北京法源寺》恰恰是这种“情绪+史料”文学观的一个鲜明例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北京法源寺》的核心可以用“历史记录”与“思想自传”两个概念来加以归纳。
○《北京法源寺》是一部怎样的小说?
就“小说理论”中的“类型学”而言,《北京法源寺》大概介于影射小说、历史小说与思想小说之间(当然这个类型的名单还可以拉长,却没什么用处)。
但就一位读者最简单的直觉判断来说,《北京法源寺》大概还算不上一部第一流的“小说”(也许可以算得上一流的作品)。好小说的标志,按王小波的说法,首先要“好看”——在艰难的读完两遍之后,我不得不承认,这部小说确实不好看。
即便我那么喜欢李敖、即便我也对小说中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有着深厚的兴趣,我还是要硬着头皮才能把它看下去——当看小说从享受变成一种“折磨”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是一本好小说。
不好的感觉包括几点:
一、人物僵化,首先,我对小说中史料的真实性既不怀疑,也不关心;其次,小说中不同的角色,不论男女、无分中外(当然指“正面角色”,慈禧之流不算),无论说话、行动还是思维,怎么看怎么象李敖自己在表演。这就很可怕了,一部好小说就象一个小世界一样,其深度与趣味性正在于情节与性格的丰富与差异,而《北京法源寺》的情节,丰富则丰富耳,只是怎么看怎么象一台一个人表演的木偶剧,看久了实在难免有无聊之感。二、历史逻辑、性格逻辑与思想逻辑的脱节。换句话说,就是在小说里,人物的思想、行动缺乏场景、经历与情节的烘托酝酿,变成一堆“圣人”在各个历史的重大关头发表一套又一套长篇大论的“人生哲理”与“救世宏论”。宏论固然不乏精彩之处,但脱离了小说本该营造出的“虚拟现实”,就变成一篇篇支离破碎的“论文”,对于一个抱着“看小说”期望而来的读者,实在无异于一场苦役。
三、 “史情”与“人情”味的缺乏。作为一篇历史小说,作者除了史学家所应具有的“史识”、“史德”、“史才”之外,还应具备小说家的一项本能,那就是“情”,而在历史小说里,这种情表现为“史情”与“人情”。“史情”者,陈寅恪所谓史学家应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实抱一种“深刻同情之理解”;“人情”者,对于具体人物在具体场景下的历史选择能够从人性的深度上加与描述与展现。坦率地说,在李敖的笔下,我除了看到对有限的一两个人(如谭嗣同、康有为)能够做到这一深度之外,对于更多的人物(尤其是“反派角色”)仅仅是脸谱化的勾勒。这使得《北京法源寺》就象弗洛姆笔下的“单面人”一样,变成了一部“单向度”和“扁平化”的小说。
四、才识过盛,而掩却了小说本来的形态与功能。古人谈作诗,“以才识入诗”被认为难入上品,对写小说而言,这大概也是一个有益的教训。李敖自身的才华、学养与见识早有公论,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充分体现了出来,然而恰恰在“小说”这一门类中,“才识”变成了阅读的障碍——那么多详实(过于详实)的史料、那么多精彩(甚至喧宾夺主)的见解,在小说中形成一段又一段难以逾越的屏障,让读者一次次在阅读时“心理加速“的快感中碰得头破血流,直至丧失了阅读勇气与兴趣——章孝兹所谓的“才子之书”,在此恐怕并非毫无保留的赞扬……
这还仅就“传统小说”理论而言,至于现代小说,李敖先生既不愿写“新潮派的技巧小说”,自也无庸挠舌……
不是好小说,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不是好的作品,在这里我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少次被作品中紧张激烈的思想交锋与思想对话所深深吸引——吸引我的不是小说文字本身,而是李敖自己思想的深度与力度。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