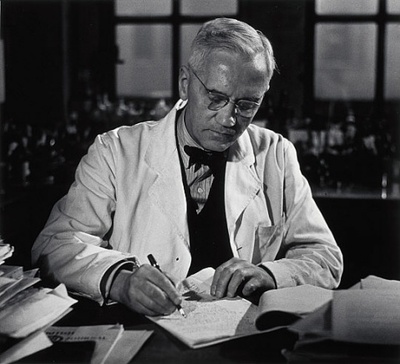——《借我一生》读后
某日出差,回到家时已经近深夜。随手从书架上新买的书中抽出一本,本想翻两页便睡觉。谁知越读越精神,等一口气读完时,窗外的天色已蒙蒙透出曙光。
这本书就是余秋雨先生的新著,他称之为“记忆文学”的自传体小说《借我一生》。
跟许多人一样,我也曾经是余先生散文作品的忠实读者,也曾为其在90年代后期作品与人生上的选择而迷惑,甚至失落。因此在初读余先生的这部精心之作时,其心情也正如一位朋友所写的那样,“是找回了一份失落已久的心情。”
在初遇的惊喜之后,我却渐渐领受到另一种新鲜而陌生的感受:过去那个在《文化苦旅》与《山居笔记》中视野恢宏的叙述者,正被另一个更加清晰,也更加鲜活的个体生命所取代——从这个角度而言,余秋雨先生的这部“记忆文学”,似乎可以看作他以自身的生命记忆对过去所有作品的一个“总阐释”。
通过余先生的回忆,我们得以对其在一系列文化散文中所表达的思索理路进行一次梳理:少年时代的经历(如为邻居写信而受到尊重)培养了他对文化的亲近与信任;文革时期的遭遇与观察令他对“文化废墟”的前景产生了深深忧虑(值得注意的是,“废墟”这一形象在余秋雨的一系列作品中有着独特的意义);在奉化及其后苦读的阶段里,他通过传统典籍的广泛涉猎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信念;在艺术理论阐释与创作的过程中,他领悟了“结构”对于文学乃至文化的重要性;在担任行政领导的过程中,开启了对“几百年来中国文化低效化”的反思;而在独自上路的旅程里,发现了以“对话”重新塑造和建构一种民族文化体系的可能;此后的旅程与创作,则是对于他这一文化思路的亲身实践……
无可否认,这种文化价值上的选择,同样也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放弃”与缺失,这种缺失甚至直接影响到余先生著作中文化言说的底蕴。比如我注意到,余先生的作品里,很少出现对“个人权利”及“个体价值”的探讨,至多涉及一种集体文化背景下的“个人担当”,而对于个体权利的界定与尊重,恰恰是西方现代文明与社会结构的基础。不深入反思这一点,很可能就会陷入“历史与历史的对话”,而缺乏与现代文明与生存状态的沟通——对话也因此而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看到过的一则资料,《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最初听余秋雨聊(本书的构想)时,特别激动。
“余秋雨萌生写这本书的念头,是因为在父亲逝世后,整理父亲的遗物和笔记时发现,父亲其实有着自己非常不熟悉的一面。每个人都有着即使自己最亲近的人也不一定了解的思想和回忆。这使他决定尝试着以一种记忆的方式写作一部作品。”
程永新说,当时他一听这个构思,感觉这个想法特别有意思,生活中亲近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朋友以及历史人物呢。余秋雨对真实提出了一个疑问,那就是什么是真实的?你以为真实的东西,其实离真实有很大的距离,这其中包含一个很丰富的哲学内涵。而在读了一二卷之后,程永新感觉“其精彩程度并未超过我的想象”。
当我读到全书第五卷的第二章时,我觉得感觉到了程先生希望读到的是什么——那是一个人以自己的生命对一个喧嚣时代的“独白”,一种个体存在对“整体真实”拒绝与反讽——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余先生多年思索所形成的文化态度与言说方式变成了叙述最大的障碍。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与余先生有着相似经历的王元化先生的一段反思,恰恰可以做余先生这篇短短“故事”的最佳旁注。
王先生在谈到一个社会中,“集体意志”(即公意)对个体的伤害时,写道:“公意被解释作比每个社会成员本身更准确无误地体现了他们应有却并未认识到的权利,公意需要化身,需要权威,需要造就出一个在政治道德上完满无缺的奇里斯玛式的人物。不幸的事实是,这种比人民更懂得人民自身需求的公意,乃是一个假像,一场虚幻。其实质不过是悍然剥夺了个体性与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以公意这一堂皇名义出现的国家机器,可以肆意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对每个社会成员进行无孔不入的干预。一旦泯灭了个体性,抽象了有血有肉的社会,每个社会成员就得为它付出自己的全部自由为代价。民间社会没有了独立的空间,一切生命也就被窒息了……”
在余先生“文化对话”的宏大构架之侧,王元化先生通过多年痛苦的反思和深厚的哲学素养打通了一条时代与文化沟通的桥梁——只有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才能从自身当下的存在出发,开始一场与历史、与文明真正的对话!
但这决不是因此而对余先生进行“腹诽”乃至“笔伐”的理由——只有亲身经历过那场文化灾难的人,才能理解整整一代(甚至数代)知识份对一片劫后余灰的文化废墟时的悲痛与无奈;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文明覆灭的切身之痛,才会催发出那么急切而焦灼的重建激情。
在我看来,余秋雨的文化追求与“文化野心”,正在于通过一次次的旅行与对话,搭建起一个越来越大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时代与文明,包括他自身的存在都能够得到明晰的表达——而这一点,正是自80年代初“文化热”以来,许多知识份子思索与写作的初衷,而他们中的相当一部份,缺少的恰恰是余先生这份对于信念的坚守。
有论者认为,秋雨散文的价值,在于其“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由于教育体制对人文知识轻视和有意无意的曲解给人们造成的知识缺陷,同时对历史文化问题的散文化解说也打通了学术与普通受众的桥梁。”并因此而断定,余秋雨顶多是个“成绩卓著的普及型作家”。
倘若抛开个人的信念与理想,仅以成败论英雄,那么还不如直接称余先生为“畅销书作家”,在市场经济深入人心的今天,这一称谓反而更切近其“市场价值”。
但抽去了文化信念这一精神骨骼后,余秋雨就不再是真正的余秋雨了。
当年陈寅恪先生所撰王观堂碑铭之结语曰:“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正是对这种文化精神的最好表赞。
当我试图从这一角度,通过《借我一生》的回忆来追溯余秋雨的人生历程时,竟吃惊地发现,原来自己过去心目中的余秋雨形象,竟然遗漏了一块重要的领域:那就是他的“行”。
是的,过去我心目中的余秋雨,是《文化苦旅》中那个激情扬溢的叙述者;是《山居笔记》里那个掸精竭虑的思索者;甚至是电视屏幕上那个温文尔雅的评论者和卫星频道下那个一脸疲倦的旅行者。
但那是只余先生的“形”,无论是文字还是图像。在这本书中我才发现,原来余先生还有那么多的“另一面”,在我所不知道的时代和不知道的地方,他原来还曾是一个“以苦为乐”的劳动者;一名自我放逐的“流亡者”;一位硕果累累的文艺理论家和前途无量的行政领导者……
有谁曾在一篇文章就可改变自身命运的时刻却选择了自我放逐?有谁正当自己多年的学术研究正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却自觉地放下了手中的笔?又有几个人能在一帆风顺的仕途上悄然远遁?
面对这一次次的选择与放弃,除了精神与信念,我找不出别的解释。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与王元化先生那样通过痛苦的反思与精深的研讨来打通“文化气脉”的努力相比。余秋雨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以自己的人生为代价,把自己放到这个动荡不休的世界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时代活生生的“文化实验品”。
为此,他甚至不惜放弃每一个文化人都最为珍惜的角色底线——知识分子的身份。
有朋友曾惊奇于这几来围绕余秋雨所发生的种种现象,“比如,当年‘文化苦旅’引发诸多文化话题,于是争论,于是批评。可是,话题突然转变了方向,当年的文化话题统统不见了,‘批余’随之成了时尚,成了游戏,成了娱乐,甚至成了产业。”
他因此而质疑道,“是什么样的‘舆论机制’有如此神奇的‘乾坤大挪移’功夫?又是什么样的‘时尚机制’将一个文化阅读问题变成了一个社会心理问题?其中道理究竟何在呢?”
就余先生自己,也曾感到大惑不解,“按照常理,我是最不容易被诽谤的,因为我不属于任何社团机构,不跻身哪种代表委员,构不成和谁争权夺利。从不批判别人,从不参加争论,从不参加会议,还长期不在城市,不在国内。然而即便这样,还是遭到了那么多诽谤……”
在我看来,这种诽谤背后的机制,其实很简单——而且它恰恰与余先生自觉的选择有关。

在一次类似“动物世界”的电视节目里,主持人谈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有着群居习性的狼群里,一旦一只狼由于种种原因被逐出狼群,成为“孤狼”的时候,不但它原本从属的那个群体会排斥它,驱逐它,就连其他群落里的“老弱病残”也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负它和欺负它,仅仅因为它们背后有着另一个群落为依靠……
这种来自动物世界的“种群生态学”恰恰是余秋雨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当他为了更加自由的思考而一次又一次地放弃自己所曾经拥有的一个个“身份”时,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恰恰是在剥离与这些“身份”紧紧相连的一重重“社会保护罩”。
可以想象,当余先生还是“余教授”时,对于他学术著作的无理讥谤将会招来整个学术界怎样的回应——他们会将之视为对整体学术尊严与自由的挑战;而当余先生还是“余院长”时,这种诽谤不消说嚣尘日上,只要稍一露头便会引来有关部门的“严正声明”,乃至“绳之以法”。
而恰恰是他自己一层层地剥开了这严密的盔甲,将自己放逐成一只文化旷野上的“孤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余先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时代活生生的“文化实验品”。
这让我想起了台湾的另一位“文化孤狼”,那就是李敖先生。将余先生与李先生的人生轨迹作个对比实在是很有趣的事。
他们同样对文化有着“九死不悔”的信念;同样对由文化而铸就的“大人格”心向往之;同样因种种原因而剥离了自己曾经拥有的文化与社会角色;也同样因为这种剥离而遭受到扑天盖地的讥评与诽谤,李敖先生更因此而两度被构陷入狱。
但两人在文化心态上其实有着很大不同,余秋雨的心态重在“立”,对此一理路的形成,前文已有论述。
这使得他无论在为文还是为人中,都显得重大局而轻个体,重机制而轻个案。就在遭受了那么无理的诽谤之后,余先生仍然从文化的角度,表示他愿意原谅那些恶意的攻击者。
“被告只是一大群人的一个代表,而这一大群人,又代表着一段漫长的历史,代表着一个强大的话语权力,代表着一种社会灾难的生成机制、蔓延机制和复燃机制。这么大的空间含量和时间含量,投射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本身就有被原谅的理由。”
但在消解个人恩怨的同时,余先生却又为百岁老人巴金重新受到大规模的诽谤和侮辱而义愤填膺,因为在他看来,这恰恰是文化上“一个真正的标志性的事件”。
这种个人与文化角色界定的模糊造成了余秋雨与他的对话(不如说“对骂”)者沟通时遭遇到相当的尴尬:在余秋雨的言说系统中,个人的“人格”是与历史文化息息相关的,于是在对手言之凿凿的“余秋雨是坏蛋”面前,他选择了一种“文化”的态度,先是“不与争”,到了“不得不争”时又采取了“文化”的态度,乃至被逼急了说出这样“文化”的话来:“你们伤害我,就是伤害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大意)。”
此言一出,对手大喜而旁观者嗤,“这丫也太把自个儿当回事了……”
殊不知余先生一直以为他对话乃至对抗的根本就是一种“文化态度”、“文化现象”乃至“文化机制”。
与此同时,李先生却在台湾大叫寂寞,盖因在其扎实的考据功夫与不留情面的辣手文风面前,台湾岛上已多年“辩者绝迹”矣。曾经的“辩手”们闻风而遁的一个理由是:“这家伙不讲大体,不讲背景,抓住一条小辫就死咬不放”,总而言之,不是“学术的态度”。
而这一点恰恰是李敖在多年的文化与体制抗争中煅炼出来的一手“绝技”:那就是以个体化的方式来“解构”乃至摧毁一个又一个包裹着文化糖衣的“宏大叙事”。
为此,李先生不惜将他从学术角度对传统历史和价值观的考证与颠覆,转变成与一个个对手(如蒋氏父子)的“个人恩怨”,把一个个价值冲突转换成一场场“文字公案”,甚至不惜兴讼入诉。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凤凰卫视里69岁高龄的李敖先生得意洋洋的表情,
“近来‘生意’清淡,只剩十三个官司要打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