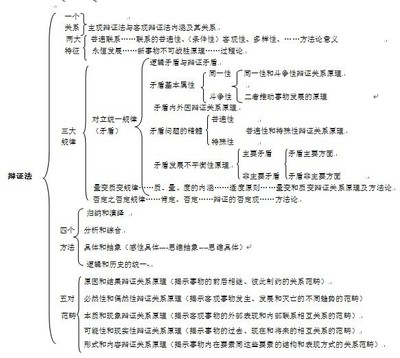我们多少年来一直在说,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可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和工作中,无论是搞政治工作的人,或是做经济工作的人,或是做学问的人,要真正把唯物辩证法当作“世界观”、“方法论”、“武器”,该是多么的不容易!
有的人懂辩证法,有的人不懂辩证法;有的人会用辩证法,有的人不会用辩证法;一个人有时用辩证法,有时又放弃它;有的人在无意识中应用了辩证法,也在无意识中丢弃了辩证法;也有正确地有意识地应用辩证法和有意识地抛弃辩证法的。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的利益需要和认识水平(以及应用辩证法能力)的高低。
可以说,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立场和观点来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事物、一切人、一切问题,才能得出正确或接近于正确、比较正确的结论。这是一条认识和理解事物的规律,但又常被人们所忽视,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著名经济学家苏星说:“一般来说,所有规律都是在被破坏时才令人感觉到,而破坏规律不能不遭殃。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当事情办成功时,认真总结经验,是同样可以认识规律的。不过在前一种情况下,可能感觉更为深刻。”(《怎样学习和研究政治经济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第75页)苏老先生的这段话本身就是应用唯物辩证法观点来看问题,它客观地提出了认识规律的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的渠道。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最常出现的反唯物辩证法的做法是:喜欢从成功中总结经验,不喜欢从失败中总结教训;从成功中总结的经验多,从失败中总结的教训少;无用的经验多,有用的教训少。
例如1986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说:“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所以还是不写的好。”([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著:《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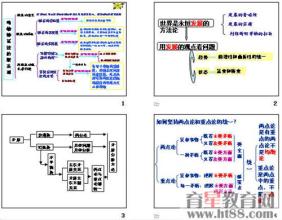
在这段话里,邓小平同志的观点至少有两点是客观辩证、令人钦佩的。第一点,承认自己做过的事有好事,也有错事;第二点,认为在自己的传记里不仅应该把好事写下来,不好的事、甚至错事也应该写下来。
可是最后一句话“所以还是不写的好”就不是辩证唯物的了。虽说这瑕不掩瑜,但也是瑕瑜互见的。那些“不好的事”、“错事”,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写出来和不写出来都应该是一个样,这有什么好遮掩的呢?因此我看邓小平同志说前边的话像“男子汉”,而说后边一句话则像“女人”——像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里所写的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未成曲调先有情”的“女人”了。这“曲调”是什么呢?这“曲调”就是写兼具“好事”和“不好的事”的“传记”。这应该是一个好“曲调”,如果邓小平同志在他生前能把这“曲调”写成,那他一定会更加伟大。可是这“曲调”未成却先有“情”了。这“情”又是什么呢?这“情”大概就是——只让大家对那些“不好的事”、“错事”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足以说明老人家是“襟怀坦白”的就行了;至于好事,那自然是在宣传物上一条一条明摆着的。邓小平同志的以上态度代表或说明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重成功、轻失误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得我们很多人在很多时候不容易、不情愿对一切人和事物都抱着一个唯物、辩证的科学态度。
违背唯物辩证法、或者说不是唯物辩证地认识事物而得出的理论、观点是很多的。假使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样都从实践中来,但却会得出十分不同的结论,“因为社会生活现象的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种意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182页)
要真正在我们的思想工作中贯彻唯物辩证法,不能只是从正面提倡唯物辩证法,更重要的是要敢于批评那些最应该按辩证法办事、却又没有按辩证法办事的大人物,让警钟长鸣。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