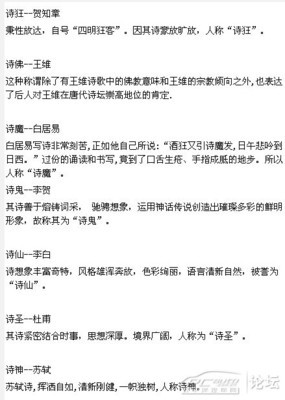生活是什么?到底怎样才算生活得实在?这些问题有点像一个三岁的孩子问他的父母:天上的星星是什么?为什么会把眼睛眨来眨去?做父母的面对这些问题往往是无所适从的。说真话孩子既听不懂也解释不清楚,似乎也没有必要。谁都知道,对一个三岁的孩子来说,真理绝对不如一个童话,更不如一个装得满满的奶嘴瓶。孩子哭叫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父母会对其讲一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大道理。所谓生活,其道理也该是这样的吧!在红尘闹市之中,恐怕没有谁可以对生活来一个“一言以蔽之”,除非真正在生活中浸泡既久,酸甜苦辣千滋百味入心入肺,漫漫长路坎坷途程不愿再提,似乎会选择一言不发,皱皱眉头算做一了百了。勉强张口也像诗人北岛那样的简练。《生活》嘛?不就一个字吗:“网”。真是艺术家的一言九鼎。一“网”字说尽了生活不可穷尽之奥妙。对此再做续貂之论似乎实在吃力不讨好,即便再出千言,也未必能比此一字之万一。颇有一日既出,众星顿无容身之隙的况味。
不过,事情又有另一面。描述为“网”的生活与实际的生活毕竟是两回事。就像另一个诗人顾城以绝顶概括的笔触写“死亡”:死亡不过是一个小手术 / 只切除了生命。比之于人在一生中所会遭遇的无论多大事情,死亡的分量都不可谓不重,甚至可以说与生命并斤两。但如此的描述“死亡”与真正的死亡又不同。这世间我们各有各的生,也就注定各有各的死。任何描述都免不了会相当片面。“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是确论,偏偏还有另一“确论”:“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鱼之乐?”除了表面看起来有些耍贫嘴的意味外,这一说法仍然触到了事物的核心。对于任何事,只要我们在经历着,我们就会有自己的独到顿悟。生活就是这样,与其身陷一“网”,不如退而“经营”,就像面对死亡,与其像顾城那样“切除生命”,不如让生命之果好好在身体这棵树上美美地结着,有什么必要亲自动手“切除”呢。这些事大自然会做,上苍会做。至于生命有限的我们,只要好好活着,“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就够了。

生活之需要“经营”实在是一件很悲惨的事,但生活之尚能“经营”又实在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世间的事往往。奇妙得甚至说起来可笑得很。不是这样么?“经营”一词代表着费尽心机,狗苟蝇营,在熙来攘往的红尘中苦苦挣扎,身为凡人就得像凡人的样子:“义”字放两头,“利”字摆中间。又得为柴米油盐操劳得容光散尽,鬓发霜雪。当然别提日出而作日落难息的纷扰了。至于求学、工作、处人、理事,可谓机关算尽;更别提婚恋、家庭、儿女等等,真正是吃尽苦中苦,难为人上人。这样的“经营”坑了多少人,已经没能统计了。只知道英雄磨难,红颜命薄已是不争的世像。曾为朦胧诗坛盟主的北岛先生在生活之“网”的围追堵截下,据说已结庐瑞典。山风海雨相隔,不知道眼下都怎样“经营”,“经营”些什么;至于顾城先生,大家也已经知道,“经营”“苦累”之余,他也给自己的生命动了个“小小的手术”,“切除了”两个共枕人的“生命”之后,也把自己的生命“切除了”。可见是生活之“经营”实在一点也不轻松。浪漫如诗人尚且不得不向自己下手;凡人更是,将作何想?只好不作何想。活着,经营着,流年似水,风过树摇。就如同前苏联作家格·马捷沃相在其名著《你的亲族》里点染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我的儿子。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不想为自己的父亲辩护……不过我要说:难道你的,你这里的亲族就好吗,他们并不弯下身子,也并不挺直身子,他们不是在生活,浑浑噩噩,善良,懒惰,他们自生自长,如果你砍去他们,那就砍去,如果你不砍去,那就继续活着,如果你摘去他们头上的帽子,那就摘去,如果不摘去,那就还在他们头上。”
说得真是妙极了。生活之艰难既然是不可回避的事实,那么,作为生活中仍然还存在的一分子,而且是作为最普通的一分子,我们又该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仔细想来,生活之尚可用心“经营”也算得上是人生之一大乐事。“经营”是才华的施展,智慧的外现。有如在当今这个全民皆商的时代,投身商海,到世纪末的商场上搏击一场,“经营”好生意只算得上愚者千虑;相反,“经营”好自己的每一个晨昏,每一段旅程,每一个脚步。总之一句话,“经营”好自己的生活才是悟到了“庖丁解牛”的奥妙。本来嘛,人生在世就是一场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的策划。不是么?假如是什么也没思虑头了,什么也不用操心了,什么也不必回顾或者向往了。这恐怕已不是什么好兆头。相反,可能标志着一切都到头了。只不过,我们的“经营”力求能够在自然之理大而化之的前提下,对自己的每一天精雕细刻。既然是“经营”,就让每一天都有所进益。在使自己的肉体之身三餐有托的同时,也给生活的别一个层面涂上一些亮丽色彩。就像作一幅画,在大红大绿的夹缝里不妨也添上几抹神秘却也醉人的蔚蓝色。
生活之需要“经营”说明我们至少还有事可做。一来尚不被生活之“网”捆绑得动不了手脚;二来嘛,至少说明我们暂时还不必要动“手术”将自己的“生命”“切除”掉。虽然免不了会有风风雨雨,那就让它吹吧、下吧。我们一如既往地“经营”着。再者,刮风下雨的日子我们起码可以心平气和地驻守在屋子里。即便正在路上,那又怎样呢?如果风雨不大,那就让它洗尘抚面,算是饯行或者迎迓;如果风雨太大,那也让它吹刮、淋漓,它无非面对我们的帽子或者头颅,它要是把两者都吹刮掉了,那就让它拿去,要是只淋漓掉了一者,那么,另一者就还在我们头上留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