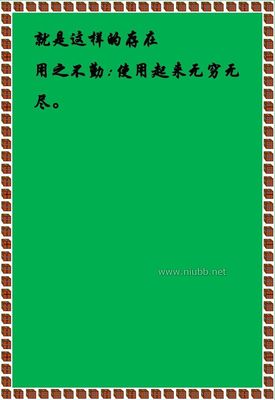在斯隆管理时代到来之前,通用汽车公司的组织结构存在一个基本问题:缺乏一套正式有效的反馈模式,公司管理层无法听取来自雇员的不同意见。除此以外,公司高层并不重视已经出现的意见分歧,更不相信这种分歧有利于解决问题。在工作时,公司高层也并不提倡开诚布公。这种做法的结果显而易见,公司成为老板的“一言堂”。在这种独裁专制的管理文化下,下级不得不服从上级的命令,否则就会被开除。就本质而言,这种管理方法是封建专制的。公司的管理层高高在上,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强硬语气命令下级。斯隆意识到了这个遗留问题所带来的影响,它使个人成为绝对的统治者:“专权是最高效的行政手段,它给管理者提供了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但管理者们永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永远不想知晓解决问题的真正方法。这就是专权最终失败的原因。”在20世纪即将到来时,由于中层管理人员的缺位,通用汽车公司成了“一言堂”。无论是收购、生产,还是市场营销,都由同一个人做出决策。对于公司的运营情况,雇员们几乎没有发言权。他们的意见要么石沉大海,要么成为被解雇的理由。无论如何,在斯隆的领导下,这一弊端得到了充分的改善。斯隆掌管通用汽车公司之后,鼓励员工及时提出异议,这种做法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管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改善了公司和工作场所的管理情况。斯隆沟通理念的形成1895年,斯隆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并获得电子工程学士学位。毕业后,斯隆进入海厄特滚珠轴承公司做绘图员。公司位于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主要生产减磨滚珠轴承。这种产品最终成为汽车产业至关重要的零部件,同时也成为斯隆得以晋身通用汽车公司的阶梯。aihuau.com在海厄特公司,斯隆遇到一位名叫彼得·施蒂恩斯(Peter Steenstrup)的簿记员,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移民。在吃午饭时,两人常常讨论这个小公司的经营弊端。当时,公司只有25位雇员,而两人尤其关注公司的老板约翰·卫斯理·海厄特(John Wesley Hyatt)。斯隆回忆:“我们养成了讨论公司事务的习惯。正如年轻人常常做的那样,我们畅所欲言,坚信自己能做得更好。”斯隆与施蒂恩斯一致认为,海厄特先生并不是一个机敏的生意人,最起码,他所具备的眼光还不能使这个小公司赢利。但海厄特先生是个天才的发明家,他曾经为赢得一笔10 000美元的竞赛奖金而发明了赛璐珞。竞赛的发起人是一位台球制造商,他想要寻找一种坚固的替代品以取代象牙来制作台球。作为海厄特公司的新雇员,斯隆对公司的运营毫无发言权。他可以将想法向施蒂恩斯一吐为快,却不能陈述给公司管理者。斯隆为不能畅所欲言而苦恼。毫无疑问,作为拥有电子工程学位的新一代大学毕业生,斯隆已经感觉到他的想法对公司是非常有益的,应该受到重视。最初的斯隆-施蒂恩斯式交流,建立了一种坦诚公开的交流模式。后来,斯隆在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阶层中大力推广这一模式。对斯隆来说,与施蒂恩斯的交流是一种享受,他找到了一个性情相投的人、一个优秀的倾听者、一个即使两人意见相左也从不拒绝分享个人观点的人。1898年,斯隆的父亲和一位同事买下了海厄特滚珠轴承公司。斯隆与施蒂恩斯成为商业合伙人,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在等待着他们。这两个年方20但满怀壮志的年轻人,迅速进入公司管理层。斯隆成为总经理,施蒂恩斯则主要负责销售。摆脱了老海厄特先生的牵绊,两个年轻人开始将他们谈论已久的商业理念付诸实践。走马上任的第一天,他们发布的第一道指令就是终止每月都发生的重复浪费。组织结构重组六个月以后,公司开始小幅赢利。由此,斯隆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精神层次的沟通会带来收获,即使是雇员们之间的冲突,也同样可以造福于公司。斯隆初涉汽车制造业1899年,位于印第安纳州Kokomo的埃尔伍德·海恩斯公司(Elwood Haynes)给斯隆发来一张订单,要求为他们的车轴生产滚珠轴承。当时海恩斯公司生产一种以燃烧汽油为动力的新型机器—汽车。18年时光荏苒,海厄特滚珠轴承公司成为全国最成功的滚珠轴承制造公司之一,为全美的车轴制造商和新兴的汽车市场供应产品。斯隆是个勤奋而敏锐的人,他在此时意识到,汽车产业这个新兴行业尚未发挥它全部的生产力。各种迹象都预示着这种情况,例如,由于汽车价格的降低,更多的美国人将购买他们的第一辆汽车。1921年,斯隆掌管通用汽车公司的第一年,汽车产量为1 400 000辆;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的那一年,汽车产量为4 500 000辆,产量增加了3 100 000辆之多。只要比较这两年的汽车生产情况就可以知道,斯隆的这个预见已经成为现实。此时,海厄特公司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销售问题—他们几乎把所有的产品都卖给了一家轴承公司—位于纽约州尤蒂卡(Utica)的韦斯顿-马特公司(Weston-Mott)。1906年,韦斯顿-马特公司开设了一家新公司,地址在密歇根州的弗林特(Flint),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靠近当时已经独立经营的别克制造厂。对于别克公司来说,周边能有一家车轴制造商无疑大有裨益,因为这样既能大幅缩短运输轴承的时间,同时也提高了公司完成订单的速度。1908年,别克公司收购了韦斯顿-马特公司49%的股份,并使其在不久后正式成为通用汽车集团的一员。在韦斯顿-马特公司的客户群里,两个最大的客户是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此时斯隆已经意识到,鉴于这两家公司在汽车制造领域里的主导地位,这两家公司迟早都会建立自己的滚珠轴承生产线,这样的结果将留给海厄特公司一个难以收拾的局面—锐减的产品销售额以及位于纽瓦克的毫无用处的工厂。海厄特公司是一个典型的二人公司。在这个小公司里,斯隆独立行使管理职能,施蒂恩斯则负责销售。在斯隆所有的自传里,都没有任何与施蒂恩斯意见相左的记录。原因显而易见,斯隆独自做出决策。斯隆与联合汽车公司1916年,斯隆将海厄特公司卖给通用汽车公司,解决了公司的前途问题。海厄特公司成为通用汽车公司新的一员,更名为联合汽车公司,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的零部件生产商之一。在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都可能自主生产滚珠轴承的局面下,斯隆此举可谓明智,他使海厄特公司得以从一场危机中解脱。斯隆并未主动出售公司,准确地说,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杜兰特提议购买海厄特公司的股票。这位汽车产业的先驱和梦想家,提出了一项伟大的计划,要将所有为通用汽车公司供应零部件的公司全部买下。这在当时是极具革命性的。除了海厄特公司,杜兰特还买下了其他几家零部件生产公司,包括代顿电子工程实验室、瑞密电子公司(Remy Electronic)和杰斯钢铁公司(Jazon Steel Products)等。杜兰特任命斯隆为新成立的联合汽车公司总裁,这给了斯隆一个良机,使他能直接听取其他主管报告并实行各种决策。年届40的斯隆,第一次有了一个小董事会。这次良机也使斯隆能够与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其他制造商共事。斯隆很欣赏他们注重客观事实的决策态度,这种风格与他自己的是类似的。在斯隆的早期管理生涯中,他首先经历了来自下属对他实施的组织变革的反对。斯隆将几个不同的公司合并成一个,这次组建联合汽车公司的成功,正是得益于这一点—斯隆有能力将异议中的合理之处吸收并利用。杜兰特的独裁风格通用汽车公司第六任总裁杜兰特的管理风格是独裁而专制的。斯隆对此十分不满,也曾因此遭受排挤。但是,斯隆关于现代公司组织结构的改革构想,很可能也正是脱胎于此。就本质而言,杜兰特是一个有魅力、相信直觉而又带着投机心理的人。斯隆与杜兰特正相反,他遇事深思熟虑,他内心的忧虑像沙砾,却能将创意打磨成璀璨的珍珠。斯隆的决策方式与杜兰特迥然不同,无论事关管理方法还是组织架构,当机会出现时,斯隆都谨慎从事。斯隆认为杜兰特擅长创造,但不是个管理者。通用汽车公司已经发展得太大,需要有组织的管理。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述杜兰特的成功与失败。在杜兰特的一生中,他曾经两度失去对通用汽车公司的控制,但他也曾两度反败为胜。在美国汽车产业历史上,杜兰特是与亨利·福特地位相当的先驱。杜兰特是个天生的推销员,但又带着投机心理。他例行公事、草率决策,既不与他人商议,也不研究那些关于事实的报告。但杜兰特实行了多样化生产体系,为消费者提供多种车型以满足不同需要,这一成就使杜兰特载誉而归。在斯隆的著作中,他几乎从未表露过对同事或竞争对手的不满。当斯隆提及他早期与杜兰特的合作时,更是谨言慎语:“我成为通用汽车公司总裁之后,常常和杜兰特先生见面。他做决策的方法总是使我吃惊。”平心而论,杜兰特做出过许多冲动但才华横溢的决策。这种冲动的表现是,他几乎一点儿也不考虑方案的成本或者适用性。杜兰特总能发掘很多不同的发明家,并为他们提供研发经费、实验场地和操作设备。一次,在他人的引荐下,杜兰特见到了一位陌生人。这个人声称,他能够用瓷制造出更好的火花塞。这位陌生人就是法国赛车选手阿尔伯特·尚普兰(Albert Champion)。得益于别克公司的种子资金,尚普兰很快为AC火花塞公司(AC Spark Plug Company)造出了更好的火花塞。该公司于1925年被通用汽车公司完全收购。然而,斯隆并不赞成杜兰特的某些做法。杜兰特的身边都是“好好先生”,他已身陷任人唯亲的禁锢之中。斯隆成为总裁,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管理模式,他绝不愿看到自己被一群亦步亦趋的人包围。在杜兰特任职期间,通用汽车公司的首脑曾经决定在底特律寻找地皮,兴建一栋办公大楼。这一事件成为斯隆反对杜兰特随性管理风格的典型例证。会议在纽约通用汽车公司总部召开。会议上的主流意见是在底特律市区选址,这也是公司首脑们一直以来的打算。斯隆偶然介入会议,随之向杜兰特提出了一个不同意见:市郊的地皮会更便宜,而且这个位置对于很多住在郊区的雇员来说也更便利。在斯隆想要将海厄特滚珠轴承公司迁至新泽西的时候,就曾经对这个问题做过深入研究:可以说,提出这个意见时我是很犹豫的,因为这并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我主动提出一个意见:“市区的地皮,无论是价格还是税收都很高,为什么要给公司增加无谓的负担?”杜兰特的回答是:“下次我们去底特律的时候,会去你推荐的那个地方看看。”我们确实这样做了。杜兰特授意我买下这块地皮,这正是他行事的独特之处。“价格呢?”我问。“只要把你决定的价格告诉出纳就可以。”这次搬迁的历史意义十分明显,因为这里最终很可能就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总部。而杜兰特做出决定时,就像订购一盒纸夹一样随便。一个身跻《财富》(Fortune)杂志百强企业的大公司,做出像重新为总部定址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时,竟然不分析房地产市场、税金和位置的可变因素就做决定,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是不可理喻的。在一开始就拒绝听取不同意见,也不写可行性报告论述潜在的候选位置,这样的决策方法,在现代管理人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在公司成立专为新工厂和办公楼选址的事业部之前,斯隆就意识到公司需要专家来处理通用汽车公司的房地产交易事务。杜兰特的独裁管理风格、个人操纵决策的做法,促使原本沉默寡言的斯隆一次次地成为团队中的不和谐因素。杜兰特做出决策时,既不与下级商讨,也不看研究报告,更不研究销售情况,甚至,他从来没有和委员会做出过集体决策。斯隆做过很多次尝试,想要将这位机智善辩的独裁者引到理性管理的道路上。斯隆认为,通用汽车公司有必要邀请一家独立会计公司,以便对公司的财务进行全面审核。在通用汽车公司里,斯隆是第一位提出这样建议的经理。他建议邀请海根斯塞乐(Haskins and Snell)会计事务所担当此任。当斯隆还是海厄特滚珠轴承公司的总裁时,这个事务所就曾为海厄特公司做过审计。使下属们大感意外的是,杜兰特迅速地对此事做出了答复,其速度与当初他为大楼选址时的速度一样快。在得到杜兰特的首肯之后,斯隆聘请了海根斯塞乐会计事务所为通用汽车公司做首次财务审计。斯隆并未主动出售公司,准确地说,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杜兰特提议购买海厄特公司的股票。这位汽车产业的先驱和梦想家,提出了一项伟大的计划,要将所有为通用汽车公司供应零部件的公司全部买下。这在当时是极具革命性的。除了海厄特公司,杜兰特还买下了其他几家零部件生产公司,包括代顿电子工程实验室、瑞密电子公司(Remy Electronic)和杰斯钢铁公司(Jazon Steel Products)等。杜兰特任命斯隆为新成立的联合汽车公司总裁,这给了斯隆一个良机,使他能直接听取其他主管报告并实行各种决策。年届40的斯隆,第一次有了一个小董事会。这次良机也使斯隆能够与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其他制造商共事。斯隆很欣赏他们注重客观事实的决策态度,这种风格与他自己的是类似的。在斯隆的早期管理生涯中,他首先经历了来自下属对他实施的组织变革的反对。斯隆将几个不同的公司合并成一个,这次组建联合汽车公司的成功,正是得益于这一点—斯隆有能力将异议中的合理之处吸收并利用。杜兰特的独裁风格通用汽车公司第六任总裁杜兰特的管理风格是独裁而专制的。斯隆对此十分不满,也曾因此遭受排挤。但是,斯隆关于现代公司组织结构的改革构想,很可能也正是脱胎于此。就本质而言,杜兰特是一个有魅力、相信直觉而又带着投机心理的人。斯隆与杜兰特正相反,他遇事深思熟虑,他内心的忧虑像沙砾,却能将创意打磨成璀璨的珍珠。斯隆的决策方式与杜兰特迥然不同,无论事关管理方法还是组织架构,当机会出现时,斯隆都谨慎从事。斯隆认为杜兰特擅长创造,但不是个管理者。通用汽车公司已经发展得太大,需要有组织的管理。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述杜兰特的成功与失败。在杜兰特的一生中,他曾经两度失去对通用汽车公司的控制,但他也曾两度反败为胜。在美国汽车产业历史上,杜兰特是与亨利·福特地位相当的先驱。杜兰特是个天生的推销员,但又带着投机心理。他例行公事、草率决策,既不与他人商议,也不研究那些关于事实的报告。但杜兰特实行了多样化生产体系,为消费者提供多种车型以满足不同需要,这一成就使杜兰特载誉而归。在斯隆的著作中,他几乎从未表露过对同事或竞争对手的不满。当斯隆提及他早期与杜兰特的合作时,更是谨言慎语:“我成为通用汽车公司总裁之后,常常和杜兰特先生见面。他做决策的方法总是使我吃惊。”平心而论,杜兰特做出过许多冲动但才华横溢的决策。这种冲动的表现是,他几乎一点儿也不考虑方案的成本或者适用性。杜兰特总能发掘很多不同的发明家,并为他们提供研发经费、实验场地和操作设备。一次,在他人的引荐下,杜兰特见到了一位陌生人。这个人声称,他能够用瓷制造出更好的火花塞。这位陌生人就是法国赛车选手阿尔伯特·尚普兰(Albert Champion)。得益于别克公司的种子资金,尚普兰很快为AC火花塞公司(AC Spark Plug Company)造出了更好的火花塞。该公司于1925年被通用汽车公司完全收购。然而,斯隆并不赞成杜兰特的某些做法。杜兰特的身边都是“好好先生”,他已身陷任人唯亲的禁锢之中。斯隆成为总裁,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管理模式,他绝不愿看到自己被一群亦步亦趋的人包围。在杜兰特任职期间,通用汽车公司的首脑曾经决定在底特律寻找地皮,兴建一栋办公大楼。这一事件成为斯隆反对杜兰特随性管理风格的典型例证。会议在纽约通用汽车公司总部召开。会议上的主流意见是在底特律市区选址,这也是公司首脑们一直以来的打算。斯隆偶然介入会议,随之向杜兰特提出了一个不同意见:市郊的地皮会更便宜,而且这个位置对于很多住在郊区的雇员来说也更便利。在斯隆想要将海厄特滚珠轴承公司迁至新泽西的时候,就曾经对这个问题做过深入研究:可以说,提出这个意见时我是很犹豫的,因为这并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我主动提出一个意见:“市区的地皮,无论是价格还是税收都很高,为什么要给公司增加无谓的负担?”杜兰特的回答是:“下次我们去底特律的时候,会去你推荐的那个地方看看。”我们确实这样做了。杜兰特授意我买下这块地皮,这正是他行事的独特之处。“价格呢?”我问。“只要把你决定的价格告诉出纳就可以。”这次搬迁的历史意义十分明显,因为这里最终很可能就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总部。而杜兰特做出决定时,就像订购一盒纸夹一样随便。一个身跻《财富》(Fortune)杂志百强企业的大公司,做出像重新为总部定址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时,竟然不分析房地产市场、税金和位置的可变因素就做决定,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是不可理喻的。在一开始就拒绝听取不同意见,也不写可行性报告论述潜在的候选位置,这样的决策方法,在现代管理人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在公司成立专为新工厂和办公楼选址的事业部之前,斯隆就意识到公司需要专家来处理通用汽车公司的房地产交易事务。杜兰特的独裁管理风格、个人操纵决策的做法,促使原本沉默寡言的斯隆一次次地成为团队中的不和谐因素。杜兰特做出决策时,既不与下级商讨,也不看研究报告,更不研究销售情况,甚至,他从来没有和委员会做出过集体决策。斯隆做过很多次尝试,想要将这位机智善辩的独裁者引到理性管理的道路上。斯隆认为,通用汽车公司有必要邀请一家独立会计公司,以便对公司的财务进行全面审核。在通用汽车公司里,斯隆是第一位提出这样建议的经理。他建议邀请海根斯塞乐(Haskins and Snell)会计事务所担当此任。当斯隆还是海厄特滚珠轴承公司的总裁时,这个事务所就曾为海厄特公司做过审计。使下属们大感意外的是,杜兰特迅速地对此事做出了答复,其速度与当初他为大楼选址时的速度一样快。在得到杜兰特的首肯之后,斯隆聘请了海根斯塞乐会计事务所为通用汽车公司做首次财务审计。在斯隆担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岁月里,他愈加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是杜兰特的独裁式管理风格,还是他“一言堂”式的决策方法,都无法长期存在。无论是通用汽车公司以指数成长的态势、不断增加子公司的局面,还是持续增长的销售量,都证明了斯隆这种想法的正确性。斯隆已经认识到,一旦杜兰特可以在不考虑其他管理人员意见的情况下独自做出第一个决策,他就会永远这么做下去。斯隆这样写道:“通用汽车公司太大了,它不再是一个人的舞台。”1920年,斯隆在通用汽车公司的职位日渐升高。同年,杜兰特第二次被迫辞职。此时,斯隆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将“鼓励员工及时提出异议”的做法系统化,并进行推广。他绝不想培植出一群对自己唯唯诺诺的人。斯隆的目标在于使通用汽车公司的气氛更加民主,以便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随着杜兰特永远地退出了通用汽车公司的舞台,那个专制管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斯隆鼓励自由地交换意见,他将这一点引入自己的公司重组计划。就此,新的管理时代很快初露端倪。然而,在斯隆实现所有的变革前,他还要跨越一个障碍,而这个障碍,在他还是通用汽车公司执行副总裁时,就已经出现了,而且这场发生在管理高层之间的争执,必然会使斯隆与公司总裁杜邦对立,会使斯隆与查尔斯·凯特林(Charles Kettering)对立,而凯特林是通用汽车公司一位不可或缺且才华横溢的研发人员。在美国汽车产业历史上一次最著名的争论是关于风冷发动机与水冷发动机的。斯隆积极提出异议,确立了明确表达不同意见这一管理模式。这一模式,后来成为斯隆长久而成功的管理时代的特点。在发动机之争出现之前,斯隆已经把反对关闭雪佛兰公司的不同意见付诸实践,这个决策对通用汽车公司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1920年,通用汽车公司刚刚上任的第七任总裁杜邦先生面临一个难题—是否清算惨淡经营的雪佛兰公司。这对斯隆来说,是个处理意见分歧的典型事例。他组织了一次会议,并在会议上陈述事实。斯隆这样写道:“我们都试图说服杜邦先生,想让他相信,有许多人只能购买比凯迪拉克,甚至比别克更便宜的车。如果在低价车领域,我们停产雪佛兰,通用汽车公司将无法与福特公司竞争,这将是通用汽车公司的耻辱。这是能力和勤奋工作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斯隆坚定不移。他的勇气影响了杜邦,使他变得更为宽容。这个鼓励员工积极提出异议的惯例,后来成为美国公司组织结构的一部分。此惯例始于发动机之争,在这场争论里,杜邦并没有听从斯隆的意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这场发动机之争的背景是这样的:1920年,杜兰特离职后,通用汽车公司当时的董事会主席杜邦决定继任公司总裁。由此,杜邦成为斯隆的顶头上司。而杜邦曾经读过斯隆的《组织研究》,斯隆富有条理、行文简明的风格,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18年,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子公司—代顿电子工程公司中,查尔斯·凯特林开始实验风冷发动机,他希望以此替代水冷发动机,进而使之成为汽车产业的标准。通用汽车公司引用了一个更高级的营销术语,叫作“铜冷发动机”。水冷发动机需要精细的水管系统和水箱,在理论上,风冷发动机似乎更高效且成本较低。对这件事,通用汽车公司的每个人都很关心,希望能将风冷发动机率先应用到自己分公司的汽车生产线上,继而再推广至各个分公司。在将风冷发动机试用到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线上的几个月前,斯隆对此就持怀疑态度。他的想法是,对于如此彻底而激进的改革,公司应当先做尝试,然后再逐步地引用到汽车生产线上,而且应该从价格最低的雪佛兰汽车入手。但斯隆所在的执行委员会似乎更倾向于大刀阔斧的改革。斯隆并未身陷急速改革的热情中,他对这种尚无人尝试的全新发动机持保留态度。从长远的角度看,这一事件标志着通用汽车公司首次涉足未知领域。在这次尝试中,两个团队之间发生了直接摩擦:一个是以凯特林为主要负责人的研发团队,一个是雪佛兰公司的管理层。应该采用哪一方的意见?是采取研发团队的意见,还是雪佛兰公司管理层的意见?斯隆意识到执行委员会并未解决这个问题。他感到一场冲突迫在眉睫,特别是当执行委员会下令停止生产所有水冷发动机之后,这种情况更为凸显。对于注重实效的斯隆来说,这是用一种全新的系统进行赌博。这种做法会给公司带来很大风险,远远超出公司所能承受的范围,更何况这种尚未经过尝试的系统很可能会大举改变汽车工业。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风冷发动机的决策,背离了斯隆所提倡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刚刚被认可—“无论是站在一个商人的角度,还是站在一个管理者的角度,我们的行为都背离了我们的信条。比如说,我们太过注重具体的发动机设计,而忽视了企业的主要目标。”这里的“企业”,是指通用汽车公司,此时公司已经拥有多个事业部。让斯隆感到苦恼的是,杜邦并不同意他的观点。斯隆知道,严重分歧的思维模式不会长期存在。“信条”是指他经过深思熟虑写成的《组织研究》。多年以来,由于既缺乏一个坚定的支持力量,又处在杜兰特的独裁式管理下,斯隆可谓举步维艰。他再也不愿重蹈这样的覆辙。在初步汽车试验中,凯特林发明的风冷发动机出现了很多严重的失败。此时,斯隆的意见赢得了可观的支持。斯隆的建议是,公司应该继续使用水冷发动机。这种情况的出现已在斯隆的预料之中,他已准备打响一场“异议”之争。斯隆希望能借此改变执行委员会的主流意见,停止继续生产风冷发动机。斯隆常用备忘录来表达他的不同意见。这些备忘录短小精炼,事实根据充足,极具说服力。作为一种明确表示异议的方法,这些备忘录在通用汽车公司会议记录中显得十分突出。斯隆曾将他的《组织研究》印成手册进行推广,他也曾把此书的副本提交给杜兰特和执行委员会,以表达他的不同意见。斯隆在表达观点时,经常利用那些标记了项目号或者数字的列表。他在记录协定或决策时,通常将要点编号,用这种方法,斯隆记录下他的提议以及被采用的意见。斯隆会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公司做出的决策。将风冷发动机装配在新型雪佛兰里的决策,后来被证明是一场灾难。1923年夏,雪佛兰分公司召回所有配置风冷发动机的汽车。由于斯隆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执行委员会最终放弃了这项发明,并停止生产这种新型发动机。风冷发动机的计划被搁置起来,凯特林对此大为恼火。他深信他和他的团队能使这种发动机变得实用可行。出于对工作成果化为乌有的气愤,凯特林向通用汽车公司递交辞呈,并请求将风冷发动机技术带至其他汽车生产商那里。而此时,斯隆对凯特林的支持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在汽车产业形成发展的那些年里,有一批机械大师和科学巨匠出现在这个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产业前沿,凯特林是这些研究人员中的杰出代表。1911年,他和克莱德·科尔曼(Clyde Coleman)发明了电动点火系统、汽车电动启动装置,取代了费力的手摇启动装置。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再次表现了斯隆的卓著才能。他采用了一个明智的方法,尽可能地安抚那些对公司决策持不同意见但又被事实挫败的组织成员。这场争论使斯隆及雪佛兰分公司站在了与凯特林和杜邦对立的立场上。在这场内部争执中,斯隆获得了胜利,但胜利永远不是针对个人的。这场争论并没有升级成中伤诽谤,或者,使斯隆和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团队成员之间产生过节。随后,斯隆允许凯特林对风冷发动机做了一段时间整改,但后来还是永久地打消了将它作为水冷发动机替代品的想法。斯隆十分清楚他接下来的任务—“我的任务是协调凯特林先生对新想法的热情和现实之间的反差。”“现实”是指1923年汽车市场经历的一段销售繁荣期。通用汽车公司必须集中精力,以满足市场对水冷发动机不断增长的需求。这种发动机已经被整个行业所认可。距此两年后,斯隆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邀请凯特林将代顿电子工程实验室迁址底特律,在那里,凯特林将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研究所(General Motors Research Division)的主要负责人。这个新组建的研究所,比他过去的实验室更大。在那里,凯特林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关于汽车的任何实验。另外,作为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斯隆还许诺为研究所提供充足的资金、场地、设备和人力支持。斯隆为凯特林提供了一个全新而出色的实验场地,并提供充足的资金保证。在这里,凯特林可以进行任何与汽车有关的研究,而不受通用汽车公司内部任何分公司或是财务机构的约束。对于斯隆提出的这个全权委托的条件,凯特林十分满意。这样优厚的条件,任何发明家都无法拒绝,凯特林也不例外,他接受了。为了让凯特林带着研究团队迁址底特律,斯隆将他的年薪提升到120 000美元,这一薪资水平,比当时通用汽车公司付给斯隆的薪水还高20 000美元。而且只有凯特林和沃尔特·克莱斯勒可以称斯隆为“艾尔弗雷德”,其他人都只能称呼他“斯隆先生”。凯特林接受了斯隆的提议,带着他的团队迁址底特律。这次迁址使凯特林更接近通用汽车帝国。斯隆总是言出必行,使凯特林拥有随心所欲进行研究的自由。这个决策所带来的结果是20世纪上半叶最为成功、利润最高的两项发明—乙基汽油和用于冰箱的氟利昂液化气。这两项发明都诞生于凯特林的研究所,并在那里得到完善,这两项发明都为通用汽车公司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斯隆与凯特林的私人关系,并未因发动机之争而受到致命的影响。斯隆坚持实行鼓励员工提出异议的政策,在发动机之争的过程中,这种做法使他能听到各个方面的意见。斯隆认识到了凯特林作为一名科学家的价值,这证明了他的管理才能。凯特林曾经在通用汽车公司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而在未来,他也将持续发挥他的重要作用。斯隆找到了一个明智的方法,用以抚慰灰心的凯特林和他的研究团队。1945年,得益于高薪和所持有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所带来的回报,经济宽裕的斯隆与凯特林开始实施一项有关医药的新兴理念—他们在纽约市新建了斯隆-凯特林医院(Sloan-Kettering Hospital),进行癌症研究。依靠事实根据,斯隆使其他人与自己站在了同一立场。这种方法帮助了斯隆,使他在第一个据理力争的战役中获得了胜利。斯隆同样包容持反对意见的一方,允许他们在会议上和报告里宣扬他们自己的立场。最终,在取得最后的胜利后,斯隆很快开始着手弥补公司与研究团队之间的裂痕。员工分歧挽救凯迪拉克20世纪30年代,斯隆的管理体系得到了很好的巩固。同事们都已了解,斯隆,这位通用汽车公司的第八任总裁,总是鼓励员工提出不同意见,这种大度促使中层主管们勇于表达对决策的异议,即使面对公司最高管理层,主管们也不用担心这种行为会危及自己的职业生涯。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历史上,有很多关于不同意见的事例,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件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当时公司需要做出一个决策:是否让产品滞销的凯迪拉克公司停产?1928年,包括新车型拉塞尔在内,凯迪拉克分公司的汽车销售量达到41 000辆。但接下来的四年,销售量开始逐年下降,到1932年,由于整个国家处于经济低迷时期,凯迪拉克的汽车销量下降至区区9 153辆。与此同时,在国内豪华车领域,凯迪拉克的主要竞争对手普克汽车公司(Packard Motors)调低了产品的市场定位,不再保持其产品的最高价格。通用汽车公司当时可以停止生产凯迪拉克,继而利用1927年引入市场的新车型拉塞尔与普克公司以低价竞争,结束萧条时期豪华车销售不景气的现象。1932年,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会准备让凯迪拉克公司停产。凯迪拉克这个品牌很可能会由此永远留在美国汽车产业的历史里,多数董事甚至打算很快就将凯迪拉克这个品牌注销。由于斯隆对坦诚的欢迎和鼓励,凯迪拉克公司里一位名叫尼古拉斯·德雷斯塔特(Nicholas Dreystadt)的年轻工程师想和董事们见面。德雷斯塔特想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让凯迪拉克公司在18个月内赢利。他请求董事会给他10分钟时间。得益于斯隆的影响,这位工程师有机会向董事会阐述他的计划,尽管见面时间只有10分钟。德雷斯塔特想要说明,在通用汽车公司的一系列车型中,凯迪拉克是地位的象征,只有那些在商界做出成就的人才会购买。德雷斯塔特还向董事会提供了另一个信息,这让董事会很吃惊:凯迪拉克同样是富有黑人的地位象征,正如美国的其他汽车公司一样,通用汽车公司并未开辟面对黑人的市场,在黑人聚居的城镇或郊区,并没有公司的代理商,黑人只有请白人朋友作为代理人,才能买到凯迪拉克。多年之后,在德雷斯塔特回忆起自己与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的首次争论时,他对彼得·德鲁克这样说:一个董事问我:“德雷斯塔特先生,你是否明白,如果你的计划失败,你可能得离开通用汽车公司?”“当然先生,我很清楚这一点。”德雷斯塔特回答道。“可我不这样认为,”斯隆先生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德雷斯塔特先生,如果您的计划失败,您将离开凯迪拉克公司,凯迪拉克公司也将不复存在。但是,只要通用汽车公司还在,只要我还是总裁,像您这样的人就永远有工作。您敢于担当责任,善于采取主动,您有勇气,更有想像力。您关心凯迪拉克的前途,我关心您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前途。”凯迪拉克是一款低销量、高利润的车型,即使是销量的小幅上扬,也代表着利润与损失之间的关系变化。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会授权德雷斯塔特,允许他直接向黑人售车,并且给了他18个月的时间达到他的目标。通用汽车公司这次向黑人售车的尝试,标志着在美国汽车产业历史上,定位目标市场的案例首次出现。这次尝试的结果出人意料。1934年,在德雷斯塔特的领导下,凯迪拉克的销量上涨到11 468辆;1941年,产品销量达到新高60 037辆;1962年,这一高利润车型的销售量接近160 000辆,并且成为美国豪华车型的经典。斯隆此时对于自己1932年所做出的决策十分满意。正如1920年雪佛兰公司所经历的一样,鼓励员工积极提出异议的做法挽救了凯迪拉克。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斯隆对这一政策的坚持。通用汽车公司:特殊委员会的圆桌会议斯隆明白,要使通用汽车公司众多的子公司达成一致,最好的方法就是召开公司会议,让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全部出席。斯隆强调,要将众多的分歧集中,以便让每个人都能了解不同的想法,明白不同观点的基本理念。1923年,斯隆指示各分公司负责人要定期召开会议碰面,并且要求工程设计、制造生产和市场营销部门的负责人也出席。例如,一位工程师想要在汽车上增加一个零部件,他要先到生产部门去咨询这一做法或改进的可行性;他还要去市场营销部门了解增加的这一部分造价可能会对价格产生何种影响。从过去的发动机之争中,斯隆得出一个惨痛的教训:“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是极其重要的,这一点,我们能从过去的艰难历程中得出结论。关于风冷发动机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部门间没有沟通与协调,公司就会有麻烦。”斯隆永远不愿通用汽车公司卷入任何一场矛盾中,这会破坏公司平稳的运营。此外,在《组织研究》被广泛接受之后,斯隆也感到过些许的自豪,他希望他的管理体系能够像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在实际应用中表现良好。在斯隆担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期间,他创立了特设委员会,以满足各种需要。斯隆强调,这些委员会必须有做出决策的权力。在实施这些决策前,委员会要听取各个委员的不同意见。可口可乐公司的新可乐这个新可乐(New Coke)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是市场营销的一次重大失败,也是一起因公司内部意见不和导致公司受损的典型事例,即使如今旧事重提,同样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公司里那些原本持反对意见的人们,是被“一致”的旋风压得无法抬头,而附和了一项错误的决策,同意将新饮料投放市场。事实证明,从对产品的研发销售,到产品投放市场,直至终结项目,关于新可乐的争论从未停止,总有完全不同的意见出现。20年来,百事可乐(Pepsi)公司为其产品所做的广告,都是以年轻人为导向,其著名的宣传理念是“百事一代”(The Pepsi Generation)。1981年,不懈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百事可乐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可口可乐(Coca Cola)公司这一年的盈利率只超过了百事可乐公司5%,而这有限的领先,也是靠可口可乐的柜台服务和冷饮机销售以及可口可乐在“麦当劳”(McDonald誷)和其他快餐店里的独家碳酸饮料销售权得来的。在超市里,情况则完全不同。在罐装饮料市场,百事可乐公司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对手两成。百事可乐公司向消费者们发起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当时著名的广告语是“百事挑战”(The Pepsi Challenge),这是对可口可乐饮料直接猛烈的冲击。在这样的影响下,两家公司的盈利差距更大了。在可口可乐公司位于亚特兰大的本部里,还有更为糟糕的情况。可口可乐公司的经理们认为,公司需要实现一些重大的突破,以此改善市场销售情况,例如进行有奖销售,或者发动广告宣传攻势以终止百事可乐公司对自己市场份额的侵蚀。如果可口可乐公司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百事可乐公司无疑会成为美国市场上头号软饮料商,这对可口可乐公司来说,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因为每失去1%的市场份额,就意味着公司损失了数百万美元的销售收入。可口可乐公司的管理高层想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办法,即改变原有的饮料配方。最初,这种想法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可口可乐,几乎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个美国的标志,这一点是其他罐装饮料商无法比拟的。无论是饮料瓶身那广为人知的轮廓,还是反衬着亮红底色的手书白色商标,都已为大众所认可。可口可乐的商标是世界上最流行的商标之一,这个标识已经成为美国的象征,就像“母亲”牌(美国著名品牌)、苹果派和棒球一样。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一家咖啡馆展出了一张不同寻常的照片,它摄于著名的圣马可广场。这张照片是在钟楼顶上拍摄的,这座同时也是警戒塔的钟楼高达325英尺。照片上有数千只鸽子,在广场上啄食早已摆放好的鸟食。鸽群看起来有点混乱,但大致形成的图形却准确无误,正是可口可乐的标志!有谁愿意冒风险改变饮料配方呢?在这场激进改革之后,后果又是什么?如果公司生产出一种新型可乐,再冠以“新口味”或者“改良口味”的字样,这对可口可乐公司的未来发展是否能起到积极作用?分销商们又是否愿意将这种新饮料介绍给年轻的消费者?这种饮料是否能够在“婴儿潮”(Baby Boomer)一代充斥的市场上与百事可乐一争高下?1984年,现实情况不容乐观。1981年,可口可乐公司的市场份额是24%,1984年下降至22%。鉴于这一令人气馁的数据,改变配方的议题摆在了公司高层面前。管理层选择了才华横溢的市场营销经理瑟尔兹恩·施曼(Sergio Zyman)作为此方案的主要负责人。正是他在1982年将健怡可乐(Diet Coke)投放到市场。这种出于对实际情况的考虑压倒了不同意见。可口可乐的技术部研发出一种全新的、味道更甜的配方。经过初步分析,证明配方里含有真糖(Actual Sugar),不含天(门)冬氨酰苯丙氨酸甲酯(Aspartame)(一种约比蔗糖甜200倍的甜味剂)—一种当时流行的人造甜味剂。在口味测试中,这种味道更甜的可乐,赢得了比百事可乐更好的反响。是将新可乐投放市场,还是继续生产老配方的可乐,这在最初就是有争议的。可口可乐公司里持保守意见的人认为,放弃已经有100年历史的老配方会给公司带来负面影响。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郭思达(Goizueta)认为,对于已经负担了健怡可乐和樱桃可乐(Cherry Coke)生产的瓶装厂来说,同时生产新老两种可乐是不能接受的。

在美国历史上,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产品投放市场行动。然而,仅仅过了79天,可口可乐公司就不得不将使用老配方的可乐再重新搬回货架,并冠以“经典可乐”(Classic Coke)的字样。公众拒绝了新可乐,此产品成了可乐类饮料中的“埃德塞尔”① (Edsel)。口味测试和各种定量定性的研究,都没有揭示真正的事实:美国大众不愿意看到这一历史悠久、深为大众所喜爱的饮料消失。最终,可口可乐公司的主流意见决定了事件的结果。在市场上,新可乐曾经以各种形式又存在过一段时间,最终演变成“第二代可乐”(Coke 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次“绝版风波”之后,可口可乐的消费者们反而更忠实于这个品牌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老配方的可口可乐所占市场份额明显增长,百事可乐公司那无法动摇的、针对年青一代的广告宣传开始显露颓势。与此同时,百事可乐似乎也不再是“让人感觉味道更好的可乐”了。在出版界和广播媒体对新可乐的评论中,大部分是消极的,但也有积极作用,这为可口可乐免费做了数百万美元的广告。每一天,大众都可以在报纸上读到,或者在电视上看到有关可口可乐的报道,而相应产生的影响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可口可乐的市场份额开始回升。郭思达并没有因为员工向公司提出异议,或者因为新可乐方案的失败而辞退任何一个人。这种做法,与斯隆在经历了风冷发动机这个插曲之后的做法是一致的。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公司的股价有所提升。郭思达和他的团队获得了巨额利润。试想,如果作为可口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郭思达辞退了每一个参与到争论中的人,这将会给可口可乐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的员工发出一个信号:公司拒绝任何使组织承担风险的行为,也不希望员工持有异议。玛瑞恩实验室:逐层向上反映埃温·玛瑞恩·考夫曼(Ewing Marion Kauffman)于1950年创建玛瑞恩实验室(Marion Laboratory)。考夫曼在初创制药公司时,条件艰苦,在地下室办公,但凭着他所坚信的几个商业原则,以及1989年和默瑞林公司(Merrill)的一次成功合并,考夫曼将这个小制药公司发展壮大。对于公司成员,考夫曼从不叫他们“雇员”,而是称“同事”。在美国历史上,只有很少一部分高级主管继承了考夫曼的才能。考夫曼能够使主管和地位较低的同事们之间保持一种和谐而充满诚意的良好关系。考夫曼的贡献在于他友善的管理风格。受此影响,他公司里的人都称考夫曼为“K先生”。在玛瑞恩实验室,员工之间的关系良好。考夫曼在鼓励提出异议的同时,还附带着一个重要而有趣的条件:无论同事还是主管,只能向上级抱怨。他把这种体系称为“逐层向上反映制”。这一体系不仅能使高管层更好地了解下级们的不满,而且削减了同一级别的同事们之间那种常见的、互相指责的情况。早年间,当考夫曼还是个推销员的时候,他听到了很多同事的抱怨,但很少有同事愿意冒着失去工作的危险,将这些抱怨传达给老板。这种现象产生了消极影响,这些不满在基层人员之间生根。由于无法传达到管理高层,弊端也就不可能得到什么改善。这种情况让考夫曼觉得,如果采用那些合理的异议,也许会使公司转变成长方向,那些地位较高的决策者们,也应该听到这些来自下级的不同意见。曾经发生在玛瑞恩实验室里的一个实例,可以说明这个体系是怎样发挥效用以及是如何让每个人满意的。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曾经花了数月时间进行调查,最终确定在波多黎各建立一家新公司,这能让公司享受大幅减税。当这个项目即将付诸实践的时候,公司总裁否决了此方案。首席财务官认为,是否能利用这一合法手段以达到减免所得税的目的,对于公司利益来说至关重要。他请求与考夫曼见面,向他提出这个意见。考夫曼听取了他的陈述,表明这一方案事实上也确实有利可图,但接着向他解释说,公司的规模之所以没有扩大,是因为正在开发一个新产品,对于公司来说,这项新产品的短期盈利和长远回报都比可能到手的减免税要高得多。考夫曼的政策向来如此—参考不同意见。他不想让任何人的想法变成所谓错误的观点。由于要求将意见向上级传达,他实行了一套可行性方案以听取不同意见。尽管斯隆与考夫曼的领导风格截然不同,但两人处理组织中不同意见的想法是相同的。他们都采取了鼓励政策,并且都积极听取不同意见。得益于这种态度,两家公司都享受到了这种做法的益处—雇员们知道,他们可以将不同的意见一吐为快。美国军方命令链美国军方采用了一套自上而下的命令链,通过这一可靠的体系,军队高层的命令和决策能十分高效地传达到基层。部队里如果出现了不同意见和不满情绪,人们习惯的解决方法是“去找上级”,这就要求每个遭受了不平等待遇的人,必须要从命令链的低级向高级逐层反映问题。当申诉人员在上一层级没有解决问题,就会得到许可,允许他们向更高一级申诉。很多时候,申诉人的不满在第一级就停止了,因为如果申诉人没有得到机会再向上级申诉,他们的问题就只能在较低的这一层解决。20世纪 60年代,美国军方认为,这种体系很可能会抑制申诉的上报,从而使问题无从得到解决。因为在这种体系下,新兵的合理申诉可能会被认为是对抗上级,申诉人可能会因此放弃申诉。军方高层决定实行一种新的方法,让士兵们能越过层层叠叠的命令链,有机会秘密地单独与军法署署长(Judge Advocate General)谈话。具体的办法是,每月有一个晚上,军法署的办公室向士兵开放,并有一名军队律师出席。上访的信息每周会在公告栏上张贴。这一套申诉体系很少使用,但是,这套体系的存在,给了部队官兵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有一条渠道发泄不满情绪。如果公司给员工提供了一条渠道,让他们有机会表达不满,公司高层很快就会发现,员工们的抱怨反而减少了。原因很简单:员工提出的不满得到了重视。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常见的方法是建立组织化的体系,鼓励雇员们思考对公司发展有利的变革方法。尽管斯隆的公司并没有率先建立这样的体系,但是由于斯隆鼓励员工提出不同意见,所以这样的体系事实上是存在的。风冷发动机和凯迪拉克的案例,则是对通用汽车公司这一政策的明证。汤汁传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做出决定,让生产罐装汤汁的亨氏公司(Heinz Company)转产滑翔机上的塑料配件。这个决策,让当时主要的汤汁生产商坎普贝尔汤汁公司(Campbell)在战争期间大为获利。1945年之后,美国市场上的汤汁产品几乎全部是坎普贝尔汤汁公司的产品。熟悉的红白相间的罐身颜色源于康奈尔大学足球队的队服颜色,还有个俗称叫“大红牌”(Big Red)。这样的罐头几乎占据了超市的所有货架,给亨氏公司留下的空间所剩无几。接下来的25年里,亨氏尝试着从坎普贝尔公司手里夺回一些市场份额,但没有成功。在汤汁市场上,坎普贝尔公司的市场份额上升至75%~80%,而剩下的市场份额,亨氏公司还必须和当地专业生产汤汁的公司进行争夺。亨氏公司夺回市场的第一步是将“愉悦”牌汤汁(Happy Soup)介绍给大众。这是一种给孩子们喝的汤,罐身标以迪斯尼人物,造型也很有趣。这一产品的构思是让孩子在享用自己的汤汁时,同时可以注意到罐身造型。在亨氏公司内部,这一构思遭到断然反对。虽然公司针对这一产品做了很多有趣的电视广告,但产品在市场上还是以失败告终。20世纪60年代晚期,亨氏公司认为,营养丰富、价格较高且大包装的汤汁产品会有新兴市场。公司将新的产品命名为“美国巨人”(Great American)。罐身包装是纯蓝底色上印着红色字母和白色的星星,因为蓝、红、白是美国国旗的颜色,是爱国的标志。广告预算交给了恒美广告公司(Doyle Dane Bernbach)。这家广告公司为亨氏公司的调味番茄酱做过著名的“慢速”广告。然而在接下来的五年间,“美国巨人”牌汤汁在市场上的销售情况从未达到公司市场营销部所预计的水平。亨氏公司内部就此产生分歧,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将此产品退市,还是继续在全国范围内销售。最后的结果震惊了每一个人:公司决定,邀请喜剧明星斯坦·费雷贝格(Stan Freberg)为这一品牌做广告,以提升产品知名度。恒美广告公司的管理层对此十分不满,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广告公司管理层断言费雷贝格将使“美国巨人”牌汤汁损失更加惨重。费雷贝格是位才华横溢的喜剧演员,他曾经为Jeno比萨和Chun King食品公司做过一些气氛欢快的广告。费雷贝格要求对广告全权负责,他甚至拒绝为亨氏公司管理层放映广告样片,也从不与管理层讨论广告计划。“美国巨人”牌汤汁的广告制作费用据说达到了1 000 000美元。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在广告的特写镜头里,出现了当时很受欢迎的好莱坞舞蹈演员安·米勒(Ann Miller)。她在镜头里随着一段引人入胜的巴斯比·博克利(Busby Berkeley)风格的音乐,在一个8英尺高的“美国巨人”牌汤汁罐头上跳舞,汤汁罐被喷水池、一支管弦乐队和在跳踢踏舞的姑娘们所环绕。当米勒轻盈地走进厨房时,她的丈夫面露倦容,问:“你为什么要搞得如此花哨?”广告令人十分难忘,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很多人只记住了那个受欢迎的广告明星,但没记住产品。这一次,亨氏公司和恒美广告公司里持反对意见的人们占了上风。费雷贝格的广告并没有重现他往日的成功,它所达到的效果远远不及他为Jeno比萨和Chun King食品公司所做的广告。亨氏公司的管理层在一开始就应该听取不同的意见。昂贵的广告为“美国巨人”牌汤汁敲响了丧钟,亨氏开始全神贯注于生产突出家庭理念的汤汁,而这一建议,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们早在几年前就提出了。如何应对反对者在组织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们表现过激。这里的问题是,尽管他们的想法是正确的,但公司对他们的过激行为应当如何对待?斯隆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一个方法以应对这些表现过激的人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内,为了避免涉嫌形成托拉斯垄断组织,引起联邦政府的注意,通用汽车公司曾经做出决策:公司将会控制产品在美国汽车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使其保持在50%左右。公司最担心的是,如果公司占有了市场份额的50%以上,就必须接受联邦政府依照垄断条例进行的详细审查,然后被拆分为两个或者更多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市场营销部里的一位年轻雇员坚决支持这一做法。他的态度很坚决,要求将公司分成两个实体后,再让这两个实体尽可能地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这个激进的“分裂再征服”计划,激怒了公司里的资深雇员,他们认为这种不入流的做法会将通用汽车公司毁于一旦。这位市场营销部的年轻人很快变得消极怠工。面对这种情况,通用汽车公司管理高层的想法是:给这个雇员一笔钱然后将他解雇。但是斯隆不同意,他说:“我们不会因为人们有不同的意见就将他们解雇;相反,我们希望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斯隆采取了和管理高层不同的处理方法,他将这位提出异议的经理升职,将他从底特律调往芝加哥的电动机车头部(Electro-Locomotive)。由于凯特林的新发明可以减轻柴油机车头的重量,这个分公司正处于繁荣期。斯隆的评论是这样的:“这种方法会促使这位经理尽其所能,尽量为公司增加盈利,就好像他成了通用汽车公司的高级主管之一。另外,这位经理应离开底特律,因为在这个地方他树敌过多,甚至包括我在内。他在这里已经无法立足。”就这样,斯隆把一个十分得力的人才留在了公司,这样的做法也并未影响他实施那具有历史意义的政策。斯隆的政策是这样的:鼓励团队成员提出不同意见,对员工一视同仁。公司听取异议的好处总体来说,公司在听取异议时,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公司和组织应该鼓励成员互相交流意见;第二,让成员知道如何反映这些意见;第三,永远不要处罚那些因为提出异议而表现过激的人们。这三个基本原则包含了一套切实可行的体系,保证公司管理高层能够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鼓励不同观点在斯隆的领导下,通用汽车公司不仅允许员工提出异议,并且鼓励来自各个方面的异议。斯隆将人员组织成不同的特别委员会,他的职责就是鼓励这些委员会将不同意见统一,达成一个可以普遍接受的一致意见。斯隆的目标是:每一个委员会都能做出经过认真筹划的计划方案。那些受雇于通用汽车公司的新人,很快就能知道,这家公司不仅允许员工提出异议,而且认为这是管理过程中必要的一环。对于斯隆来说,这个鼓励团队成员提出异议的方法,正是帮助团队成员达成一致意见、做到互相理解的渠道。斯隆很清楚,只有出现了不同意见,最终才能达成一致。表达异议在委员会的讨论过程中,使用备忘录是一个表达异议的常用方法。在通用汽车公司,主管们都学会了以备忘录的方法表达异议。斯隆的备忘录论述有力、言简意赅,既是叙述事实的良好范例,同时也极具说服力。事实上,这种备忘录无论是在会前会后,都起到了促使成员提出异议的作用。在会上,这种备忘录可以罗列要讨论的议题;在会后,利用这种备忘录还可以对会议内容做出评论。在很多公司里,都有一套正式的建议体系,以鼓励员工说出自己的想法。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米尔福德市(Milford)的比克公司① (BIC Company),拥有一套名为“出色的构想”的体系,以此满足员工提出异议的需要。公司的每一个新雇员,都会得到一本六页的小册子,那上面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体系。重要的是,如果员工的意见被采纳,公司还会予以一定奖励。位于俄亥俄州托莱多市(Toledo)的德纳公司② (Dana Corporation)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体系,公司要求每位雇员每月向公司提出两条新的建议。雇员能够畅所欲言,这就标志着公司鼓励开诚布公。承认异议正如斯隆反复示范的那样,公司管理层是否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十分重要。无论提出异议的人脾气如何暴躁、态度如何强硬和不肯妥协,都要允许他提出意见。回顾一下斯隆这一鼓励员工提出异议的体系的前两步:公司和组织应该鼓励成员互相交流意见;让成员知道如何反映这些意见。如果在员工提出异议之后马上进行阻止,这两步都是无法成功的。一位首席执行官提供了一个事例,说明在见面过程中,如何控制提意见者的情绪。这位在一家中型咨询公司任职的首席执行官,曾经在西班牙工作过两年,他留意过这个国家特有的斗牛赛。他注意到,在斗牛前,会有一位工作人员对牛的情况进行检查,以确定这头牛在生理上是否适合进行竞技。如果这位工作人员发现牛角或牛蹄有缺陷,他就会禁止这头牛进行竞技。在这个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才能将这头已经被激怒的庞然大物安全带出场地?解决办法是这样的:把六头拴在一起的母牛带进场地,脖子上都系上很大的牛铃。让母牛绕着竞技场转圈,慢慢地公牛会自己走进这支队伍里,平静而又安全地离开竞技场。这位首席执行官在开会时,就会准备这样一个牛铃。如果在会议上,争执升级到人身攻击,或者讨论已经白热化,他就会用力地摇动铃铛,平息持反对意见者的怒火。关于不同意见,还有这样一段往事:有一次,一位同事与斯隆发生矛盾,很多人都认为,斯隆完全可以对此置之不理,当时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律师问道:“既然这位员工如此烦人,您为什么不把他解雇?”斯隆怀疑地反问道:“解雇他?多荒谬的主意,他只是在完成他的任务。”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