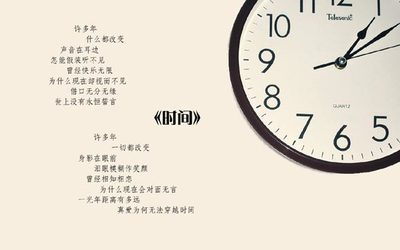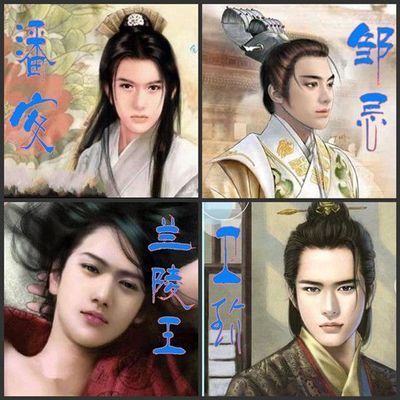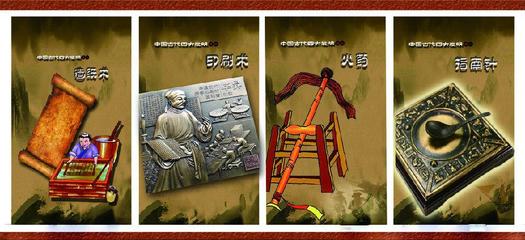图/聂作平 文/李华《蜀都赋》称四川“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而这种情景在自贡更为突出。因盐设市的自贡是井盐发祥地之一,其1800 年的井盐生产史,让许多同类城市望尘莫及。这座兴衰系之于盐的城市,其来历与“自流井”和“贡井”两口盐井有着深刻的渊源,而城中纵横交错的众多街道,其命名也与盐业息息相关。“尚义号”、“宝兴隆”,这些当年的盐商商号便在沧海桑田中变为自贡颇具特色的街名。 自贡在唐、宋时期即成为四川盐业之中心。到了清朝,尤其是清朝末年,自贡盐业更是盛极一时。凿成于公元1835年的燊海井,井深1001.42米,是世界上第一口人工开凿的超千米深井。燊海井的凿成,标志着“冲击式顿钻凿井法”的成熟,此项技术被一些专家誉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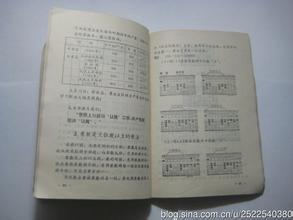
作为自贡盐业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盐井,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具有生产能力,是国内硕果仅存的古法制盐的“活化石”。燊海井以及周围大大小小深浅不一的盐井,共同书写了自贡盐业的繁华历史。从中开采出来的井盐,既满足本地及四川的需求,还通过釜溪河-沱江-长江水道,运抵重庆、湖南湖北和江西等地。 从那些业已发黄的老照片中,我们不难还原出釜溪河上的繁忙景象。这条穿城而过的河流,虽然并不十分宽阔,却是自贡井盐出川的重要通道。河上频繁往来的盐船和两岸的隐隐青山,不仅让釜溪河青春勃发,更让它具有了某种不可言传的诗情画意。而在自贡沙湾码头上,那些忙忙碌碌的挑夫,那些谈笑自若的盐商,同样构成了釜溪河上最生动的画面。 然而,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自贡井盐的辉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候,釜溪河作为内陆航运的功能已经废驰,这条曾经千帆竞发的河流上再也看不到往昔的热闹,只偶尔会有一两只游艇划过寂寞的河面。 洗尽铅华的釜溪河到底还保存了它最原始的灌溉功能,到底还在哺育着三百四十万自贡儿女,而那些同样作为盐业辉煌见证的天车,却已经淡出历史的舞台。 遍布城乡的天车,曾经是这个城市最别致的风景。这些由上等杉木制成的木架,高高矗立于盐井之上,发挥着汲取卤水的重要作用。在自贡所开凿的一万余口井盐之上,几乎都能看到它们曾经挺拔的身躯。不过,在历史前进的滚滚车轮中,在高科技润物无声的渗透中,土法制盐如同一条后继乏力的河流,变得越来越脆弱。真空制盐开创了自贡盐业的新纪元,也为天车的时代划上了句号。失去了实际意义的天车开始被拆除,只有极少数才在专家学者的据理力争中孤独地幸存下来,成为千年盐都的一个旁证。 天车,以及竹片、铁钻、锉头等与盐业密切相关的物什最终都委身于博物馆,以锈迹斑斑的表情犹自诉说着当年的幸福与忧伤。作为历史陈列室的博物馆本身,却也经历了自贡盐业那段风生水起的岁月——博物馆叫“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它的前身是西秦会馆。井盐滋养了一座城市,也致富了城里南腔北调的盐商。那些在自贡这片弹丸之地发了大财的陕西盐商们,在1736年的某个吉利日子,开始了长达16年的西秦会馆的建造工程。他们没有想到,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当遍地开花的盐井大都废弃,当雄姿勃发的天车也已成为历史的标本,这座雕梁画栋的建筑已成为盐业博物馆,迎来了它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