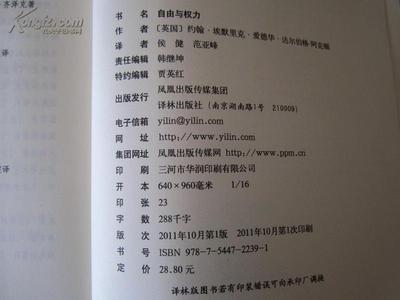我觉得自己现在也不适合做企业,但时代大潮把我们推上了浪尖,结果就做成了

早年诗人,后从政,上世纪90年代“下海”,成为旅游地产大亨
我1956年出生在甘肃兰州,青少年时代在宁夏银川度过。1958年的三反运动,我父亲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判刑三年,他在狱中含恨自杀,两岁的我便戴上了“黑五类子女”的帽子。受大哥的影响,我11岁的时候就加入了当时的民间书友会,因而比别的同龄孩子更早接触文学书籍,12岁时连猜带看读完《西游记》、《三国演义》繁体版,还读了很多泰戈尔、惠特曼的诗,13岁时,《宁夏日报》就发表我的诗歌了。如果我从小不读书,不写诗,我可能就变成一个混小子了,也就没有后来的人生轨迹。正因为大量读书,我才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插队时才能脱颖而出。 1973年,我作为“知识青年”来到银川郊区的通贵公社通北大队。那时候我对自己“黑五类子女”的身份已经非常敏感了,我只有白天拼命干活,晚上向书寻求慰藉,读完了《资本论》——那会看书确实有逃避现实的原因。因为苦干、能干,村民们对我印象非常好,插队仅半年我就入团了,任大队团支部书记,不到一年我就是大队会计了。手握财权,用现在的说法,我是大队的CFO。其实那会儿连算盘都不会打,都是现学的,这可能为我今后干企业埋下了一个伏笔,我对数字、对成本的概念从那时就树立起来了。 18岁生日刚过,我和每个“有志青年”一样,对入党充满向往。但这时候出身问题成为一道障碍,有人提出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子女,多亏大队书记据理力争,我才以“改造好的现行犯革命分子子女”身份入党。那个年代,有些事是很荒唐的。 入党以后,确实有翻身得解放的感觉,出身不再影响我的前途。1975年,军区到我们那里选体育兵,我那时1米88,是通贵公社篮球队的主力,但我没去,我想上大学,后来也有当工人的机会,我也放弃了。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我把握住了人生第一个重要机遇。北大中文系当时在全国挑了一批各省的文化尖子,而我在《宁夏日报》发表过大量作品,党员身份也成为重要加分因素。人生就是环环相扣,上对了路,接着走就是了。 从农村走出来以后,北大的人文环境更让我如鱼得水。北大有一批非常棒的教授,像谢冕、袁行霈,上他们的课就是艺术享受,我之后的诗歌创作就是师承谢冕。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生最好的出路就是进机关,或留校任教。当时中央国家机关就缺年轻人,尤其北大、人大的毕业生,供不应求。那个时候我对国家兴亡的那种责任感、使命感极强。我如愿进入一个中央部委,26岁副处,29岁正处,仕途一帆风顺。 在中央部委,我站在中国政治的最前沿,看到了风云变幻的十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问题最尖锐的阶段,我没错过,而且是近距离参与。我做过人事工作,看过好多人的档案,有30年代、40年代入党的人,经历那么多的运动,现在怎么样?人无法跟政治命运对抗。我继续做下去会是一个好官吏,但这不是我的人生目标,我想离开这个环境看看自己能不能生存下去。我找到陶斯亮(现任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他们正在组建中国市长协会,邀我加盟。1990年,我离开中央机关,进入中国市长协会工作,并出任该协会下属的一家出版社的常务副社长。 出版社的几年,是“惊心动魄”的几年,我对“政治斗争”有了全新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因为其中牵扯很多人、很多事,就不一一言表了。1995年我离开出版社回到中国市长协会任职。而1996年的时候,相关部门出台规定,要求协会与下属企业所有权脱钩。北京中城信息交流中心当时是协会下属的多家企业中的一家,主营业务房产中介,负债50万元。协会决定给它改制,但没人愿意接手,我愿意承担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于是改到我名下,公司也更名“中坤”。现在回头看,我下海实际也是无奈之举,我当时一点不懂房地产,糊里糊涂地就去做了。 我们第一个生意是北京印刷三厂的旧楼改造,挣了两百万。接下来的大项目是“都市网景”,一块别人拿不下、不愿拿的地,我一查,这里当年是军工厂的隔离带,但那家军工厂已经转产了,不再有保密的义务,这块地的性质应该可以调整。我找了很多部门,一个衙门一个衙门地拜,我之前的工作背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要谈成的时候,中远房地产的李明插手了。他是我的EMBA同学,我出项目,他出钱,于是我们联手,这个项目挣了8000万元。 做企业是历史给我的又一个机遇,我赶上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爆发式增长的几年,当初谁能料想房价会涨得那么高呢?我做旅游也是阴错阳差,我的一个朋友在安徽当副县长,请我为该县下辖的宏村投资一、两百万,那是1997年,我当时虽然没什么钱,但是我知道宏村的商业价值,我请清华大学的陈志华教授和当地规划院联手做出了一份保护规划,所以2000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宏村轻松战胜江苏古镇周庄。中坤从旅游尝到甜头,接着又做了新疆的旅游项目。 我有必要提一下我的团队,我现在是中坤集团的董事长,集团总裁是一个年轻人,焦青。他在市长协会时就一直跟着我,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说到团队,我想起了2001年的那场被镇压了的“公司政变”。 我从商是半路出家,一开始思维方式仍比较“官僚”,我最初的创业团队成员都是我的老部下、老同事,我非常信任他们。很偶然的一次,中远的李明跟我聊天,说你怎么又成立一个公司?我这才如梦初醒,原来他们早就私自联合注册了自己的公司,还把公司的一层办公楼的产权也转到了他们的公司名下。我及时出手,平息了“叛乱”,将“叛军”统统扫地出门。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和我在公司战略上存在分歧,不愿我搞旅游,另外担心焦青接他们的班。作为一个诗人,我觉得人性很悲哀,在钱的面前有人真会丧失理智。不过换个角度看,公司洗了个大澡,借势完成内部利益分配体制。从此,一路平步青云,发展得令自己吃惊。 做企业让我得到两种感觉:一个是掌握了权力的感觉,挺自豪的,我能让我的员工富起来;压力就是我可能毁掉他们的生活。再一个就是自由,我不在体制内,一个人在经济上、政治上不受约束的时候,我就是自由的。 我觉得自己现在也不适合做企业,因为我不愿意陷入到具体的事务当中。但时代大潮把我们推上了浪尖,结果就做成了。我们这代企业家是很特殊的一群人,冯仑、潘石屹都不像真正意义的企业家,更像社会活动家。我和冯仑曾经是同事,和我不同的是,他是主动创业。看我们这一代企业家的发展轨迹,很有意思,这批人的背景都是官员、知识分子。而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阶层,从以做官为荣,到做企业为荣,正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大家看到的是成功的,其实更多的人都失败了。 我是个文人,又做过官员,可能在体制内受的伤害太多了,所以现在才知道我做企业是无奈之举不得不做,因为做诗人是活不下去的,所以做了企业我就想活得更好。好在我把握住了每个机会,合着时代发展的脉动,一步步走过来了。我没有浪费我的生命和时间,基本上社会的每一次大潮我都经历了,我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 (采访并整理/《中国企业家》记者齐飞)2007-11-13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