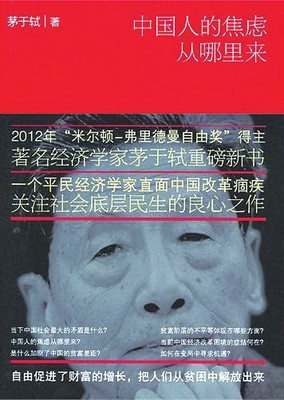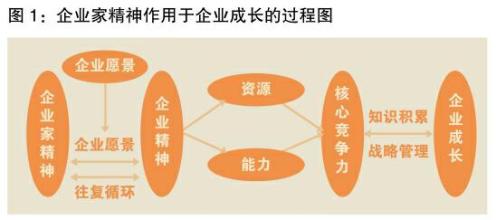朱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
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中国并非“市场失灵”而是“市场不够”
朱敏:茅老,当前这场始料未及的经济危机转眼已席卷全球了,以您的观察和思考,究竟问题出在哪儿? 茅于轼:应该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问题和原因,中国的情况有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是受到发达国家衰退的影响,国内的订单减少;内部原因是低劳动、低环境成本的经济模式亟需调整,属于价格的低估。这是总的原因。具体的原因就要微观分析到个人行为。 朱敏:您是微观经济学的权威,从微观上讲,是否在市场机制上存在问题? 茅于轼: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市场经济也有很多问题,要针对实际问题去解决。中外问题存在着差异,中国更多的是“市场不够”的问题,欧美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中国之所以市场不够,是因为市场配置的资源太少或者政府配置的资源太多,像现在垄断的国有企业都是政府在配置资源,这是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果。改革30年,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还在。 朱敏:微观机制上如果有缺陷,是否最后必定会反映到宏观经济层面?反过来讲,宏观经济层面出现危机,是否必定由于微观机制上存在不足? 茅于轼:宏观经济是总量经济,微观经济是个体经济。宏观经济理论是从凯恩斯起产生的,在亚当·斯密、马歇尔时期都是没有宏观经济之说的,这是凯恩斯的重大贡献。宏观规律和微观规律不完全一样。宏观是总量,微观是通过价格的调整达到供给平衡。总需求和总供给不能平衡,形成了宏观上的种种问题。 微观的最佳状态是:价格是自由的,任何一种商品都能够供需平衡。但是每个微观商品供需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却不能平衡,这中间还存在储蓄转换为投资的问题。再比如说环保的问题,原本也是微观问题,但反映到宏观上就会影响到整体环境。
应“敬畏”市场而非“驾驭”市场
朱敏:现在主要是微观还是宏观层面上的危机?茅于轼:两方面都有。首先价格就有问题,国家可以干预公共交通和电力价格,但绝对不能干预肉和粮食价格,这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必须放开价格管制。
朱敏:管制的动因何在?
茅于轼:权力大嘛,而且不受约束。
朱敏:在目前的政府思维中,究竟对市场是一种什么态度?
茅于轼:政府一方面依靠市场,另一方面干预市场。只有依靠市场,才能生产财富,没有市场就无法生产出财富;只有干预市场,才能在市场失灵时,让权力有用武之地。因此二者都需要。
朱敏:权力的干预,应以尊重市场为前提。前段时间吴敬琏">吴敬琏先生也表达过自己的看法,大意是说,有些官员自认为有了权力就可以无所不能、无所不为,乃至于视市场规律、自然规律为无物,试图“驾驭”市场。中国当前的危机就此意义上讲,是不是这样一种惯性思维的恶果?
茅于轼:这种思维不是一天形成的。“驾驭”与“干预”尽管一字之差,就眼下危机对中国而言,令人担忧的可能正是这样一种问题。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大部分还是投到基础设施领域而非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领域,自然也有对市场认知不够的一面。
应着眼于“隐性工程”而非“显性工程”
朱敏:针对“4万亿”投资计划,您最近大力呼吁政府要瞄准就业而不是瞄准GDP,这一观点亦被普遍认同。您呼吁的依据是什么?
茅于轼:在美国,奥巴马一当选就宣布创造250万个就业岗位,没说GDP要增长多少,似乎不是很关注这一点。在中国,政府部门关心的是GDP,老百姓关心的是就业,如果仅仅是GDP上去了,失业趋势却未被遏制,对老百姓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只是官员在政绩上、面子上好看。当然二者也有关系,GDP 增长也会使就业增加,但是二者不是一种完全对应的关系,瞄准就业和瞄准GDP后果显然不同。
朱敏: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实现GDP增长,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工程”;而通过民生建设提高社会福祉,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工程”。
茅于轼:对,二者在政绩的彰显上有着差异。现在政府部门也存在利益的博弈在里面,存在对显性工程和隐性工程的权衡。比如,究竟如何效用最大化地配置“4万亿”投资?中国现在的总产值约为25万亿,4万亿将近占了20%,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绝不能依赖于显性工程。
朱敏:隐性工程诸多环节当中,颇为关键的一环,在于如何在中国构筑起一个安全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茅于轼:目前社会保障关心的仍然是城市人口,应该将重点转到农村。城市大部分人口都已享受公费医疗,而农民还没真正意义上享受公费医疗的权益,包括教育也是偏向城市。还有住房,纯粹是牺牲农民利益为城市人买房子创造条件,是“劫贫济富”的行为。理应是从富人手里拿过来帮助穷人,现在的模式却是从穷人手里拿出来帮助富人买房子。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并且滋生腐败。
朱敏:越来越多的舆论认为,只有多在民生问题上下功夫,改变国富民穷的状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内需问题进而拉动经济良性循环。
茅于轼:解放初期是国穷民穷,现在也不能说是国富民穷,民间还是很有钱的。确切说是,现在是国家富了,老百姓也富了。现实问题在于大政府、大财政的问题,政府部门的开支很大,并且缺乏监督。
目前财富创造主体已经在民间,民间不富,国家也富不起来。但是富的比例太悬殊,从GDP的分配来看,国家分配的越来越多,包括税收、垄断的国企利润越来越高,表现为国家的财富增加过快,而且手里有大量土地,不够还可以从农民手中获得土地。现在需要扩大内需,减少国家的分配部分,增加百姓的分配比例,比如减税。
朱敏:具体路径您认为有哪些?

茅于轼:除了减税,重点应加大国有企业私有化力度、改革垄断部门和行业。比如铁路,效率低、浪费大、服务差,政企合一。民航和铁路就不一样,民航的服务就好得多;甚至铁路还不如公路,公路因为有竞争,服务有很大改进。铁路还和30年前差别不大。
朱敏:如何打破这种僵局?
茅于轼:铁路的问题是垄断问题。铁路的垄断很难避免,因为有轨道在。这条轨道归谁的,它就有垄断权,除非另外修一条轨道。同样电网也是垄断的,除非另外修网,那可以竞争。从资源配置讲,如果一个网就够了,再建一个就是资源的浪费,电力可能就是这样。不过对于铁路来讲,铁路是不够的,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民间资本。
通过开放“学西方”是30年进步的主要动力
朱敏: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学者指出,对外开放是这30年的最大成果,因为有了开放,通过行政手段获得生产性资源的路径才得以维持。
茅于轼:的确,一个国家的生产性资源如果更多地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可支配的钱就越多,民众口袋里的钱就相应越少,这是一种此消彼长的过程。如果没有开放,生产的东西就可能销售不出去,开放维持了我们外向经济的局面,所以改革和开放要分开来看。
同时也要看到,30年改革开放最不容忽视的力量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的财富并没有掌握在国家手里,市场是削弱了政府权力。
就对外开放而言,最重要的意义是实现了东西方交流,中国得以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没有这一点中国改革不可能成功。开放最主要的结果,不能简单说是维护了统治阶层利益,更多的是促进了中国在技术、制度、文化等领域全面向西方学习。我们的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到法院、律师、大学,还有各种制度等全是从西方来的,而不是慈禧太后的东西。
朱敏: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学习是不是更专注于形式,而精神理念上仍然有着很大差距。
茅于轼:现在精神上也在学,最近出现的维权行动就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真正在学西方的,主要是一些民间人士;作为垄断利益集团,尽管一方面抵制西方思想,另一方面也在受这些思想的影响。
我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发现,中国政治改革一个重大进步是在人权方面。值得肯定的是,几十年一直不断在进步,其实是老百姓对政府的监督权在加强。就“杨佳袭警案”来说,杨佳是该判死刑的,但下此判决还没那么容易,需要照顾到网上那么多的意见。这就是一个进步。
朱敏:您认为进步的动力是什么?
茅于轼:主要就是学西方的关系。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人权思想,儒家没有人权思想,儒家是君王思想,人权思想是“进口”的。先是欧洲然后到美洲,现在全世界都在讲人权。人权不是靠权威来保护的,要靠老百姓的自觉。
朱敏:能否说说渠道的问题?
茅于轼:渠道其实就是东西方交流,包括人的交流、商品和信息的交流。因此说,中国政府对改革开放的功劳很大,我们也去过日本考察,其开放程度远不如中国。
朱敏:现状还满意吗?
茅于轼:终归是能存在、能发展。这全是靠市场,市场的力量给每个公民创造了机会。现在社会上的有钱人,不全是垄断集权者,大部分还是民间的创造力量,经济杰出人物大部分来自民营企业。
微观机制出现新的认知和改进
朱敏:我们注意到您最近在关注一些青年学人的观点,有没有特别推崇的?
茅于轼:经济学以往只强调“理性经济人”追求财富,现在有个年轻人发现了另一个角度,那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比较:“注目礼”。这是个很有价值的发现。
同时也要看到,“比较”并不是人人都赢的,名次是不值得追求的;但是在绝对值上提高,你的财富、学问增加,这是个好的追求,是可以实现的。
朱敏:这个问题可能类似于哲学中“实然”和“应然”的关系。在这里,“实然”是指人跟人的比较属于一种主观机制,“应然”则指人应该有超脱于比较之外的更高追求。
茅于轼:以“帕累托改进”理论看,追求财富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追求名次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改进。因为帕累托改进是在没有人受损的前提下有人受益,而排名次往往非此即彼。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追求绝对值和追求名次的区别了。
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基于人们追求绝对值的行为推演的,没有考虑人们追求名次的行为情形,而现实当中,人的一部分行为是以追求名次为目的,这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以另一种微观机制来解释。他的这个角度,可以视为对理性经济人假设、乃至于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种补充。
朱敏:是否也可以这样认为:理性经济人尽管“实然”却未必“应然”?是不是某种理论假设一旦长期盛行,就会成为一种引导人们行为方式的价值观?
茅于轼:市场经济的成功,其实不是靠理性经济人,而是靠责任感。确切说,市场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责任感。现在90%以上的创造财富都不是为自己赚钱,都是为单位赚钱。花钱也是一样的,现在很多都是花别人的钱,政府也是花别人的钱,社会投资也是花别人的钱。所以光有利己,靠“看不见的手”是根本不够的。一个复杂社会是有组织的社会,它花别人的钱,同时为别人赚钱。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一个客观结果。
朱敏:有人断言,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其实是个“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流于神秘主义。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吗?为什么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不能祛除这个神秘的“看不见的手”呢?
茅于轼:“看不见的手”就是在市场环境下,每个人都为自己利益而努力的共同动机,它是为社会服务的。过去人们认为赚钱是损害社会的行为,亚当·斯密则认为这是为社会做好事。这是斯密的一种感觉,是一种很天才的发现。在人是追求利益的假定下才有了市场,进而有了物质的改善。这不是神秘主义。
复杂市场问题只能靠分散决策解决
朱敏:“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您曾对韩愈的这句话提出深刻质疑:究竟谁是伯乐呢?当时您是一种怎样的心境?
茅于轼:中国人受韩愈这篇文章的影响很深,遇到复杂问题,总是想到应该找一个伯乐来解决。但没有想过:谁是伯乐?怎样鉴别?所以靠伯乐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不是办法。计划经济就是寄望于伯乐的经济。事实上,最后市场的复杂问题只能靠分散决策,而不是靠伯乐解决。
朱敏:市场到底是不是计划的对立面?
茅于轼:市场和计划就是势不两立的,要计划就要放弃市场。问题是要分散决策还是靠集中决策。这说明还是要解决一个决策机制的问题。其实从宏观上讲,决策机制其实就是政治体制,就要考虑民主。
朱敏:您一直奉自由主义为圭臬,那么自由是不是真的不证自明?
茅于轼:自由是需要证明、也是可以证明的,是有逻辑的,并不仅仅是一种感受。
自由的对立面是不自由。为什么不自由?是有人干涉你,为什么能干涉你的自由?就是因为不平等,不平等的社会是不自由的,也就不会安定。人类历史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大家都平等了,就不会有冲突了。问题是大家都平等了,这个社会怎样治理?所以有了民主的办法,人人平等但又可以管理。
特权是自由的障碍,特权的约束条件宽。因为你有特权,就把别人的自由侵犯了,社会就不能安定。
朱敏:更多的是靠法治还是道德层面?
茅于轼:都需要,很多层面都要提高。老百姓的觉悟,老百姓的教育……
(2008年12月10日上午10:15-11:30,与茅于轼先生对话于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全文经茅老本人核定,刊登于《新经济导刊》2009年第1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