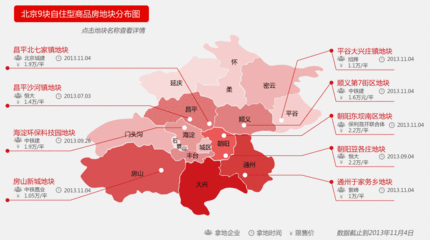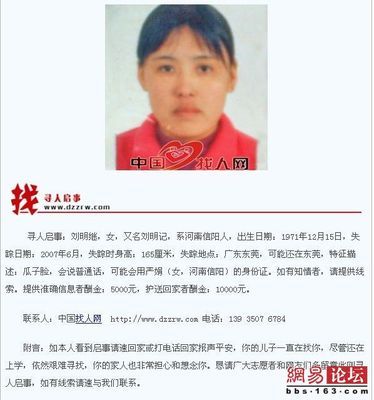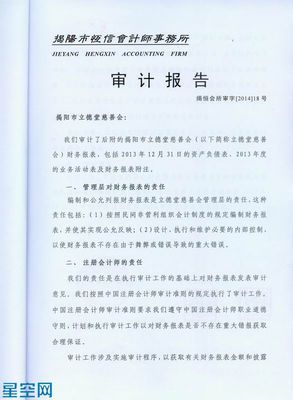自去年底到达上升周期顶部后,宏观经济已进入“调整期”,由于基本面良好,“保增长控物价”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未来调控应加强针对性,以免错失结构调整机遇
中国经济从2001年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后,至2007年底,走出了一波“持续平稳较快”上行的漂亮曲线:经济增速从2001年的8.3%,在宏观调控一路护佑下,至2007年底平稳上行到11.9%,以7年时间,走出高差为3.6个百分点、平均GDP增速10.1%的优异成绩。
就在人们习惯了GDP年年上行、宏观调控年年“控温”之时,今年上半年10.4%、同比回落1.8个百分点的GDP增速,以及1-7月7.7%的CPI涨幅,开始让人们对今年及此后经济走势产生迷茫,加之股价下挫、楼市徘徊,迷茫乃至悲观情绪更被“放大”。
由此,如何判断当前经济形势,不仅成为升斗小民投资理财的“热议话题”,更成为各地各级政府引导发展和生产力布局的关键。
中期:拐点显现,基本面良好
“繁荣顶部未雨绸缪”,是去年底本刊推出的《中国发展报告》中有关经济部分的标题,从目前情况看,这样的判断恰可以说明今天的经济现实。
也就是说,在现代经济仍无法超越而只能尽可能熨平的经济周期中,中国已走过了从2001年至2007年的“上行”部分,2007年经过修正后11.9%的GDP增速,某种程度上成为这根稳定上行曲线的“繁荣顶部”。而事实上,此前成功的调控,已将这条上行曲线熨得相对平稳,一个发展中大国能够保证连续7年没有大的起伏的高速增长,本身已是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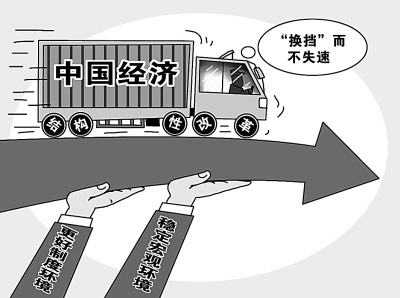
持续的高速增长需要调整,就像长时间高速运转的齿轮需要“润滑”一样,这是本刊近年相关经济采访中王小广一再强调的观点。还是在经济以超过11%增速运行时,这位任职于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学者就认真地向记者指出“持续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自身肯定有调整的需要,否则我们的资源、环境都无法承受,必要的结构调整也无暇进行”。
本次采访,王小广仍坚持这一观点,并认为从现在起,中国经济将进入调整期,而且“这种调整对中国经济而言不是坏事,不调整将更有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立群研究员长期参与重大调控政策的调研和起草工作,谈及当前经济形势,张立群认为目前的增长放缓是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的共同结果。在其看来,始于2001年的新一轮中国经济周期,正是由于近些年以“抑制投资过热”及此后“抑制通胀”为基调的宏观调控,才改变了原本可能出现的大起大落,使这一轮增长曲线在平稳上升的同时被拉长,成就了连续7年的上升曲线。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的经济增速放缓,既是经济自身调整的需要,也是持续宏观调控力避过热的结果,目前要做的是密切关注数据变化,通过预调微调避免经济大幅走冷,而没必要恐慌和担心。
在王小广看来,那些看到上半年GDP同比下降1.8个百分点就觉得“中国经济不行了”的观点,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恐怖言论”。国家统计局8月26日发布的7月经济景气也佐证了上述观点:在对宏观经济各项指标的评估中,7月份的工业生产指数、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工业企业利润、金融机构各项贷款、货币供应M2等指标都处在稳定的“绿灯区”。
8月27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受国务院之托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报告经济执行情况时,亦指出上半年10.4%的GDP增速,仍超过近7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0.3个百分点,目前的经济形势是“高位平稳适度回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关于“基本面没有改变”,宏观层面的数据提供了充足的论据。
一是农业连续实现续第5年增产,夏粮同比增长2.6%,猪牛羊禽肉产量增长4.8%,生猪出栏增长3.7%,存栏增长5.0%,成为保障有效供给稳定CPI的重要物质保障。
二是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改善。我国经济一直以来的投资消费比例失衡、进出口比例失衡问题得到很大缓解,前7个月,在投资增长27.3%,增幅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的基础上,消费增速高达21.7%,比上年提高6.2个百分点,投资与消费增幅的差距由过去几年一直在10个百分点以上缩小为5.6个百分点;以往挠头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也得到缓解,随着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前7个月顺差减少132亿美元,顺差过大造成的种种问题得以缓解。
三是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统计显示,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0.9%,除石油电力以外的其他37个行业利润增长38.4%;而且,随节能减排的推进,上半年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2.9%,降幅比去年同期和今年一季度分别扩大0.12和0.28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
与此同时,上半年进行的国务院机构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及电信业重组、航空工业体制改革等,或全面实施或局部推进;加上继续稳增的城乡居民收入(即便是扣除物价因素,实际涨幅也分别达到了6.3%和10.3%)和全国财政收入(前7个月增长30.5%),以及近年探索出的一整套宏观调控经验教训等,都成为下一步中国经济稳健前行的坚强基石。
近期:在“保增长”中“控物价”
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的“防过热防通胀”,到今年7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保增长控物价”,期间仅仅7个月的时间,中央对经济增长的判断就发生了180度逆转,相应的政策也开始微妙变化,其中原因何在?
采访中,参与相关政策研究的张立群认为原因有二:一是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影响下的全球经济进入2008年后陡转直下,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外需出口、汇率走势和进口价格,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此前对其影响力的判断;二是持续5年的宏观调控举措此前更多表现为量变,但量的累积到一定程度,加之多方因素共同作用,使得调控效应发生了质的变化。
此外年初南方的雨雪冰冻灾害、年中的5.12汶川特大地震,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上述影响经济的负面因素,使得从宏观经济的增长隐忧从二季度开始若隐若现。
相应的,年初严峻的CPI走势,随着连续三个月的指标下行,目前压力稍有舒缓。统计显示,CPI增幅从今年2月份的8.7%到7月份的6.3%,增幅回落已达2.4个百分点。受上一年翘尾因素影响,CPI此后可能还将下行,王小广预计全年CPI增幅在6.5%左右,张立群则认为可能更低。但即便如此,1-7月的CPI涨幅仍高达7.7%,后期仍有可能叠加能源燃料等新涨价因素。
物价压力稍缓,“增长”问题成为高层关注焦点。
整理7月份高层行程便会发现,从7月4日至7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前,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王歧山等高层领导分赴苏沪浙粤鲁等沿海省市调研,并三次组织座谈会,分别听取地方负责人和经济学者意见,两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前,专门听取了党外人士对经济形势的意见建议,其瞄准的问题除物价之外,更多集中在“增长”上。
在此调研基础上,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5日召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问题,将此前“两防”的调控思路调整为“一保一控”,强调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并将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概括为以下四点。
一是物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前7个月的CPI涨幅仍高达7.7%,后期仍存在新涨价因素叠加的可能;二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依然较多,集中表现在农业自然灾害和农资化肥涨价影响农业生产成本上;三是能源资源制约经济发展的矛盾仍很突出,集中表现在能源价格尚未理顺、电力缺口较大,经济增长大量依赖消耗能源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节能减排难度加大方面;四是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集中体现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产行业特别是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上。1-5月,纺织、家具、橡胶行业利润增幅分别回落18.4%、16.5%和47%,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分别增长32.5%、78.1%和52.7%。企业效益下滑、自有资金不足,加上缺少多元化融资渠道,部分中小企业资金面临断裂危险。
基于上述判断,中央形成了“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有效抑制物价过快上涨,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保持对外贸易平稳增长,努力增加煤电油供给,支持中小企业解决生产经营困难”等具体工作思路。
一段时间以来紧锣密鼓出台的各项政策,便是上述思路的贯彻实施。如降低小型微利企业的所得税率;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提高纺织业出口退税税率;出台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提高个税起征点等,此外,中央财政还将安排35.1亿元专项资金扶持中小企业,安排2亿元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等。
“保增长与抑通胀并不矛盾,关键是找准发力点增加有效供给;保增长也不意味着政府的干预一定会扭曲市场信号。事实上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如果政府能选择合适的手段方式帮助企业一把,很可能起到四两拨千金的作用,避免大的调整带来的经济下滑和社会资源浪费”,采访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者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
张立群认为之所以现在要“保”,是因为此前我们持续的紧缩政策已开始发挥效力,如果真等经济冷了之后,再启动要费更大的精力,“比如房地产业,涉及50多个行业,3000多万人就业,真要垮了,牵扯面确实比较大”;在他看来,1-7月的货币仍然偏紧,“还可以再放一些”。而事实上,中央密集调研后的7月19日,银监会在其年中会议上便提出,应“满足正常合理的房地产信贷需求”。
对于持续低迷的股市,王小广认为政府不应无所作为,因为“从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看,他们都非常重视股市,其融资功能可以极大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张立群则认为从去年10月16日6124点跌至目前的2400点左右,目前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只有十几倍,泡沫基本上挤得差不多了,“以前股市有2000多亿资金在里面转,现在只有几百亿资金,而这些资金等在场外也是有成本的,所以如果能想办法让股市涨上来滚起来,股市在下一轮增长中应该是有所作为的”。
此外,王小广认为放缓人民币升值步伐也是缓解出口压力的重要一步,统计显示,上半年人民币已升值6.5%,几乎相当于去年全年的升值幅度(6.9%),如果升值过快,实体经济增长跟不上,自然会带来出口减少、员工失业等诸多问题。事实上,自7月底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出现的连续10天微贬,表明人民币升值策略确已发生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从年初起采访张立群时,他便强调“价格不是今年最主要的问题,重要的反而是增长”,这次接受本刊采访,张立群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从目前国际大宗产品走势和国内CPI走势看,这一观点颇值得关注。
长期:结构调整恰逢其时
谈论中国经济遇到的难题,很多最后会被归咎于“结构性问题”,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经济结构中存在诸多不配套不衔接之处。
比如我们说CPI上涨过快是“结构性”的,源于其中的食品上涨过快,而食品上涨过快则是因为农产品紧缺,农产品紧缺又牵扯到中国农业的竞争力问题,其背后则是整个“三农”体制机制如何适应自身生产力发展及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发展需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非一日之功,更需条件时机成熟后的顺势而为。
再比如目前谈论较多的出口企业生存艰难问题。表面上看是外需减少、生产用工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土地环保成本增加等诸多因素的结果,但去除一些偶然因素我们会发现,一些企业活不下去的根本原因是自身的竞争力低下。
以目前说得比较多的“上半年全国倒闭6.7万家中小企业”为例。财政部财科所的文宗瑜研究指出,过去5-10年每年都有接近5%-10%的中小企业倒闭,好的年景可能有5%-6%,经济低迷的时候可能是8%-10%。而以140万中小企业计算,6.7万家相当于8.5%。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中小企业淘汰比例,而非媒体宣称的“中小企业过冬”。
这就牵扯到如何“保增长”,如何扶持?扶持哪些中小企业的问题,因为“扶持”不好,可能让本应被正常淘汰的企业又活过来,不利于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而即便是每年5%-8%的中小企业倒闭,我国仍是一个产业升级缓慢的国度。中国产业生产缓慢,同样离不开“结构”问题,比如因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形成的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供给,比如因知识产权保护不利和信用缺失、地方保护造成的企业创新乏力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肯定没法像“抑制过热投资”那样立竿见影,而必须在好的时机下多方协调、综合施治和持续努力。
事实上,经济增长进入下行轨道或曰调整期时,恰恰是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大好机遇。原因很简单,产品供不应求,好坏都有人要的时候,企业没有品牌建设和创新动力,如果靠给工人低工资、或出口退税率就能赚利润,很多企业就不会冒不成功的风险去自主创新。而当你800元招不到农民工、1500元自己又没得赚时,才会考虑是不是革新技术,或者转移到劳动力便宜的地方,再或者关门大吉,由此形成全社会的产业升级和产业梯次。
文宗瑜研究员说自己二季度时也去了一趟浙江,发现那里的企业有些困难,有些却出口额、销售额、利润三增长,这表明目前叫得很凶的“中小企业困境”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正常的产业淘汰。而如果这样的企业被政府施以援手,无疑再次阻断我们期盼已久的自然产业升级进程。
所以,对于6.7万家倒闭的中小企业,应该做一个具体分析,哪些是该倒闭的,哪些是成长性原本很好只是因为贷款紧缩被困的企业,应细分之后区别对待,而不要“花钱办错事”。
与之相类的还有“三高”企业的生死问题。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方向是减少“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企业数量和产业比重,目前随着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节能减排带来的环保成本上升,很多“三高”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生存压力:要么增加环保投入进入达标行列,要么转产或者倒闭,而无论哪种选择,对于中国过重的产业结构和巨大的环保压力来说都不是坏事。但如果决策者对此没有清醒认识,一些“三高”企业很可能在“保增长”说辞下再次得到政策扶持,躲过自然的产业淘汰过程。
所以,在“保增长控物价”的同时,必须结合国家总体发展目标和思路综合考虑,切不可“头疼医头”,一叶障目不见森林,错失整个中国经济再上台阶的发展契机。(2008.9.1《了望》新闻周刊》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