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浦东逻辑”说起,盘点中国产能过剩
钱 宏
保持自组织活力,形成自组织均势,是地球人类生态系统得以永续存在与发展的充要条件。如果说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知识形态、自立财富形态和自由权力形态,是一个社会共生主义的运动体系,亦即一个全生态社会建设系统,那么,自组织力及其法则,对于人类、国家、民族而言,就是生态文明形态必然的结构方式。
——引自《中国人应有“大战略思维”》
有人说,外向型制造业与基建型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只飞轮。那么驱动这两只轮子飞快转动的发动机是什么呢?本文试图从一个侧面解剖,揭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密钥。
从1984年地方政府从中央政府分灶吃饭,到1992年中国实行政府型市场经济,并以GDP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及官员政绩的基本标准,全国各省市县乡镇大大小小共计5万多个政府,就历史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5万多台发动机(这里没有把行业垄断性行政公司计算在内)。
自从林毅夫先生用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名为社会主义实际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继而用以描述90年代至本世纪初“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以来,“比较优势法则”可谓深入人心。尤其是手中握有国家垄断资源的各级政府及其官员,可谓心领神会。如果转换成中国人固有的思维和中国话语,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于是,那些有山水可靠并懂得发挥比较优势的群体,1990年代后,便相继在非民粹主义的口实下结成所谓“精英联盟”(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而那些靠不了山,靠不了水的群体,就只有极尽“关系学”之能事尽可量“靠上”一点儿边,或者干脆沦为所谓“弱势群体”这一词汇描述的构件随波逐流。这似乎就是,中国政府在开放条件下取得30年经济增长成就的基本密钥。而且,比较优势理论对于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描述,也得到包括世行组织及外国许多经济学人士的认同。
然而,当人们津津乐道比较优势和中国模式时,却忘记了中国还有另一句老话,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同样,这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比较优势理论,在概括中国模式作为成功案例时固然不泛说服力,但却无法涵盖伴随30年经济增长积累下来的高昂的代价。正如袁剑在《大裂变来了》一文中所地指出的: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对内债务。常识告诉我们,成本不能无限制地向未来转移,也无法永远隐藏在地毯之下。中国经济中的种种不祥之兆暗示,中国经济增长高昂的成本正在进入集中释放周期——这个曾经被我们强行捉进瓶子里的幽灵,正在悄悄从后门回到我们中间。显然,在三十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麻烦周期,或者说是一个还债周期。不巧的是,中国内部这个危险的周期可能与另一个不祥的周期即“全球体系”60多年的外部危机叠加在一起并发生共振。
为浦东逻辑辩护,剖析地方政府谋利动机何以成可能
有人说,赵启正先生的《浦东逻辑——浦东开发与经济全球化》一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土地制度的一种实存描述。我认为也可以看作是相对于“社长(がぃしゃ会社首席执行官)型市场经济”的中国式“市长(行政长官)型市场经济”内在机制的逻辑揭示。
赵先生说:“1993 年,全浦东新区的财政收入只有12亿元,只是吃饭财政,即维持行政和教育支出,而无多少余力投资市政基础设施和开发土地。经过反复研究、比较,浦东决定采取‘以土地吸附资金,以资金开发提升土地价值,再以土地吸附更多资金,并以此推动更大规模的土地开发’的方式,即‘空转启动,滚动开发’的土地开发模式。”赵启正“浦东逻辑”的描述的“空转启动,滚动开发”,创造性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土地制度,在盘活存量资本和可控制资源上,所具有的世界独一无二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在土地私有制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公有(国有-政府有)土地的市场收益,使政府无需额外向公民征税去进行浦东新区的开发,这一机制在中国有着相当普遍的创新意义,甚至,有人指出这种模式和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James Meade) 的“自由社会主义”不谋而合。因为米德认为,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使政府不必依靠高税收来完成公益支出,低所得税率又能促进民间投资(在中国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而非消费服务型投资),因此公有资产和私有资产可以是相互促进的,而不是像流行的“华盛顿共识”所说的相互矛盾的。
但是,近年来批评“浦东逻辑”或“浦东模式”的声音,渐渐多了起来。在此,我想说的是,浦东逻辑是一个创举,它本身并没有错。因为它作为中国急需以CBD模式建成一两个国际大都市,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城市化的典范,其建设主体——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可以说再好不过地发挥了资本欠缺而资源垄断的比较优势,对世界与中国社会而言,正是中国政府具有出色的“自组织力”的一次完美表现。
然而,中国是一个经验主义盛行的地方,不大善创新却十分善于复制。浦东逻辑一出来,人们在对陆家咀那一幢幢仿佛一夜春风来,拔地而起的高楼惊鸿一瞥后,全国各地各级政府考察取经团就接踵而来。于是,浦东逻辑象所有“龙种”一样,一经种到中国其他土壤里,长出来的就变成了“蝗虫”、“跳蚤”。要说是浦东逻辑的错也可以,那么,错在哪里?我想,错就错在它为中国各级各地地方政府谋利动机提供了可行性,提供了“合法”的“可直接借鉴的经验”(再不需要绕湾子的“广东经验”了),错在其核心方法即“土地空转”在中国成为经验主义的样板,1995年后被魔术般地推广到全国孵化,错在中国5万个政府一窝风假借浦东逻辑“循环吹大泡”、“竞相埋地雷”。
为什么这样说?据有关方面2007年统计,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竟有183个城市提出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出于同样的目的,各届政府都会竞相出让土地、变相举债甚至“财政空转”等行为,设法增加当届政府的可支配财力,比拼基本建设投资和形象工程,由此引发债务风险和后续财政压力不断积压。下一届政府明明知道其中内情和债务风险的严重性,但是由于体制性原因,本届政府领导人不但不采取相应措施去积极化解上届政府留下的债务风险和财政压力,而是为了GDP政绩等短期因素,继续强化财政压力和膨胀政府债务,这就是所谓“循环吹大泡”。与此同时,随着财政压力和政府债务不断积累放大,大家也就较着劲地埋下了一个个总有一天会被哪一届政府踩爆了的地雷阵,来个总爆发。所有的秘密,都在本文开头指出的1984年由计划经济全国统筹转变为地方政府财政包干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想方没法一步步将政府性资金来源扩大到这样五个部分: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债务收。其中,除“一般预算收支”(仅占总额的百分之十)需要纳入同级人大的预算审查之外,其他四部分(十分之九),均在政府行政系统之内进行决策和运作。到目前为止,由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还只是处于试点阶段,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得举债,因此,地方政府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和债务收支实际上处于体制外状态。在支出结构上,一般预算支出主要用于保吃饭、保运转,而大量脱离预算审查的其他政府性资金则主要用来搞建设、搞投资。中央财政部2005年发布禁止违规担保专文后,尽管融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地方财政借贷的数量却在逐年增加。据有关方面透露,不但落后地区如此,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也是如此。表面看,在一般预算支出中,地方基本建设资金绝对数不大,所占比例不高,但是,在全部政府性资金支出中,基本建设资金数额很大、比例很高,发达地区尤其突出,有的地方人大预算审查范围之内的地方政府性资金占比仅为1/10。比如中国东部某个仅有156万人口的县级市,年财政收入才3亿左右,而这个市2006年新建成一座设施豪华的政府办公楼就投资2.2个亿,占当年一般预算收入的三分之二。
从民生和社会建设的角度看,为何中国各级各类政府预算外的税、费能够达到16600多亿元?——这意味着减少了6000万个就业机会的社会创业积极性;我们的财政支出结构为何严重失衡?——高比例的行政管理费、经济建设费、投资额等,意味着教、科、文、卫、社保等民生公共物品费用的减少;为何宪法规定的国企(公共企业)为全民所有的产权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不能遵循产权收益全部归产权所有者所有的一般原则,而来自资源垄断的资源缺陷性(租金)升值的巨额“利润”又为何不能全部上缴国库?——这不仅意味着国企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意味着行政任命的全权管理层,及其内部工资奖金分配不需接受人大和公众的监督(其所有财务和重大信息不必向公众披露),而且意味着我们的国企在目的设定上,不是主要提供公共设施,而是提供本应由也完全可能由社会性企业(民企)提供的利润与社会就业,与民争利,且造成社会性分配不公。
尽管我不能苟同杨鲁军《中国城市发展之上海模式批判》一文中的情绪化的立场,这一立场妨碍乃至伤害了文章的公允性,但是,他在文中提出的“声东击西”(指以浦东开发之名行浦西旧城区改造之实)倒也属实,如何评价则是另一个问题。特别是,杨文提出了三种城市发展方式,即:“最经济合理的当属打造新城;其次是存量拆建,即原拆原建;再就是异地拆建,这也是代价最大的一种方式。”我想还不失为中国基建型城市化运动的一种微观描述,甚至对“浦东逻辑”的微观补充。其实,1989年以后的上海,事实上是这三种发展方式都在运用,即既有“打造新城”,即浦东开发,又有原拆原建,也有异地拆建。凭心而论,我倒是认为,上海城市的拆迁,改善了城市面貌,大量的市民从昔日的棚户区搬进了新房。问题在于,是不是全国所有的城市发展甚至城市化运动,都要采用所谓的“上海模式”,恐怕要具体情况具体研究。但有一条,如果城市化的进程和结果是以无限扩张钢筋混凝土建筑物鲸吞国土才农田,固化城乡二元生活结构和消灭乡村生活为代价,那么,这种城市化是绝对不可持续的,其灾难性结果第一是扩大生态失衡和社会分配不公,第二造成中国战略资源的再生性障碍。
顺便说一句,自从国务院2006年10月出台18亿亩耕地保有总量“规划纲要”的“死命令”①以来,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炒房团”及相关产业的“老板”们(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在嘲讽,指责,甚至咒骂温家宝和国土资源部,这正好说明中央政府这件事做对了,做得很英明——“没有办法的办法”,在现阶段的现行体制无法改变的条件下,依然是一种办法。起码延缓、缓解了“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的进一步超速恶化,从而为下一步整体目标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和改善,保留了一些资源环境。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任何时候都千万不要忘了农民兄弟,中国中央政府肯定还会有一种长效的补偿机制,让公共财政合理合法地补给“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者”——可爱的中国乡村居民。历史将记下这一笔。
结论:
本文基本结论:如果说,中国政府对“全球体系”的自组织行为,是北京共识的内在动力,从而创造了包括组织奥运会在内的复制型产能过剩的奇迹,也赢得了世界的赞许与尊重;那么,中国社会对于“北京共识”的自组织行为,才是摆脱“中国30年改革积累的内部危机与全球体系60多年的外部危机”,从而引领世界文明新纪元的原动力。
因此,中国亟需将经济学的比较优势法则纳入社会系统的自组织均势法则之中。
2008年7月29日-8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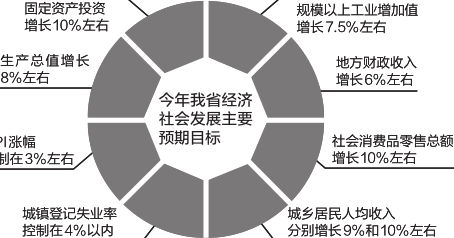
①注:据新华网2006年10月21日报道,10月12日,全国各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部门的规划负责人神色匆匆会聚重庆。他们是在黄金周之后才被临时通知到重庆开会的。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重新部署《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修编的调研工作。因为半个月前,国土资源部上报的《纲要》草案被国务院以“不够严格”为由暂缓审批,重新调研工作随之启动。“总的标准已经确定,就是到2020年时,确保18亿亩的耕地保有总量,这是国务院的‘死命令’。”此后,全国各地各级政府每年有关土地问题的违法、违纪、违规案件数以万计地发生,并逐年增长上升。
本文作者,为凤凰新媒体凤凰博报首席评论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出版集团(总社)编审,“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称号获得者。现任江西省双休日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641679-9.html?time=1219553989#comments5592986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