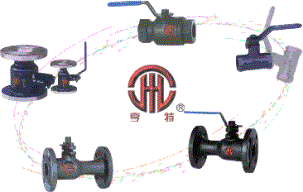2007年11月26日—12月5日,随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团一行到鄂西恩施农村考察,并在三里乡河水坪调查一周,对鄂西农村形成了一些初步的印象。鄂西主要包括鄂西北的十堰地区和鄂西南的恩施地区。鄂西农村是山区,交通不很便利,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湖北其他地区,且外出务工人员众多。这次形成的鄂西印象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是风土人情,二是乡村治理。以下分别述之。
一、家庭结构
恩施农村有“耙耳朵”一说,所谓“耙耳朵”是指怕老婆的男人,这种男人在老婆面前有理无理矮三分,只要老婆在,麻将不敢打,酒也不敢喝。“耙耳朵”最初是对那些怕老婆男人的嘲讽,不过,在现在的恩施农村,“耙耳朵”的评价有了正面含义,大家认为这样的男人顾家,知道好歹。不仅如此,“耙耳朵”数量也增加得很快,在有些村,约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里,男人成了“耙耳朵”。与 “耙耳朵”越来越正面的形象相反的是对女人怕男人的评价,村民认为,如果女人怕男人,则无非是男人自恃力气大,好打老婆,好打老婆的男人算什么男人?有力气到外面使,不要在家要老婆嘛。因此,如果女人怕男人,要么是因为女人作风有问题,要么就是她家男人是个“二百五”、“二黄腔”。“耙耳朵”的数量越来越多评价也越来越积极,不仅表明妇女地位越来越高,夫妻关系越来越好,更表明农村小家庭越来越重要。男人怕女人就让女人当家,这样男人行事就会顾忌后果,逞一时英雄的行为越来越少:不能凭一时冲动与豪气在外大碗喝酒,大把赌钱;因为女人当家管财政,男人想塞钱给父母,回家后钱却被女人搜走。
与“耙耳朵”越来越多,夫妻关系越来越重要相一致,农村家庭中纵向的父子关系越来越无力。恩施农村关于代际间的责任义务的两句话是“收亲完配、生养死葬”,其意思是父母有为儿子娶媳妇、为女儿找婆家的责任,子女有赡养父母、安葬父母的义务。“收亲完配”与“生养死葬”构成责任与义务之间的平衡。不过,在当前的鄂西农村,父母“收亲完配”的责任越来越大,且越来越难以完成。“收亲”是指为儿子娶媳妇,父母不仅要为儿子建房,而且要出彩礼、办酒席;“完配”是指嫁女儿,嫁女儿就得出嫁妆,嫁一个女儿,陪嫁的嫁妆再少也得5000—10000元,而男方父母出的彩礼钱归未来的儿媳,女方父母是不能得的,。总之,无论是娶媳妇还是嫁女儿,父母都得出钱、费力,而无任何好处。近年来,娶媳妇越来越难,置办女儿嫁妆的花费也越来越大。
“收亲完配”的责任越来越沉重,但父母总是要担着,“生养死葬”的义务,子女却承担得越来越少。“生养”主要是在父母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之后,子女为父母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比如一年300斤粮食,几百斤煤炭,每月数元油盐钱。近年来,鄂西农村的多子家庭中,父母几乎都与儿子分灶吃饭;独子家庭里,儿子成家后也大多与父母分为两家。如果老年人没有积蓄,丧失劳动能力后的生活就会十分清苦。如果碰巧子女有病或因灾而贫困,则老年人的生活就更加无人管,情况也就更加糟糕。在“死葬”方面,鄂西农村的丧事仍然办得隆重,花费较大,办丧事仅酒席花费一般就要近万元。
从恩施农村的情况来看,当前农村家庭结构中,横向的夫妻关系对纵向的父子关系越来越构成代替性,成为家庭结构的主轴。横向关系的加强,有利于生成小家庭中软绵绵的幸福生活,却难以建立起家庭绵延中所蕴含的,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的永恒不灭的历史感。家庭结构的这种变化,与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的消退,大概是有密切关联的。
二、消费方式
2007年猪肉涨价幅度之大,恐是前无古人了。2006年生猪价格才2元多一斤,到2007年已上升到7元多一斤,上涨数倍。猪肉价格如此之高,我以为农民是吃不起肉,尤其是恩施山区收入不高的农民,更会舍不得吃肉。
奇怪的是,在恩施农村,农民似乎并未因为猪肉涨价,而少杀年猪及少吃猪肉。他们在吃肉方面的舍得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在我所调查的恩施三里乡河水坪的四个村,村民历来有杀年猪的传统。无论多么贫穷的家庭,到了腊月,一定要杀猪,杀后的猪肉先盐腌,再用树枝熏熏,可备全年所需。在四个村调查,农民户均杀两头2—300斤重的年猪,杀得最多一家是八头!杀三、四头年猪的农户则十分普遍。调查中有个农户只有老两口在家,两个儿子都在广东打工,今年准备杀三头年猪,三头年猪毛重共千斤左右,市场价值6000多元。杀这么多年猪好象不划算也吃不完,老人则说,过年时儿子们会回来,平常也有亲友走动,怎么会吃不完?至于划不划算,养猪就是为了吃肉,哪有什么划算不划算的?
与村民舍得杀年猪舍得吃猪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恩施农民人均收入相当低。按地方政府的统计,恩施农民人均收入仅1000多元。这个人均收入当然是不包括农民用于自食的年猪的价值的。那么,该如何看待用来自食的年猪的价值呢?在恩施,农民人均耕地较少,但坡地多,农民除了种粮食以外,就是养猪。种粮为了吃饭,养猪是为了解决油水和营养问题,两者都有很强的自给自足性质。农民不可能买猪饲料来养猪,那样喂养成本就太高,年猪就杀不起了。山区有各种野菜,山坡边上还可以种玉米、红薯、土豆、萝卜等,这些都是很好的猪饲料。农民基本上是将喂猪当作一项事业,当作农业生产的一部分,每天打草寻食来养猪,养猪主要花费的是劳力,而不是资金。年猪买是买不起的,尤其是分开单过的老年人,根本不可能有现金去买猪来杀。另外,养猪主要是为了改善生活,而不是为了赚取现金收入。因此,猪喂肥了,就应杀掉自己吃,而不是拿去卖。农民养猪吃肉的计算方法,与市场条件下现金收入最大化的计算方法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如果按市场价格来计算年猪价值,则恩施农民的生活水准是相当地高的。其实也是,如果以农民每天人均三两猪肉为一般标准,这里的大多数家庭都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一家三口,人均三两肉,即一年杀两头肥猪的标准。这正是恩施农村杀年猪的平均水平。恩施农民注重吃,因此看起来没有人营养不良。一方面人均收入低,一方面又注重吃,且吃得好,则恩施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就会相当地高。若用恩格尔系数衡量恩施农村的生活水平,就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形了。尤其是与北方农村相比较,比如我们调查过的陕西关中、河南安阳及山西运城的农村,三地农民人均消费猪肉一年有30-50斤,仅及恩施农村人均猪肉消费量的1/3,且三地农民的人均纯收入都要高于恩施农民的近一倍。可见恩格尔系数的不可靠。
恩施农村户均杀两头年猪,日常的生活支出相当高,但恩施农村仍然是贫困的,住房相对比较简陋,有钱的农户也很少。相比较而言,吃在农民生活中所占的地位高得有点离谱。再看北方农村,那里的农民更在乎住房而不是吃。在河南开封农村调查发现,农民本来有冬暖夏凉的砖瓦房,刚建不久并且宽敞、结实,却非要拆掉再建楼房,因为村里很多人都建了楼房。为了建楼房,农民节衣缩食,甚至不用电,以节省电费来建楼房!不用电也要建楼房,在开封被称作“有志气”,而恩施农民则认为这是要“虚面子”。在恩施农村,农民是瞧不起要虚面子的人的,吃都吃不好,年猪都不杀,建那么好的房子给谁看?

相对于河南农村竞赛似的建高楼房,又往往无钱装修,且仅仅讲谁家房子高、谁家是楼房而不是砖瓦房的外观竞争,在住房建设上面,江浙一带农村乃至南方农村更强调“内秀”,强调住房的内部装修。修建了楼房却没有象样的内部装修,在江浙一带是相当不体面的事情,甚至是很丢人的事情。而在北方农村,哪怕是用碎砖烂瓦建的房子,只要是楼房,就觉得比砖瓦房上档次,有气派,感觉好。
此外,有些地方的农村青年特别喜欢买摩托车,开起来风光!全然不顾买摩托车的花费和摩托车是否有实际用途。有些青年还玩起了手机,他们换手机的频率甚至可能高于城市中等收入阶级。
农民的消费习惯在不同地区有着十分重要的差异,在不同年龄群体之间也是如此。此处我们主要讨论的是一差异。有的地区重视短期的吃喝,认为还是吃喝了最实在;有的地区认为吃得再好别人也看不到,因此穿衣最重要,穿得光鲜、干净、整洁,才是最重要的;还有的地区认为吃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修建房子。建房是需要有长期积累和长远预期的事业。但建房子是为了给人看还是要自己住起来舒服?北方农村似乎更是为了给人看,南方农村似乎更关心自己住得舒服与否。但南方农村住房建房上如此强调内秀与外观的一致,难道仅仅是为了自己舒适而没有作给人看的成分?
三、打工经济
河水坪是三里乡的一个中心集镇,四周是山。所谓坪,就是一块相对开阔的平地,河水坪约有2000亩耕地,主要种植水稻。河水坪的这2000亩耕地分别归周边5、6个村所有,每村有几百亩耕地,算上山坡边的坡地,人均耕地仍不足一亩。在没有矿产资源的情况下,农民可能的收入来源主要就是种田和养猪。而种田和养猪的主要目的都是自给,农民的现金收入非常少:虽然恩施农村的生活水准并不低。因为现金收入少,农民就很难盖得起砖瓦房,也买不起电器。到1980年代末,作为区域性中心的河水坪才有两栋水泥修建的平房,农民很少买有家用电器。此地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远低于湖北省的平均水平。直至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恩施农民人均纯收入也仅有1500元左右,仅及湖北省其它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半。
当然,农民纯收入的计算方法也有可商榷之处。在1985年前后,恩施农村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外出务工的收入远高于当地农民务农的收入。外出务工因此在1990年代成为潮流。目前,恩施农村劳动力的一半左右外出务工,农民主要的现金收入也来自于外出务工。
外出务工对恩施农村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因为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价格是全国性市场的价格,这个价格远高于恩施农村一直以来的劳动力价格,在这个价格的参照下,之前的大多数经济行为都变得颇不合理,恩施农民的经济行为因此发生重大变化。
2001年开始修建穿越恩施农村的宜万铁路,将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标准搬到了当地山村。宜万铁路正好经过河水坪,修建时间长达数年,需要大量当地劳动力,技术工人的工价在每天70元左右,一般工人的工价也在50元左右。两个工价都远高于当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时雇工的价格。在1997年,农民雇工的标准是一天8元,到了2004年,雇工种田则一天至少要40元,且要好吃好喝,还要送一包烟。连吃带喝,一天的工价约在70元。这个工价,无论如何是当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所难以接受的。由此,在恩施农村,农业生产方式越来越粗放,越来越多的农田被拋荒。
从上,我们可以大致划分出打工经济对恩施农村产生影响的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可以看作是,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对所有山区农村经济及社会状况产生影响的一般化形式。
第一阶段是1985年前后,因为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形成,恩施等缺少现金收入的山区农村的农民开始外出务工,以赚取现金收入。外出务工的目的只是为了从外面赚钱来补贴家庭农业经济之不足,尤其是用于需要现金支出的建房、娶妻和上缴农业税费。农业生产和家庭经济的传统格局并未发生变化。
第二阶段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劳动力外出使得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明显不足,尤其是子女外出后,在家务农的老年人不得不在农忙时期雇工经营。最初只是请亲友来帮忙,但自家子女在外打工赚钱,却让亲友来义务帮忙种田,从情理上说不过去。于是村子里开始出现花钱雇工的现象。雇工一天8—10元,另外供吃供喝。因为只是农忙时节雇工,且雇工所要报酬不高,农业生产仍可以照旧进行。
第三阶段是2000年以后,外出务工的收入有所提高,村庄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已外出务工,农忙时越来越难以雇到劳动力,雇工价格直线上涨的同时,对所供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为此只能在最关键的生产环节雇工,农业生产的一些细节越来越简化,农作越来越粗放。务农越来越不能赚钱。
第四个阶段,就是当前农民一方面不得不高价雇工经营农业,一方面不得不渐渐地放弃从农业中获取收益。近年来,恩施农民退耕还林的积极性很高,因为退耕还林,每亩可以得到230元补贴,在一些坡地,即使没有得到退耕还林的指标,农民也已经不再种地而自动退耕了。河水坪最肥沃的水田里,以前是春种水稻、秋栽油菜,因为栽油菜太费工,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栽油菜。三里乡因油菜产量高曾是湖北省百强乡镇,现在几乎无农户栽种油菜。不仅无人栽种油菜,种水稻的工序也越来越简单,农民越来越愿意用机械代替人力和畜力。更重要的是,有的农户因全家外出,土地无人耕作,就干脆将土地无偿转让他人耕种,不收一分钱的转让费。
河水坪地理位置较为中心,是居住、建房的好地方,山上的农户都愿意将房子搬到平地居住,他们购买坪地农户的责任田,每亩的价钱在1.4—1.6万元,买来的耕地用作建房的宅基地。上面的政策不允许土地部门收费(只能收5元的宅基地办证费),而土地部门审批宅基地的费用又远高于办证所收的5元工本费,为此它拒绝管理土地,农民买耕地建住房的现象在河水坪一带因此泛滥。
与受打工经济的影响,农业生产发生巨大变化相对的,是用于喂猪的坡地山田的经营。山田主要种植喂养年猪的作物,一直以来采用间作和连作的种植方式。间作是指春季种玉米,玉米间作黄豆。连作是玉米地套种土豆,土豆在五月份收获,玉米在七月收获。收了土豆,即在玉米地套种红薯,等到红薯收获后即种萝卜,到了冬季即开始播种土豆,到第二天春季收获萝卜,同时在种有土豆的山田套种玉米。由此,在同一块山田,可以连续种玉米、黄豆、土豆、红薯、萝卜等多种作物,而种这些作物,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喂牛养猪。可见,为了年底能杀两头年猪,农民在山田所费工夫也是很多的。如果将种坡地山田和喂猪的工钱算起来,则喂年猪成本也极高,甚至高过市场上的猪价。
问题正在这里。如果农村的老年人也以市场价格为参照来计算自己的劳动力价值,虽然这些劳动力实际上不可能外出务工,却因为有了一个全国平均水平的劳动力价格,而不再能投入到不划算的喂养年猪的生产劳动中。按此种逻辑行事,这些农民就不得不一方面无事可做,一方面又无年猪可杀,无猪肉可吃。当前恩施农村的部分未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正处于此种一方面闲着无事可做,一方面又有事而不愿做(因为按工钱划不来)的状况。打工经济使得农民有了一个理性的计算方法,这种理性计算使得劳动力与劳动对象分离开来。
四、村组干部
取消农业税后,村民组长似乎就没有作用了,因为村民组长在取消农业税前的主要作用就是协助乡村干部收税。恩施农民的负担不重,向农民收取税费虽然也不容易,但还没有难到非得给村民组长高报酬以调动其积极性的地步。在取消农业税前,河水坪一带的村民组长的年报酬也就150元,相对于湖北省村民组长平均1000—2000元的报酬,是很低的。尽管村民组长报酬低,取消农业税后,恩施仍然和全省其它农村一样取消了村民小组长。
不过,取消村民小组长后,农村有些事情办起来颇不方便,且村民组往往是由生产队演变而来,生产队是农村土地基础的所有权单位,一些地方便以种种名义恢复了村民组长的设置,恩施农村以综合治理中心户户长的名义,替代或者说恢复了村民组长的位置。在乡村干部看来,中心户户长就是村民组长,只是中心户户长一般不拿报酬,仅仅记下误工费,一年的误工费也就是百元左右。中心户户长虽然不在乎报酬,却很在乎这个荣誉。中心户户长职位具有社会性收益。此外,乡镇政府每年年底召开总结表彰会,每个村都会有1—2名中心户户长受到表彰,除发奖状外,还有200元的奖金。
三里乡擦查坡村的刘书记用三点概括中心户户长的作用。首先,户长是本村民组情况的“情报员”。每个村民组的情况,只有本组村民最清楚,他们天天在一起,时时都见面,谁家状况如何,本组村民都是十分清晰的,中心户户长有责任和义务也有能耐将本组情况向乡村报告,村里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中心户户长会,让中心户户长报告本组情况。村民组内特困户的情况,其它各种异常消息,都可以通过中心户户长及时“上传”;第二,他是国家政策的“宣讲员”。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村干部理解后要向农民宣讲传达,但往往缺少有效的渠道,如果村干部召集村民代表、党员和中心户户长开会讲清楚了政策,而这些中心户户长们有的是时间和机会与周边的村民交流。这样,村干部只要说通了中心户户长,中心户户长理解了国家政策,则中心户户长就有能力将政策传达到每个农户那里,有时间和机会与每一个农民进行细致的交流和讨论。与宣讲员类似,中心户户长往往还是各项典型示范的示范户,比如说擦查坡村建的小水窖和沼气池,都是先在中心户户长家建成示范,村民再跟进。中心户户长往往是在本村民组有威信的人,由他们宣讲、示范效果就十分地明显;第三,中心户户长是处理村民组内矛盾的“调解员”。村民组内有什么矛盾,村民在无传统组织权威可以依靠的情况下,往往会先找到组长,当农民无处可求、无路可走时,他们也就首先想到中心户户长。涉及村民组利益的屋场转让、土地流转、山林边界划分等,也只有中心户户长作为中间人,才能有效地处理和解决。更重要的是,现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村婚丧事的办理也成为难题,尤其是丧事,因为要找较多的人来抬丧、开坟等,就必须由中心户户长来协调本组在家的人力,甚至要到其他村民组找人来帮忙。
以上述及的中心户户长的三种身份:情报员、宣讲员和调解人,大致可以勾勒出中心户户长在当前农村的作用,而最为根本的则是,正是村干部加上中心户户长,再加上村中党员和村民代表,形成了一个农村基层的组织网络,这个网络使得人财物外流的农村,仍然可以留有消化国家政策,解决农村面临各种问题的能力。在恩施农村调查,发现村干部其实可以很忙。之所以说“可以很忙”,是因为村干部若消极工作,不做事情,也是可以的。但若他们积极工作,则有大量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事情可做。以擦查坡村为例,最近一年,村干部在全村建了37口小水窖,解决了相当部分村民吃水难的问题;建了42口沼气池;推动全村村民种烟叶和甜柿;保证农民合作医疗100%的参合率;向上级争取到两笔残疾人危房改造金,并组织村民为这两户村民义务维修住房;讨论确定了全村11户20人的低保户安排(为确定低保户,村干部召开多次村民代表、党员和中心户户长会,最后一次会议长达六个小时,讨论极为激烈,同时又很公正、公平,没有人因为不公正而上访);村干部一般还要调解数十次纠纷,还要协助处理村里的红白事,尤其是丧事。如此等等。积极、主动的村组干部队伍和农村基层组织网络,使得农村社会有了应对快速变迁的社会的能力,也有了接应国家的好政策和救贫济困的能力,从而提高了乡村治理的能力。
还可以提一笔的是,擦查坡村刘书记说到选中心户户长的条件时,特别强调要选敢于说直话的人。说直话,意思是不仅敢说,而且说得公正、公平。在农村人财物不断流出,传统也快速流失的背景下,农村的原子化状态越来越严重,若有人敢于说直话时,村庄中的舆论力量至少就会有一些,对原子化状态带来的糟糕境况也会有点应对之力。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