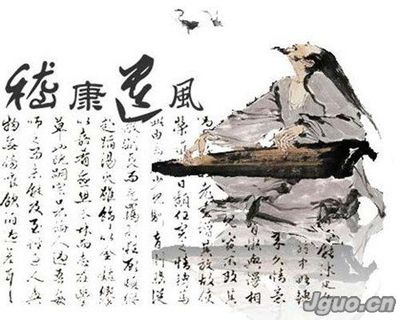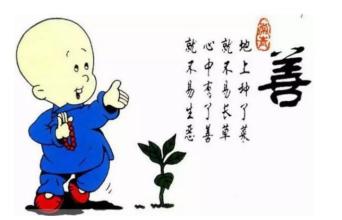在常规的阅读印象中,旅行文学总在主打一种情绪:鼓励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走出去,尽情释放青春荷尔蒙。但很多书在迅速满足了读者对外界的新鲜感之后,便就此停住,不再深入,鲜少有对人生的体察与反省—即便书中有些真实的情感,表达手法熟练,却也不免在公式化的写作技巧中流于浮浅,多半逃不出快速消费品的命运。 这类文学的鼻祖,当属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书中描写了一群青年因信仰迷惘,而企图在公路上行走中获得生命的力量。可是在经历了狂喝滥饮,耽迷酒色,放纵之后,却依旧感到虚无。这种情绪,恰迎合了当年上世纪70年代美国嬉皮士文化风潮,战后时代安逸的生活使得青年人失去了精神的方向,于是便期待着借用反叛,来打碎自己青春的迷惘。但正如美国哲学家艾伦·布卢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所说:“这种生活其实和他们摒弃的生活一样空洞虚假。选择不是存在于一时的兴奋或者枯燥的算计之间。” 《十五颗小行星》恰巧在这个我们承平已久的工业化速食年代,“不合时宜”地谈起了人生应该如何选择的问题,曾获得2010年台湾《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及2011年台湾金鼎奖“文学奖”。刘克襄,作为台湾开启自然写作风潮的人物,一直以其自然、淳朴的文风,被视为“最懂得在台湾旅行的人”。此前,他的写作一直集中在对自然的保护和观察上。比如对流浪狗(《野狗之丘》)、鸟类(《永远的信天翁》)、铁道(《11元的铁道旅行》)等。而在这本书,他将视角从自然投向人群,转为对每个单纯、执著生命的悲悯。 整本书以书信体的方式,展现了15个生动的人,就像放电影。视角定在台湾,透着乡土气,有来台湾山林纵走后失踪的外国人鲁本,也有台湾首位登顶珠峰的拾方方,有从台湾走出去的旅行者三毛,也有放弃大城市繁华生活而开创有机家园的老五。刘克襄作为线索人物,步伐轻轻地走遍了这15个小故事,他既是参与者,更是旁观者。15个单纯的人,实验了人生的一种可能性,即遵从内心的意愿选择人生,脚踏实地地将其实现,以致最终能够骄傲地对时代的枷锁和命运的羁绊说,“我是自由的”。 比如“鹰人”沈振中,因为热爱老鹰,于是一生都试图用老鹰的视角看这个世界,或者赤脚而行,或者经常模仿老鹰的姿态。书中有张配图,夕阳西下,在大自然中,沈振中全身赤裸,背脊向前弯,双手抬起模拟起老鹰起飞前的样子,放松舒展。可乐、汉堡包、手机、互联网中,居然还有这样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没办法用成功与否衡量。 在《云豹还在么》这个故事中,记录了一个执著追寻台湾云豹脚步的小伙子。上大学时,因为“没有办法啊”,他选择了念资讯工程系。但最后,他依旧天真率性地选择研究台湾云豹,一种几乎灭绝的动物。在这个过程中,他同时面对了调查途中女同伴被山洪卷走的残酷打击……“或许是树灵不满我在他们身上架自动照相机吧;或许是我打扰了山里人祖灵的清净所以要我也不得清净……应该是山神在生气吧,带走了恩师和阿秀。经常想起他们时都会偷偷掉眼泪……”

而刘克襄亦在这旁观的同时,找到了为无序人生重新排序的方法:只有遵从内心真正的召唤,才能定位自己的人生,释怀得与失。刘克襄说,当17岁的儿子感慨人生没有意义,想要靠染头发排遣时,刘克襄仿佛看见了年轻时候的自己—这是生命的轮回,每一代的年轻人都需要以自己的方式找到“慰藉的出口”。每个生命都需要打磨,思索,最后才能散发属于自己的明亮。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