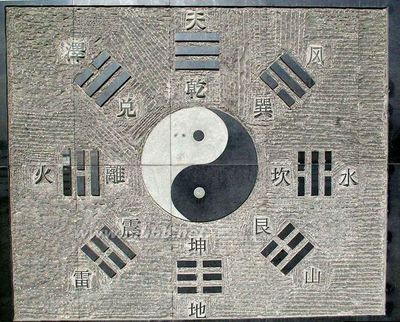系列专题:劳动合同法
2007年最重要的两部法律,很可能是《物权法》和《劳动合同法》。《物权法》为整个市场经济奠定了产权基础,《劳动合同法》为市场经济中劳方与资方的合同关系奠定了基础。据说,全国人大公布《劳动合同法》草案后,总共收到近20万条意见,创造了全国人大立法史上的新记录。事实上,这部今年6月通过、明年1月实施的法律,已经引起了企业的强烈反应。
9月,中国知名高科技民营企业华为公司要求所有具有8年以上工作年限的7000多名员工自动辞职,随后再签订新的雇佣合同。10月,全球最大的流通企业沃尔玛拟在全球裁员200人,其中中国区占了一半以上,涉及沃尔玛采购系统的深圳、上海、莆田和东莞等四个分部。据说,在6月之前,一些大企业甚至就开始裁减工龄较长的员工。由于华为的影响力,相信有更多的企业对此拭目以待。
华为、沃尔玛裁员与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究竟有何关系?如何从全局角度来看待《劳动合同法》?针对企业的规避法律行为,有关部门应该怎么办?这一事件可能给我们提供哪些深层次的启示?本文将就上述问题进行经济学及法律经济学的分析。
一、华为、沃尔玛裁员所为何事?
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组织。因此,企业裁员的主要原因,要么是成本变大,要么是收益变少。华为公司网站数据显示,从2002年到2006年,华为的销售额从175亿元一路增加到656亿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55%。显然,华为裁员(或温和地说“调整人力资源”)一定是由于成本上升。沃尔玛一度是2001-2005年“财富500强”第一名,2007年再次夺得第一名。“财富500强”根据企业的销售额排名,可见沃尔玛的收益应该没有减少。从成本角度看,由于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中国成为沃尔玛最大的供应国,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的总部也设在深圳。因此,沃尔玛不惜对包括深圳在内的采购系统进行裁员,原因也是成本上升。实际上,无论华为和沃尔玛是否承认,成本上升都与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不无关系。
为什么《劳动合同法》会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呢?因为《劳动合同法》提高了企业雇佣和解雇员工的成本。具体地说:(1)违约成本提高。《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第十条),并必须约定报酬(第十一条)。(2)“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使企业解雇长期雇员的成本提高。《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或者连续两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十四条)。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在企业裁员时享有优先留用的权利(第四十一条)。(3)使用试用期雇工的成本提高。《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只能和同一劳动者约定一次试用期,试用期最长不超过6个月(第十九条),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正式工资的80%(第二十条)。(4)大量裁员的成本提高。《劳动合同法》规定,企业裁减20人以上或者10%以上的员工,必须提前30天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听取对方意见并且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第四十一条)。(5)解雇成本提高。《劳动合同法》规定企业用人单位必须给予员工经济补偿,补偿标准为工作一年补一个月工资(第四十七条)。(6)使用临时工的成本提高。《劳动合同法》限定“非全日制用工”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小时(第六十八条),报酬不得低于最低小时工资标准(第七十二条)。
依据上述规定就不难理解华为和沃尔玛的举动了。华为让大量工作满8年以上的员工辞职,很明显是为了规避上述第二点,即避免公司出现无固定期限合同雇员,从而减少以后的解雇成本。而沃尔玛则很可能是针对上述第四点,即通过提前解雇避免以后大量裁员的困难。公平地说,《劳动合同法》在某些方面提高了企业的成本,但在另一些方面也保护了企业的利益。例如,允许裁员的情况比《劳动法》更宽松了;规定员工的保密义务以及竞业限制。何况,无固定期限合同工的出现有利于员工形成长期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与企业建立更加紧密的雇佣关系,这对一些高科技企业和专业服务业企业是有利的。当然,企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组织,好处不嫌多,成本却总是嫌高。因此,华为、沃尔玛的举措不难理解。
二、不同的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率

静态地看,《劳动合同法》似乎保护了工人的利益,加重了企业的负担。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从博弈的角度讲,市场经济的主体除了企业,还有作为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居民(如工人),以及作为市场管理者的政府。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通常是有效率的,但是市场经济可能导致不公平的分配结果。众所周知,在企业和工人的博弈中,企业由于其在组织和资源方面的优势,拥有强大的力量;工人则由于过度供给和缺乏组织显得弱势,拥有很少的谈判力。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很可能导致企业越来越强大,而工人越来越弱小,这种谈判力的不均匀分布最终将导致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即雇主和工人分别处于财富的两个极端,这种分配不均匀进一步加剧了下一轮分配的不均匀。极端地说,如果政府不为社会最终分配的结果设定某种目标,那么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也是符合帕累托效率的!但是这样的社会显然是危如累卵的。因此,如果政府要维持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就必须对禀赋进行某种合意的再分配,使调整后的雇主和工人的禀赋仍然位于“契约线”上,这样的社会经由市场竞争仍然可以到达帕累托效率,此即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禀赋通常包括财富、自由和谈判力等,在本文的话题中,主要指谈判力。因此,政府通过立法适当提高工人的相对谈判力,这是将追求社会正义与提高经济效率相结合的必然选择。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呼吁保护弱势群体。
从历史上看,通过立法提高工人谈判力乃是趋势。肇始于18世纪下叶的工业革命,在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劳动者和资本家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19世纪之后西方国家纷纷进行劳动立法。1802年,英国通过《学徒健康和道德法》,开现代劳动立法之先河;法国1841年通过《童工、未成年工保护法》;德国1918年通过《工作时间法》,明确规定8小时工作制;美国1935年通过《国家劳工关系法》,规定工人可以组织工会与资方集体谈判。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新中国没有理由在劳动立法方面落后。
从动态的角度看,通过劳动立法适当提高工人的相对谈判力,长远来看对雇主也是有利的。现在内需不足,是因为广大工薪阶层缺乏购买力,进一步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太少。通过立法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一方面提高了工人的收入和购买力,这是一阶效应;另一方面,有助于工人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和利润,这是二阶效应。简单地说,如果一个社会中穷人没有购买力和劳动能力,富人的钱从哪里赚呢?
三、明线规则:让工人拥有更多谈判力
抽象地说,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法律、制度乃至人与人之间的所有交易关系看作是一种契约。这种契约从合同要件的角度,可以分为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所谓完全契约,就是契约毫无遗漏地规定了所有情况下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并且这种规定可以被法院执行。所谓不完全契约当然就是不能规定所有情况的契约了。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现实中的契约通常是不完全的。而法律,作为一种粗线条、广为应用的契约,更加是不完全的。为什么要从契约完备程度来分析呢?因为契约不完全可能导致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进行事后的敲竹杠。比如,在雇佣契约中,雇主可能借口工人没有完成工作目标,克扣、拒付工资,甚至解雇工人。因为劳动合同通常不可能详尽地规定“工作目标”这种难以被第三方(如法院和仲裁机构)证实的合同要件。敲竹杠会导致效率损失,也有碍社会公平。
在工人和企业的博弈中,工人通常处于弱势,因此更容易成为被敲竹杠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弥补不完全契约所带来的效率或公平损失呢?不完全契约理论提出的主要方法是,赋予工人更多的事前权力,即直接提高工人的谈判力。例如,《劳动合同法》规定,在没有“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正常情况下,劳动者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第三十七条),但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则必须对劳动者进行经济补偿(第四十六条)。这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问题是,法律本身也是不完全契约,因此通过立法提高工人谈判力的做法效果未必很好。比如,怎么从法律的角度定义“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销售额减速增加算不算经济情况恶化?
因此,我个人提出另一种解决方法,就是在不完全契约中增加更多“明线规则”(bright line rule)。所谓明线规则,是指很容易判别的临界点,即法律中的强制性规范。比如,规定工人每小时工资不能低于5元人民币,这是可以被法院证实的。理论上,明线规则可能限制了当事人的最优选择。但是考虑到敲竹杠问题,适当的明线规则有利于从最低程度上保护当事人的人力和物质投资激励。可以证明,敲竹杠的风险越大,明线规则越是容易改进效率。现行各国劳动立法中,关于书面合同、最低工资、8小时工作制和经济补偿等内容的规定,就是我说的明线规则。
回到华为、沃尔玛等企业规避《劳动合同法》的难题。显然,企业在节约成本和挑战立法当局的权威之间走钢丝。《劳动合同法》是法律,是法律就有契约不完备的问题。立法当局应该如何通过明线规则来保证法律得到有效贯彻呢?我的建议是,先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在细则中限制企业的恶意避法行为。例如,规定企业在正常经济情况下解聘员工后,一年内不得与员工再签劳动合同。如此一来,那些被华为解聘的职员很可能在一年后流失到其他企业,华为将为此得不偿失。同时,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发布《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实施之前发生劳动合同纠纷时的判决依据和适用判例,提高企业避法行为的经济损失。当然,这又导致立法和司法机关如何协调一致的问题。
四、《劳动合同法》凸显几大隐忧
适当地超越华为、沃尔玛裁员这个具体的背景,我觉得这次《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当前立法和司法的一些隐忧。
首先,立法应取得广泛共识。法律作为一种制度,应该是一个博弈均衡,应该使当事人能够并且愿意履行。一些企业在《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之前仓促裁员,也可能是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缺乏了解,以为这种合同是终身雇佣合同。立法部门在立法过程中,应该广泛发布和解释法律草稿,同时与企业等利益相关者充分沟通。此外,司法部门应该预期到法律的事后可操作性,不能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中国企业、事业单位还有大量的临时工,《劳动合同法》如何适用于保护这些人的利益,这可能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难题。
其次,立法当局面临政治压力与司法效率的权衡取舍。《劳动合同法》以“四读”的方式在今年的人大常委会议上通过,不能不让人将其与今年发生的山西奴工事件相联系。该法居然没有提到与《劳动法》的关系,而且关于书面契约、最低工资、裁减人员和劳动仲裁等方面的规定明显与《劳动法》重复,其仓促可见一斑。
再次,保护工人利益的根本办法仍然处于政治敏感区域。资本主义国家尚且准许工人通过组织工会来保护工人利益,但中国对于工会定位、组织架构的规定,仍然使其在保护工人利益方面备受掣肘。如何让集体行动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发挥作用,这是对政府的考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讲师。作者感谢江艇、宁红丽、王菁和吴锦宇提供评论,但文责自负。)
《西部论丛》2007年第12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