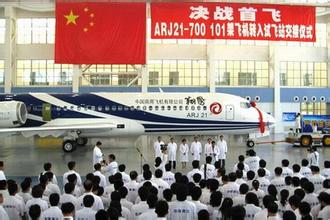1999年元月7日,牟其中、夏宗伟在北京街头被刑事拘留,拘留时拘留证上的“拘留原因”一栏空白。
1999年11月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南德集团涉嫌“信用证诈骗罪”一案,夏宗伟和牟其中一起站在了被告席上。
2000年5月30日,牟其中被判犯信用证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夏宗伟免予刑事处罚。
4年来,夏宗伟只身一人开始了漫无止境的搜集证据、写材料、打报告、上访申诉之路……
艰难讨“说法”
赢:对于你个人来说,四年来不断地搜集证据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夏:几乎从出了看守所我就着手做这些事了。当时老牟已经被判无期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判罪,但他坚信自己无罪。老牟的孩子在国外,我在南德原来管的事情挺多,就觉得这事我不能不管。安顿下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情况。
我先从证据材料、文件部分入手。当时公安已经把南德所有档案材料都没收了。公司档案当时有好几大屋子,后来还到我手里只有很少一部分,包括老牟自己写的报告和一些往来信件。我就从手里仅有的材料入手,觉得稍微有点关系的,就找出来,探监的时候给老牟看,通过这些材料唤起他的记忆。通过他的回忆,我再去调取其他资料,同时也寻找公司当时的一些当事人,让他们写证明材料以便将来作为旁证。
搜集到眉目清楚了才觉得有些欣慰。但刚开始两眼一摸黑,不知前面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确实很痛苦。我所能做的就是一点一点地去获取、去搜集,像拼图一样去还原真相。因为我是被判过罪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不配合;有的人跟案件有利害关系,会在其中制造各种障碍。最困难的是,我绝大部分时间是身无分文,单枪匹马、行囊空空地在做这些事情。很多时候我不得不考虑去弄一点“饲料”,把个人生存维系下去,才能接下来继续奔忙。
赢:从被判决有罪开始,你们就决定要不断地申诉下去。是什么促使你坚持不断申诉?
夏:到2000年7月,随州法院有一个公告通知民事庭对此案恢复民事部分审理,当时老牟已经有点失去信心了,总觉得案件已经被“政治定性”,再重审也没有用。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管他们听不听,至少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法律身份,我们是被告,有这样一席之地我们就有讲话的权利,就有机会把事情真实的一面说出来,而换在别的地方没人听你讲,讲完之后也不会记录在案。
开庭之前要阅卷,当时案卷有好几千页,不可能在那里看完,我就随同律师全部复印了一套,搬回来慢慢看。结果越看越生气,我想材料里明明不是那么回事,为什么就那么判呢?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刑事辩论时竟然没有一个辩护律师完整接触到这些案卷。
当时大家觉得是特批过的案子,再怎么样也无能为力了。我的想法就是,不管是谁批的,只要我有事实证据,请你对着证据说话,在证据面前请再批一回。恢复民事审理之后,我马上就提出必须要去应诉,因为我觉得这是惟一一个可以了解和反映情况的正规渠道。
民营企业的法律尴尬
2003年1月18日,受南德集团理事会委托,国际刑法协会副主席兼中国分会主席高铭暄、中国法学会刑法研究会会长赵秉志、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黄京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龙翼飞等4位著名法学专家,依据大量相关材料,对牟其中刑事案进行了充分、严谨的论证。得出如下结论性意见:“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单位南德集团暨被告人牟其中等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一审判决与二审裁定据以定性的基本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应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本案予以重新审理。”
赢:去年1月法律权威们作出这个认定以后,对于事情有没有一些推进和帮助?
夏:北京的法律专家是从纯法律的角度进行论证的,他们做了这个结论之后,没办法再去进一步推进这件事。但这个权威的论证结果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舞。此后我们做过很多努力,联系了多家媒体。除此之外,我也将这些材料递交给有关部门。因此,对案件有所了解的人肯定越来越多。但是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一个部门出面来解决这个事情。可能觉得这个案子太大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不归我管就不管……所以,整个事情的前前后后,当你在不断地获得希望的时候,也随时要承受难以承受的失望……每当我多收集到一点材料,觉得重审的可能近一步的时候,就增加了一点希望和信心;但每当递上材料,碰到冰冷一片,没有反馈的时候,我觉得心里又……
(夏宗伟说到这里,忍不住叹气,话音断续,情绪显得非常激动。)
赢:从南德集团卷入经济纠纷,你本人也成为被告开始,到现在都五年了吧?
夏:将近五年了。南德遭遇这个打击之后,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我被判有罪的时候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出来以后,通过搜集证据和不断跟律师接触才了解到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应该让公众了解事实真实的一面。有一次,我抱了一大堆案件材料在马路边一个店里复印。一个市民扫了一眼,看到“首骗牟其中”字样的标题,就开始愤愤地评论:“我最痛恨这样的蛀虫!”我在一边听着,眼泪都出来了,恨不得踢他一脚,要与他辩论一番:老牟不是骗子!。后来我想,你踢他也没用。老百姓看媒体上都义正词严地进行道德审判了,跟着骂个痛快是很自然的。1999年的时候你讲什么都没有用,因为当时的媒体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大环境跟以前有很大不同了。最少媒体已经开始了解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我就期望通过媒体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件事,让了解的人多一个、再多一个,直到引起社会关注,或许能够对解决问题有所推进。
赢:在你为南德案件争取重新审理机会奔忙的过程中,南德集团的民营企业身份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中是否遭遇到一些求诉无门的尴尬?
夏:要是国营企业,可以先找上级领导,或主管部门出面,这样会更有说服力,更引起对方重视。轻工上有经贸部、交行上有总行。而南德是民营企业,只能靠自己跟发生直接法律关系的司法部门对接,比如对于高级人民法院,南德上头没有跟他们对等的“单位”。因此一些按法律来说属于可答复可不答复的问题,法院往往就不答复我们。
我手头有一份湖北轻工的报告,报告里说,刑事开庭之前,他们跟交行、中行的人都就此案向有关机关做过汇报。按理说如果调查案情,你应该听每一家被告单位的意见,可是当时从来没有任何机构来找南德正面调查此案。
我们也尝试过去找工商联,但工商联对于企业而言只是一个行业性的协会组织,不存在直接的行政管辖关系。南德集团原来曾是全国工商联的直属会员,但出事以后这层关系也就不存在了。我以个人身份去找人家不会接待,以企业身份去找,他们的态度不是很明确。毕竟,有些事他们也拿不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我们说谁都靠不上,自己挨门去磕吧。
申诉至今杳无回音
两次民事审理以及专家的意见,让牟其中重拾信心,他一直坚持自己无罪,并委托夏宗伟写下包括证据在内厚达151页的申诉书,递交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也抄送给中央10多个部门……
赢:申诉材料递上去之后有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答复。我征询过律师,法院方面即便是驳回申诉,一定要写明驳回的理由。也许上面暂时可能还不便协调或有其他原因,反正目前还没有一个机构作出回应。但是从法律程序的层面来讲,无论如何必须给我们正当的刑事申诉一个合理合法的答复。
赢:从法律的程序上来说,现在应该是哪个部门应当对牟其中的申诉作出反应?
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是直接办案单位。我的材料是直接特快专递,并抄送了最高人民法院。前阵子我还打过电话去问。对方说材料是看见了,等等再说吧。
赢:你觉得推进此案重审的最大阻碍在什么地方?
夏:最大的阻碍和最大的希望都在于民事判决结果和刑事判决结果认定的法律事实的矛盾。

1997年这个案件是作为一个民事经济纠纷开庭的。当时南德集团的态度是“我认这个账”,并且愿意按照法院的判决来担负南德应承担的责任,该赔谁就赔谁,并没有不还钱的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纠纷,湖北中行是原告,湖北轻工是第一被告,贵阳交行是第二被告,南德集团是第三被告。如果按正常程序走下来,还款责任次序应该是轻工先归还中行的钱;交行作为担保方,在轻工还钱的基础上把钱还给中行;最后是南德和交行之间将担保生效之后的经济关系理清。
当时如果给南德一定的时间,南德还有这个还款能力。但是,我们申诉难就难在这里,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讲,肯定不希望这个事情再推倒重来,把事情暴露出来。所以这就是申诉背后的一些东西,牵涉到方方面面。
2000年8月22日刑事判决终审裁定南德集团犯信用证诈骗罪,判处牟其中无期徒刑。而2002年7月12日的民事判决终审裁定则确定了刑事判决所依据的三大证据文件均为伪造,“南德集团与原告(湖北中行)之间无直接的信用证法律关系”。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依据的事实基础就不一样,这本身在法律上就是非常矛盾的。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不可能拿民事判决的结果直接去推翻刑事判决的结果。这使得民事判决书本身在措辞上也十分矛盾和含糊:头一段引用了刑事判决书的内容作为大前提,后面“经本院查明”,才开始说民事查明的结果。并表明“对南德集团应承担的责任,本案中不予处理,有关当事人可另行起诉。”
民事审判结果下来之后,按这个判决结果,交行方面还是要赔这个钱。于是交行也提出申诉,又拿出了刑事判决书的那套说法,即“南德属于诈骗行为,我们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事情就拧在那儿了。
赢:那么交行的申诉是否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回复?
夏:他们的申诉实力比我们强,没几天就得到最高法院的回复,说裁定民事要重审。这个回复我是在几个月后才知道的。但现在不管是民事重审还是刑事申诉都还没有动静。其实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重审,都有可能回到事实的本来面目上。但这可能需要最高的部门出面来处理这个事情。
赢:除了通过法院途径,还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争取到案件重审的机会?
夏:我还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向全国人大、政法委、人大法工委等反映情况,因为它们有对案件影响和进行监督的职能。只要有30个人大代表联名就会成为大会议案,一定能得到答复;只要有一个人大代表给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案发信,最高法院就必须以书面形式给予回复。我目前正在广泛联系,我想,全国有这么多人大代表,应该会有理解并愿意为这件事出面呼吁的代表吧。
赢:你估计案件重审的可能性有多大?
夏: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无论如何中国的法制还是在进步,整个大方向让人感到欣慰。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战胜现在的痛苦,争取有朝一日得到一个公正的答案。我还是有信心的。
赢:在这个过程中,据你的了解,牟其中在心态上有什么变化?
夏:一开始刑事判决下来之后,老牟几乎被无期徒刑的事实给压垮了。那时几乎是落在深井底,而且找不到往上攀的岩石。后来事情有些转机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强的“活下去”的信念——只有“活下去”,才有机会弄清事情的真相。他确实是心理调节能力很强的一个人,但是这次入狱毕竟不比头两回,年纪更大了,身体更差了,还增加了很多心理压力。目前,他已经由无期改判有期,可以要求“保外就医”,但是湖北这边暂时还没有批他的“保外就医”。监狱里虽然资源有限,但他一直尽量阅读书报跟外界的发展保持同步,经常思考一些问题。商业是他的爱好,做生意是他的本能,他始终放不下。如果能出狱,我相信他还是雄心勃勃地想再干一番事业。他现在心情很好,就是迫切想出去做事情。我也经常安慰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急也急不来。现在,保重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赢:经过这么多事,你个人对老牟有什么评价?
夏:他是一个太理想化、太执着的人。由于太执着不会转弯,也由于太执着得罪了不少人。他不是一个喜欢享受的人,他享受的只是对于“新的生产方式”这一思想的实践和推广。
赢:你自己也改变了很多吧?
夏:我原来像个小孩似的,什么都不操心,天真快乐。直到这件事情扣在头上。我进去的时候还不到30岁,现在都快35岁了,居无定所。天天面对着监狱、法院、公安的人,我觉得自己脸上的肌肉都已经不太会笑了,心里头也老有一根弦绷着。现在惟一觉得放松的时候就是有好的能牵情的电视连续剧办完事就心里欠着去看一看只有在那时我才会随着剧中人的喜怒哀乐放逐而彻底忘却眼前的苦恼。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