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1期
[关键词] 生态文明 生态文化传播战略 政治社会化 社会政治化 内在关系存在论
[摘要]包括生态危机的“现代性危机”,以及生态经济新的发展趋势预示着一个崭新的生态文明形态的到来。生态文明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也是生态文化主体的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问题。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的俗文化的感性文化层次,对前者进行理性升华的雅文化的理性文化层次,雅文化政治化的政治文化层次。生态文化理念的传播过程有一个生态“政治社会化”带动生态“社会政治化”的规律与战略。其关键是观念性知识分子成为取得生命的内在自由的生态文化的先进教育主体,在公共领域进行生态文化的政治社会化的话语传播的实践,从而建构生态政治的合法性,使现代人确立“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内在关系存在论”的生态思维方式,使人与自然形成两种和谐的关系:“主体间”的存在体验关系,“主体-客体-主体”的实践认知关系。进而建立符合生态正义的绿色差序格局和谐发展的理治社会。
一、 生态文化理念传播的前提:“生态经济”的现实基础与“生态文明”的必然前景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1]发展“循环经济”之新的“科学发展观”成为我国的国策,这既有一个全球化发展问题背景,也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逻辑:
首先,全球化进程所造成的“现代性危机”特别是“生态危机”使发达国家认识到传统的发展模式已行不通了,必须改弦更张,实行“生态经济”,这预示着一个崭新的“生态文明”的发展前景。
工具目的理性的“现代性”导向下的现代化使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付出的代价有二: 一是主体异化、“德性传统失落”的意义危机,一是自然人化功利目的化、自然生态破坏所带来的“生存危机”,我们通称之为“现代性危机”。
对包括“生态危机”的“现代性危机”最敏感的西方的思想界,20世纪以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危机”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其中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一批后现代主义学者,主张“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 “这种建设性的、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真理和真理观与前现代真理和价值观的创造性的结合。”[2]企图在现代性辩证否定的基础上,企图重新恢复有机论的“返魅” (reenchantment)的世界观。
注重实际问题的专家、企业家科学家们则发动了绿色和平运动。1968年来自十个国家30多为专家学者在意大利著名企业家、经济学家A·佩切伊的倡导和主持下集会罗马探讨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形成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指出人口、经济、粮食、污染和资源五个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决定因素,其中后三个因素组成的“有限制的系统”与前两个因素组成的“增长的系统”的冲突不可避免,将会造成“生态萎缩”,因此增长是有极限的,应采取“零增长”经济发展战略。专家们指出发展问题以后,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社会开始出现风起云涌的绿色和平运动,成为一股影响很大的政治势力。他们提出了“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绿色政治”的思想。在此历史背景下,联合国1972召开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倡议。
最终到20世纪八九十年,发达国家政府认识到,传统的增长模式行不通了,必须改弦更张:为了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以生态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了“循环经济”发展思路,形成了新的经济潮流。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循环经济已成为经济的重要产业和普通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日本2000年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社会的理论。美德日还建立循环经济的立法,从制度上保障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是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的经济形态,实际上是生态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
包括生态危机的“现代性危机”,以及生态经济新的发展潮流启示我们,这不仅仅是个现实全球化发展问题,而且预示着未来一个崭新的生态文明形态的到来。“现代性危机”从社会文明的视角来看就是现代工业文明危机。人类文明已经经历了不同的形态:狩猎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其中,狩猎采集文明和农业文明从精神实质来说属于“神圣文明”,工业文明则是理性的世俗文明,是对神圣文明的否定。“现代性危机”表明:工业文明已经陷入不可自拔的危机中,已经完成它的使命,正在从兴盛走向衰亡,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将逐渐取代工业文明,成为未来文明的主导形态。人类文明的演进曾经经历了一个从古典朴素的生态文明,到现代科学文明的过程,将要经历一个“后现代的生态文明”的否定之否定的文明转型阶段。由于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而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及相关的文化价值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为文明转型。当前随着绿色技术的出现、循环经济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核心的生态价值观念的出现,人类文明将必然转变为“生态文明”。
其次,中国的发展面临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严重的人地资源矛盾和生态问题,迫使中国采纳、响应西方的“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人民正凯歌高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些发展问题。中国发展问题有许多,正如学多专家反复讨论过的:中国存在社会剧烈转型所带来人欲的膨胀与的共识信仰瓦解的矛盾问题、社会阶层贫富分化以及沿海和中西部的发展矛盾和差异问题、行政权力无限扩张所造成带来腐败问题、特别是人口的膨胀、经济的增长与有限的生态资源矛盾问题。我国GDP成本长期居世界前列,单位GDP能耗和物耗远远高于世界先进水平,如不更张发展难以持续。我国资源短缺,原油进口逐年增加,水资源紧张,不少矿藏超负荷开采,全国出现数十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再就业任务艰巨,大批工人下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局部改善整体恶化,水体污染、黄河断流、沙尘暴、江河洪水、非典疫情,凸现了生态问题的严重。正如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第二届“绿色中国”论坛上的发言中所说: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紧迫,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人口的继续膨胀,开始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总量来支撑高消耗的生产方式,我们没有足够的环境容量来承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我们必须强化全民的资源环境危机意识,必须发展循环经济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必须发展清洁生产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成本,必须发展绿色消费以减少消费过程对生态的破坏,必须发展新能源以实现生产方式的彻底超越。唯有如此,我国人民才能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仍生活在安全优美的环境之中,告别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种种灾难,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培育出一个全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和谐的生态文明。[3]
二、 生态文化理念传播规律与战略:先进生态文化主体的生态“政治社会化”,带动生态社会政治秩序建构的生态“社会政治化”
人类要发展生态文明,中国要发展循环经济,这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而更是一个创造全新的生态文明新人的生态文化理念的传播的价值导向问题,亦即生态文化建设问题。
(一) 文化建设有一个社会政治化与政治社会化双向互动的规律
我认为文化可分为三层次: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的俗文化的感性文化层次,对前者进行理性升华的雅文化的理性文化层次,雅文化政治化的政治文化层次,这要由文化的定义谈起:
文化定义是什么?这一直是文化学者、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争论不清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中列举了欧美对文化的一百六十多种定义。我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综合各家的观点,认为文化可分为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社会结构功能系统: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的俗文化的感性文化层次,对前者进行理性升华的雅文化的理性文化层次,雅文化政治化的政治文化层次:
据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考证,从18世纪末之前,西方语言中的“culture”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根据类比--人的培养过程。但是到了19世纪,后面这种文化作为培养某种东西的用法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是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最后,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4]就西方而言,基本能够达成共识的,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化是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这样定义文化:“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5]上述学者所说的“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观点,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可分为感性的社会文化心理和理性的社会意识形式两个方面。
文化与文明的概念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文明是文化的物化形式,恩格斯认为国家是文明的标志,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精神和文明的最高体现。
因此,我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的俗文化的感性文化层次,对前者进行理性升华的雅文化的理性文化层次,雅文化政治化的政治文化层次。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是文化的基础层次,具有长时段的稳定性;知识分子对人民生活方式的理性反思所形成的体现在宗教、艺术、政治法律和哲学中的雅文化世界观体系是文化的核心灵魂;雅文化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的政治文化层次是文化的最高形态即政治文明。
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观点看,俗文化的人民生活方式早在原始社会就存在,原始社会后期几乎同时出现了知识分子的雅文化与国家文明形态。
其后文化的演进,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的雅文化以社会经济变迁为基础的不断更替,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以及国家政治文化的复杂互动,有两种文化演进规律:
一般的自发演进型的文化演进规律是:先是有技术方式与生产方式变迁,然后是观念型人物的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变迁并以人民群众的俗文化为新文化观念创造源泉,建构新的观念体系,为新的政治上层建筑提供政治合法性,接着是行动型人物的知识分子主导下的群众社会运动,建构国家政权,然后是国家政权强化新的政治文化,进行政治社会化,形成新政治文明,新的政治文明缓慢改变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
后发传播型文化变迁的规律是:观念型知识分子学习接受先进文化观念,行动型知识分子以改良或革命的方式主导国家政权,然后进行技术方式与生产方式的变革,政治文化社会化与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冲突面临政治合法性危机,观念型知识分子体悟人民生活之道重构新的政治合法性,建立新的政治文明,新的政治文明影响人民的生活方式。
两种文化变迁的共同规律在于,知识分子的雅文化与国家政权及其政治文化的双重互动关系,包含了双重的过程:从知识分子的雅文化到国家政治文化的过程,是“文化政治化”(the culture politicalization)的过程;国家政治文化影响人民生活的过程则是“政治社会化”( Politics socialization)。
自然的文化演进的规律是是自下而上的“文化政治化”进程带动“政治社会化”,传播型的文化变迁的规律是自上而下的“政治社会化”带动“社会政治化”。
西方发达国家工业文明形成和生态文明萌芽是一种文化自发演进历程,体现了前者的特点,是“文化政治化”进程带动“政治社会化”。如前面所说的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文明萌芽的过程:现代性危机技术方式变迁引发思想者的反思批判,然后是技术专家的绿色发展理念,然后是绿色政治家的绿色政治运动,最后是西方国家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主要体现为“社会政治化”的过程。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演进是一种西方文化传播的现象,因此其规律是“政治社会化”带动“社会政治化”的过程。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国民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革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主要特点是观念型和行动型知识者发动群众运动,掌控国家政权,自上而下推进生产方式、技术方式和文化观念变革的过程。“新发展观”形成和“生态文化”建设也是自上而下的“政治社会化”带动“社会政治化”的过程,这其实是一种生态文化哲学理念的传播的过程。生态文化哲学理念的传播过程是一个生态政治社会化带动生态社会政治化战略。具体来说,就是观念性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现代生态科学文化哲学理念,体悟人民传统俗文化和人民生活的朴素生态之道,成为克服现代性的异化生存方式,取得生命的内在自由的生态文化的先进主体,在公共领域进行生态文化的政治社会化的话语传播的实践,从而建构生态政治的合法性。即通过传播生态文化哲学理念的广义的生态文化教育活动,逐渐转变个人本位的现代性政治秩序为后现代生态社群为本位符合“生态正义”的绿色政治差序格局。这涉及到一下中华传统俗文化、生态哲学以及生态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即前文所说的文化的三个层次。
(二)生态文化哲学理念传播的主体条件:体悟人民生活的传统文化之道,学习西方的先进生态文化和哲学观念,克服现代性的异化的生存方式,取得内在的生命和心灵的本真自由,从而培养千百万生态文化教育的先进文化主体
要成功地传播生态文化哲学理念,建设生态文化,培养尽量多的生态文化的先进教育主体是关键。
1、克服现代性的异化,体悟人民生活之道,恢复生命本真的自由自在
“现代性危机”从主体来说是一种异化的生存方式的危机,人在工具目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中丧失了自由自觉活动的本真的存在,异化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商品、金钱的工具,甚至异化为后现代主义所说的抽象的类像、符号。在现代性的外在庞大外物的统治下,人迷失了自己,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焦虑状态,在后现代主义所说的主体零碎化、破碎化的生存方式中,人处于虚无化“耗尽”(burn-out)的状态,丧失了生存真实感。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由于科技发展,物质资料丰富,已经消除了匮乏威胁,具备了人基本需要前提下过自由自在本真生活的条件,但异化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用“虚假的需求”,刺激人的消费贪欲,迫使人组织起来利用技术无限掠夺大自然,造成生态危机,同时“额外压抑”人的本真自由,使人沦为科技理性专制的奴隶的单面人。
现代性的异化本质上就是庄子所说的“人为物役”,只不过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更为严重罢了。因此重新体悟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逍遥于道”的内在生命自由、心灵的自由的文化理念,对克服现代人消费主义的异化生存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古今中外诸子百家公认自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或价值。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允诺自由与解放,却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奴役悖论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觉悟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只重视摆脱束缚的外在自由,而忽视了内在的自由,或者重视内在的思想自由,而只觉察到心理意识的表层现象,而没有如中华先哲般觉悟到内在本真心灵及其自由。内在的本真心灵自由,是精神所处的无拘无束、无挂无碍、自由自在却与存在融为一体的状态,这种自由是完全由内心决定的,其实现取决于个体心灵对孤独、恐惧、焦虑、苦恼、惶惑等内在因素的摆脱。他同外在自由是个体的显现不同,而是个体融入自然、回归天地、返回原始本源有机联系的“内在超越”的过程,“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这是本真的原始自由的升华,自由就是“是其所是”,是人的本真自然自在状态,而不是萨特所说的“是其所不是”的徒然挣扎的一股无用的激情。这不是神秘的彼岸迷狂,而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道在日常人伦中,是摆脱了手段-目的的功能主义异化的审美的和谐的生活方式,刹那即永恒,生存的当下即存在的显示。作为当代的学者,学习传统文化之道,不是作传统文本的奴隶,而是体悟活的人民生活之道,文化就是当下的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之道就是生生不息的人民生活之流。体悟人民生活之道,是恢复生命本真的自在自由的前提。
2、对传统生态文化哲学、现代生态科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辩证扬弃,确立“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内在关系存在论”的生态思维方式
要养成具有以生态文化哲学为内涵的自由人格,还需要学习西方生态文化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体悟生态自然法则,获得顺应生态法则的外部自由。
生态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新天理”的生态世界观,包含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态价值论。要形成这样一种世界观或文化哲学理念,首先要做西方“自然法”学理传统,中华道学传统,现代诸子百家理论特别是现代西方生命哲学包括存在主义的理论,和健康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之间的对话、交流。另一方面,需要人们在一个漫长时间在一系列生态灾难面前的惊醒与觉悟。前者需要知识精英在“公共领域”讨论交流,传播生态文化哲学理念,后者需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强制,只有现代性社会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人们才有可能觉悟生态天理“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道理的真实不虚。
我们认为,“新天理”作为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应是一种“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内在关系存在论”的生态存在论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所谓“内在关系存在论”,讲的是在存在论上人与自然一体共在、内在统一的关系,这与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体二分为基础的“外在关系存在论”现代性思维方式区别开来。“生态存在论”的基本命题是:“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人以自然而存在”这个命题,说的是人源于自然,以自然之性为自己的“根性”,与自然形成了一体共生、“内在统一”的关系,探讨的是人的“类本质之根性”的问题,这是传统西方哲学所遗忘了的。认为“生”既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本然状态,也同时是人的“类本质”或“类本性”,这种“生”的本性,既是自然的内在规定、内在目的、内在价值,也是人的内在规定,内在目的、内在价值。“自然以人而存在”这个命题,说的是自然靠人的生存而显现其存在,自然以人为其自组织演进的最高目的和价值,人是自然价值的最高体现。这样,人与自然就构成了两种和谐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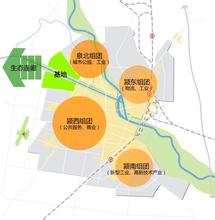
一是“主体间的”存在体验的关系,在主体间基于“生”之“根性”的本真整体体验中,自然和人从本真上被把握为一个生命的主体所共生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人不是中心,自然也不是中心,而是一体感应、共鸣的关系。在存在体验中,自然-社会-人的是自组织、自演化、自调节的三位一体的内在有机统一的生态复合系统。如梅洛-庞蒂从现象学提出“身体-主体”(body-subject)概念作为克服近代主客体思维方式,认为以“身体-主体”把握的人的生活世界是一个格式塔的整体知觉世界,这个整体知觉世界“始终是一切理性、价值和存在的先行的基础”[6],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之间呈现出一种具有“可逆性”(reversibility)的“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梅洛-庞蒂指出在人与世界关系的背后,还有一个不可见的本体,它使得世界通过人显示出来。这种不可见的本体便是大写的存在(Being),这不是传统意义的实体,而是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存在主义的马塞尔也指出,我们不仅要从功利性的“问题”出发,把世界看成分裂的“功能世界”,而且要从“奥秘”的最贴己生存状态出发,把世界体验为一个整体,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不再是一个主客体的“第一反思”关系,而是“我-你”的交流沟通的“第二反思关系”。
一是以主体间存在关系为前提的主客体的实践认知关系,也就是在把世界体验为一个整体的前提下,把握人作为自为主体的对自然有机整体的调控、适应关系,以人和自然的“主客体关系”为媒介,人和人也发生了“主体间”“共在”的关系,即“主体-客体-主体”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当代人与子孙万代的关系是以自然为中介建立起来的平等“共在”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二者互为变量:人与人之间是互相竞争利用的主客体关系决定了人与自然的主奴关系,人与人之间是和谐共感共生的主体间关系则易于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感应共存的主体间关系;人与自然是征服与改造的主奴关系,人与人之间也互相利用争斗不已,而人与自然是主体间的和谐审美或价值体验的存在关系,人与之间往往也易于形成主体间和谐共生的关系。
(三) 生态文化理念传播的关键环节:以公共领域的政治社会化的话语实践,建构生态政治文化秩序
1、 生态政治文化与生态政治社会化:绿色公共领域的话语传播实践
政治文化概念首先是由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提出的。政治文化是人们对政治体系的认知、信仰和情感,是政治体系合法性的所在。从“体系”的观点来看,“政治体系”是一个与“社会环境”有着信息输入和输出的开放系统。按照美国政治体系理论创始人伊斯顿的观点,“政治合法性”本质上是“社会环境”对“政治体系”的一种无条件的支持,即“散布性支持”,所谓“支持”是“社会环境”中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赞同态度,所谓“散布性支持”是“社会环境”中成员对“政治体系”无条件地依附、赞同。[7]在古代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一种神圣的价值信仰,或者来自于上帝创造的“自然法”或者来自于“法自然”的“道”,实际上是神圣文明时期朴素而充满魔力的神圣世界观。这种合法性来源于自然的神圣性,既支持了政治体系的相对稳定,又使政治体系与自然体系按照列维·布留尔所说的“原逻辑”神秘交感的方式有机统一起来,具有保护生态系统的功能。随着马克斯·韦伯所说“世界祛魅”(disenchantment)的理性化的现代化进程,政治的合法性转化为“民意的合法性”和法律程序的合法性,这两种合法性,一方面导致多元主义“诸神之争”,削弱了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强度,导致人们“价值共识”丧失的精神危机,另一方面也割断了政治体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神圣直接的联系,使自然生态系统化约为社会体系包括政治体系征服奴役改造的功能性的物质客体,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包括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的“现代性危机”警示人们,必须在更高层次上回归传统的神圣世界观,既作为政治体系政治合法性所在,也对生态系统起着良好的看护作用。如何才能建设政治文化呢?体系理论主张通过政治合法化的方式。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和大众传媒的途径向社会主体传播的过程,实际上是政治合法化的过程。
哈贝马斯主张以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以语言为基础以“交往理性”为原则的交往行动的话语实践,形成“重叠共识”( overlapping consensus)重建政治合法性。交往性的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是社会交往中人类同胞发生关系,是以语言为中心的导向社会主体间相互理解(action-orienting mutual understanding)旨在达成共识的活动。行动者在相互语言交流的时候,其合理性在于遵循三种有效性规则:事实上是否真实、道德上是否正确、主观上是否真诚。此外还包括语言上的有效性:可理解性 (行为导向的相互理解)达致有效性的方法是论证。论证主要通过交往参与者“对话”或“商谈”(discourse)进行。[8]
这启示我们生态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是形成生态文化的话语实践的绿色“公共领域”,通过交往理性主导下的平等对话,形成生态政治文化的“重叠共识”,这也是生态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即生态政治合法化的过程。只有形成一种生态政治文化合法性的公共领域,才能影响现实政治,使生态政治文化、生态哲学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最终影响大众形成生态价值观信仰,最终建构生态文明。在这个过程中,生态文化不是无用的书生的乌托邦幻想,而是现实的“循环经济”的制度文化保障,实习是政治经济必须的。
2、生态政治秩序建设目标:推天理明人事,建立以从生态社群到生态城市,到生态民族国家或文化共同体,到生态系统,到生态存在的绿色差序格局和遵循生态伦理“生态正义”的“理治社会”。
既然自然生态的法则是整体有机关联的,那么自由主义以原子是个人为基础的社会机械联合的现代性社会秩序观则是生态政治观所必然不认同的,而认同社群主义的观点,把社会看成是有机的共同体,其基本单位是社群。建立以从生态社群到生态城市,到生态民族国家或文化共同体,到生态系统,到生态存在的绿色差序格局。
既然自然生态法则是循环运动且自组织自演化的,那么以社群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有机体的有机秩序也要遵循“新生态政治伦理”的政治生态系统的自组织的生态法则必然是一个各得其所,各有所用,动态循环的具有“社会生态位”(social niche)的分工差序格局。
“社会生态位”的设想,源于生态学的启示。“生态位”通俗地讲,就是生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拥有稳定的生存资源(食物等),进而获得最大生存优势的特定的生态定位。生态位的形成减轻了不同物种之间恶性的竞争,有效地利用了自然资源,使不同物种都能够获得比较的生存优势,这是自然界各种生物欣欣向荣、共同发展的原因所在。人类社会活动主体在占有、生产和分配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资源等方面也存在在“社会生态”中“定位”问题,实际也就是通过适度竞争的“社会分层”或“社会分工”问题:不同的社群与阶层,只有通过适度竞争,正确定位,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这与梁漱溟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理想化理解的“差序分工”的社会格局有相似之处,其不同之点是社会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的状态的符合生态伦理规范“生态正义”的和谐发展的“理治社会”。
生态伦理的核心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主体间(当代、代际)外在社会政治关系的和谐平等的一体共生的社会正义法则:
首先,要解决传统工业经济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的代价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不公正问题,必须以生态法则为基础确立新的正义原则。从经验直观就可以体认到,发达国家发达的经济、良好的生态相当大程度上以对第三世界国家污染转移为前提的,与富裕人口良好舒适的生活环境形成向明对比的是,越是贫穷的人口往往越是处于污染最严重的环境(除去非工业化的个别落后地区)。 “社会正义有环保的一面。它被称作‘环境正义运动’的主张和事业,在世界各地穷人和权利被剥夺者是环境破坏与社会不公的主要牺牲品。”[9]
而从罗尔斯“反思的理性平衡”的视野,假如我们当代理性而自私的人,在一个理想的“无知之幕”中遮蔽去各人所处的优越的地位、财富、环境等特殊的知识信息,人在制定社会制度建构的“正义原则”时,一定会假如自己就是那个最没本事、最没钱,处于最差生态环境的弱势的人去达成如下的共识:既要遵循罗尔斯所说的“平等的自由原则”,“弱势阶层利益最大化”的差别原则,也要有生态原则和生态代价主体间平等分配原则。
其次,以遵循生态法则为前提,发展可持续的循环经济,体现了当代人与子孙万代之间的代际平等。我们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之间发生关系,是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中介的。很显然,我们当代人破坏了生态环境,我们就以破坏了的自然生态系统与后代人发生了关系,他们就要承受我们当代人破坏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对无法与我们当代人进行理性的契约谈判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公正的。
第三,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确立建构生态社会的“正义原则”。这种生态社会的正义原则,我们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概念,叫做“公道原则”,体现了我们基于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对正义原则建构的理解。“公道”不同于“正义”,它不是经济理性人的社会契约,而是生态人的良知觉悟和认同。中国传统讲“公道自在人心”,运行于生态系统的“生生不息”自组织之“道”,既是超越自在的,也是内在于万物包括人心的,是人的类本质,也是生态系统的本然状态自组织法则。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互相内在包含,一体共在。只有觉悟了“生生”之德的生态人的良知才会体认它,而现代经济人的工具理性对此是难以达成共识的。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总理中共中央举办的省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新华网北京2月21日电
[2][美]大卫·格里芬著,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英文版序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18-19.
[3]《中国生态报道:可持续发展与文明转型》《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1月20日第二版
[4][美]Raymond Williams.文化与社会:1780-1950.pXVI,引自[美]韦森.文化与制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9.
[5][美]马文·哈里斯著,顾建光、高云霞译.文化 人 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136.
[6]Mealeau-Ponty,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and Other Essays,ed. By J.M.Edie,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p.13.
[7][美]戴维·伊斯顿,王浦劬译.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5-37.
[8][德]哈贝马斯著,洪沛郁译.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和理性与社会合理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107-140.
[9][美]丹尼尔·A·科尔曼著,梅俊杰译.生态政治.上海:上海译文能出版社,2002,126.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