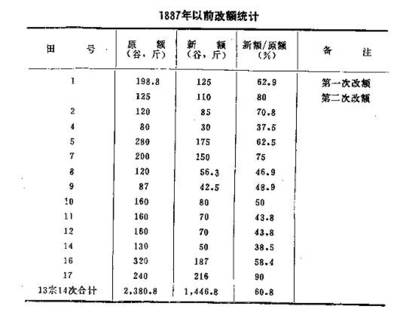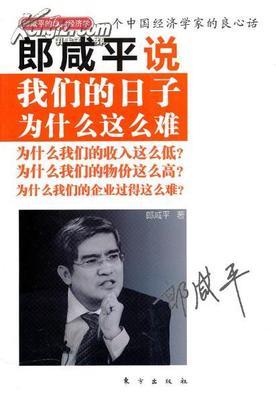系列专题:大学生就业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率持续走低,就业压力不断增大。
有趣的是,在大学生就业困难的时候,2004年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了持续的招工难,媒体称为民工荒。民工荒的存在使得大学生就业难不仅耐人寻味,也更需要解释。
在我们看来,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乃是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问题的实质是经济社会大量需要的是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熟悉某项操作与技能的实务型人才,但现实的教育制度却不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人力资本供给。这是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而且是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情况下的民工荒——同时存在唯一合理的解释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不能供给社会需求的人力资本呢?以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答案在于我们的大学的产权性质。我们的大学主体上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高等教育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和困难。
首先,公立大学名义所有权与实际所有权不一致,这使得主要以拥有剩余控制权的形式而拥有实际所有权的大学管理者的行为的成本收益发生外溢,从而像过度扩招这样的事情就很难避免,最终影响了大学的培养质量。
企业和组织资产的所有权主要体现在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上。我们当然可以讲公立大学属于全体人民,或者某个地区的全体人民,或者这个大学的全体教职工,但是由于交易费用的缘故,不可能让全体人民或者全体教职工一起分享并共同行使这两种权利,做出所有的决策。因此公立大学的名义所有者并不能够真正行使所有者的职能,也就不是真正的所有者,至少不是完全的所有者。但是上述权利决不可能没有事实上的所有者,因为果真那样的话,租值就会消散殆尽,人类社会根本就无法生存,这是租值消散定理的含义。资产的上述权利一定在人群中进行了某种配置,这种配置一般是不对称的:一方面,不同的人拥有的这两种权利组合的比重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这两种权利在不同人身上的比重也是不同的。就公立大学来说,学校领导和管理人员、教育部门的主管官员拥有的事实上的所有权要多一些,一般教职工拥有的事实上的所有权就少得多,普通老百姓呢,不是一点都没有,但几近于无,可以认为是零。
如果资产的名义所有权与实际所有权是一致的,那么该所有者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就是对称的,一般不会有成本收益外溢发生,就不会有投资过渡和/或投资不足的问题发生,而且这个所有者一定会关注大学的长期利益,因为即使他的任期或者生命是有限的,他可以将大学未来的良好声誉贴现为现期收益。但是,如果资产的名义所有权与实际所有权不一致,那么作为主要以拥有剩余控制权的形式而拥有实际所有权的大学管理者的行为就存在成本收益外溢的情况,就容易出现投资过度和/或投资不足的问题,而且也不容易关心大学的长期利益,因为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将大学未来的良好声誉贴现为现期收益。
公立大学名义所有权与实际所有权不一致的情况要严重得多,所以,我们在中国观察到各大学都大规模地建设高楼大厦和新校园,硬件一流,但在师资等方面的投资又明显不足,软件二流。前者,成本由全体名义所有者分担,但收益更多地由以拥有剩余控制权的形式而拥有实际所有权的大学管理者分享,因而不容易不过度;后者,虽然可以有效增加大学的竞争力,但是获得的收益将由全体名义所有者分享,未必能够最大化以拥有剩余控制权的形式而拥有实际所有权的大学管理者的个人利益,因而很容易不足。我们观察到的各大学的扩招冲动也是因为名义所有权与实际所有权不一致而起。而且,在大规模新校园建设后的还贷压力之下,各大学的扩招冲动必然要进一步地放大。
其次,公立大学内含高交易费用,从而限制了学术评价准则的选择。公立大学被迫选择易观察、好量化的指标,也就是用文章、课题的数量和级别来做学术评价准则,使得大家都去搞理论,不愿搞实务,造成实务型人才不足,理论型人才过剩。在这种高交易费用的约束下,大学的大规模兼并升级则进一步恶化了这种人力资本供给结构。
这里讲的高交易费用是指公立学校内部为达成一致意见而产生的高额谈判费用。一个人花自己的钱,别人一般是不能有异议的。但是对于公立大学来说,管理者花的可不是自己的钱,这就不容易达成一致意见。我们观察到的政府、国有企业、公立大学中的论资排辈就是一种节约公立组织高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同样是因为要节约高交易费用的缘故,公立大学不得不更多地采用好量化、易观察的指标来进行学术评价,而且更多地采取事后评价的办法,比如从事后发表了多少篇文章,获得了多少个课题,刊物的排名,立项单位的级别等等来进行科研评价。所以在芝加哥大学,戴维德可以凭口述传统获得教授职位;在牛津大学,莫里斯可以在无名之时获得教授职位;在麻省理工大学,丁肇中年纪轻轻可以获得远远超过其预期的学术待遇,但在公立大学这样的事情就很难发生。在我们的大学,给院士、功成名就的大学者很高的待遇可以,但要给一个成长过程中的年轻人很高的待遇就会引出非议。
公立大学内在的高交易费用限制了学术准则的选择。评价准则不同,人的行为跟着就会发生变化。公立大学不得不更多地采用文章、课题的数量和级别来进行学术评价。因为搞理论发表文章相对容易,搞实务发表文章就困难多了,于是大家都去搞理论,不愿搞实务。而且,因为这种评价准则重形式胜于重内容,实际上大家很难静下心来去真正地做好理论研究。又由于我们的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大学,其结果,不仅大学之间学科结构趋同,而且培养的大都是些缺乏实际操作与技能的理论型人才。对于私立大学来说,这种交易费用就要低些。可以推断,同样是在中国,私立大学的应用型专业、实务性课程一定要多得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一定要好得多。

本来,如果是小学校,那么大家都搞实务,办应用型专业,也是可能的。然而一旦这样的办应用型专业的学校与办理论型专业的学校相合并,在高交易费用的约束下,大家不得不采用共同的易观察、好量化的指标,也就是用文章、课题的数量和级别来做学术评价准则。这势必促使过去搞实务的人转而去搞理论。这样,大学的大规模兼并升级就使得学科结构趋同,减少了大学生人力资本的差异化程度,使得本来就不足的实务型人才更加短缺,本来就偏多的理论型人才更加的过剩,从而加大了人力资本供求结构之间的矛盾。
再次,大学和学术刊物的公立性质使得“重形式轻内容、通过形式来度量内容”的学术评价准则严重噪音化,从而使得本来就过剩的理论型人才的质量也没有了保障。
由于科学研究不是流水线上的标准化作业,很难直接度量,只能采取间接度量的方式,或者说只有间接度量才是经济的度量方式,就是通过科研成果的数量和发表刊物的级别和排名来间接地度量科研成果。这在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东方世界、西方世界都是无可避免的选择。问题是,中国的学术刊物都是由公立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所主办,因此这些学术杂志也会面临成本收益不对称的情况,难免不发“人情稿”,而发“人情稿”的老师又基本上属于公立大学,他人的揭发行为同样面临成本收益不对称的情况,因此一般不会有人来揭发。其结果,“好杂志”上发的并不都是好文章,一些重要专业杂志常常充满了烂文章,通过刊物的级别和排名来判断学术文章质量的机制被严重噪音化了。
而且,这种噪音化还具有自我加强的特征。一旦那些通过制造噪音而成“名”成“家”的人成为了“学术权威”、规则制定者,他们反过来就会把这些噪音化了的杂志规定为奖励刊物。而一旦噪音化达到相当的程度,形势甚至难以逆转。如果百分之五十一的人靠右行驶,那么我的最优选择也是靠右行驶;如果百分之五十一的人是通过制造噪音而获得职称的,那么选择制造噪音而获得职称就会成为每一个人的最优选择。于是“劣币驱逐良币”就要发生,办学质量就很难保证。本来就过剩、质量还没有保障的理论型大学生其就业前景自然就不能让人想象了。我们观察一个学校学术刊物认定方面噪音化的程度,就知道这个学校学术噪音化的程度,进而也就可以推断这个学校教学和科研的真实水准了。那些把非学术刊物列为学术奖励刊物的大学一定地是些二流的大学。我们观察一个学校是否强制学生听课,也知道这个学校学术噪音化的程度,也能推断这个学校教学和科研的真实水准——学生不学,一般来说是老师出了问题,真正一流的大学是不会强制学生听课的。
最后,给定大学的公立性质,行政干预就不能避免。但是行政干预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确保大学的办学质量,还会带来新的问题,甚至还影响了大学的办学质量。
因为公立大学花的是别人的钱,就不能不对其进行干预。花别人的钱是不能没有婆婆的。谁来当这个婆婆呢?一般是政府主管部门。如果大学的资金和人事任免主要由教育主管部门说了算,那么各大学就不能不主要对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任。问题是:第一,信息是不对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府实际上很难对大学实施有效干预。今天大学里“填表工程”和“迎检工程”之盛行,就是对政府干预能力的充分否定。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官员同样是花别人钱的人,其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同样是不对称的,我们根本不能指望他们的干预一定会促成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工商领域,经验已经证明政府官员常常被企业“俘获”,多数的管制常常走向了政府所宣称的目标的反面;在教育领域,我们同样不能保证政府官员就不会被大学“俘获”,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干预就一定能够达到其所宣称的目标。第三,正是由于政府官员同样是花别人钱的人,同样不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政府也不得不采用易观察、好量化的指标来进行评价,这会对大学的工作造成新的扭曲,那些不易观察、不好两量化的方面大学显然要轻视了。
某种意义上,大学生就业难反映的其实是超前改革的经济体制与滞后改革的教育体制之间的内在矛盾,因此大学生就业难或多或少就是渐进改革方式下难以避免要出现的一种阵痛了。可以预期,在大学生就业难的背景下,民办高等教育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甚至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步子也可能加快。还可以预期,随着大学投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由利益相关者组成委员会来治理大学最终将会成为现实,高等教育最终将形成面向市场而不是面向教育主管部门的办学机制。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