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总势头良好,但是存在许多隐患。其中之一就是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可能使中国经济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滞胀”状态。“滞胀”是指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时候却出现物价上涨,这与2005年高增长、低通胀的状态恰好相反,因此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情况。在“滞胀”的境况下,如果采用凯恩斯的药方,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加剧通货膨胀;而运用治疗通货膨胀的药方如货币主义措施减少货币供应,却会加剧停滞。这是一个两难处境。如何治理滞胀,对于宏观监管部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一、国民经济存在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的风险 中国经济已现“产能过剩”。目前官方公布的11个主要行业(钢铁、电解铝、汽车、铁合金、焦炭、煤炭、电石、铜冶炼、水泥、电力、纺织)已经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此外,房地产这个重要的行业也出现了“过剩”。截止2006年5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已高达1215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7.8%,且空置一年以上的商品房面积7979万平方米,占总空置量的65.6%。空置面积增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供大于求。当然,有时候,单纯使用供求指标衡量经济周期显得不够,需要印证指标,即失业率。如果经济景气上升,则失业率走低;相反,经济景气步入衰退,失业率走高。如果把下岗职工、国有企业中的隐性失业人口,还有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统计到失业率中,我国失业率就要高达20%以上。 当前中国实际通货膨胀率已逾“警戒线”。从最近几个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看,通货膨胀比较温和。按照发达国家的习惯,不超过3%的物价上涨属于温性通胀,对于经济运行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我国统计部门公布的CPI衡量通货膨胀,无法完全反映真实物价走势与百姓的感受偏离,因为CPI构成存在偏差。我国CPI八大类的权重比例:食品价格占33.2%,烟酒占3.9%,服装占9.1%,医疗占10%,家庭设备6%,娱乐教育占14.2%,交通通信占10.4%,居住占13.2%。这些权重尽管略有调整,但与二十年前相比变化不大,难以反映民众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一直被关注的商品房价格仍然未被列入CPI目录。如果房租权重改为房价,并按30%而不是目前的13%重新估算CPI,实际数据应该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至少高出1至2个百分点。此外,持续上涨的油价将推动物价上涨,带动CPI上涨1至2个百分点。再考虑医疗、教育等情况,中国目前真实CPI当在5%以上。 当前的产能过剩,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带来的,而通货膨胀主要由垄断行业“造价”、地方政府以及成本推进的混和的结果。 我国投资体制自2005年改革之后,投资主体趋向多元化、投资决策日益市场化,但依然没有改变政府主导的特征。许多地方的“十一五”规划都是在高增长预期下制订的,因而这类规划也是一个高投资规划。至于全国范围内的投资规模或增速是不是过度或过快,特别是许多制造业产品是不是会出现严重过剩,地方政府很少会考虑这些问题。因此,“有投资就有增长”这一发展观至今仍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 政府的高投资,也确实带来了经济的高增长。但是,这种过快的增长并不能很好地被消化。从理论上讲,投资过度具有两重性,短期内可增加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帮助消化剩余产品,从而拉动经济增长,中长期则会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在前期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埋下导致下一阶段经济回调或是衰退的种子。此外,从2005年以来的情况看,宏观经济在逐步呈现周期性调整的趋势,但地方政府采取了“逆市场”的各种政策,这些反市场周期的政策行为导致了近期又出现了投资过热问题。结果是市场调整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低效率投资和低效率供给无法淘汰,也加剧了在总量上“供大于求”的矛盾以及由此累积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即“严重的产能过剩”。 从一般情况看,产能过剩的同时,应当伴随通货紧缩。但是,体制性的因素导致物价高涨,通货不但不紧缩,反而膨胀。这里以房地产业为例进行分析。我们说当前房地产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标志性的数据就是“空置率”高于20%,远远高于经验上的警戒线。但是,房地产价格依然上升。为什么?原因在于:第一,房地产行业属于垄断行业,竞争程度还不够,为了维持暴利,一些开发商利用种种手段(如房地产商雇“托儿”制造假繁荣等)抬高价格。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即地方政府不希望房地产降价,因为降价会影响到地方经济的增长,进而影响到有关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尽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措施,但效果仍不理想,住宅投资过热及房价过高问题仍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由于地方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房地产业,由此导致房地产调控政策在地方执行力度不够。 二、当前的宏观调控效果仍待观望 当前国家针对产能过剩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为:两道“闸门”(土地、银根)。从当前经济运行以及笔者所了解的情况看,管住“银根”对投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而新开工项目清理和土地调控成为当前宏观调控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但是,土地和项目调控基本上是以行政调控为主,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调控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和随机性。在经济体制没有较大转变的情况下,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地方政府过强的投资冲动。例如,2004年采取行政性手段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产能扩张实行限制政策,鼓励能源交通建设,于是各地大上电力项目,导致电力过剩。 近期国家有关部门通过开展项目清查,虽然新开工项目增加过多的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施工项目和新开工项目均大幅减少,但据了解,一方面,今年新开工项目增加过多与个别省份前期新开工项目统计数据有水份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此次项目清理主要是亿元以上的大项目,亿元以下的项目不在检查清理之列,因此,不排除个别地方不报或少报新上项目。这一点从8月份投资和工业速增大幅回落与电力和进口加速增长相背离的情况似乎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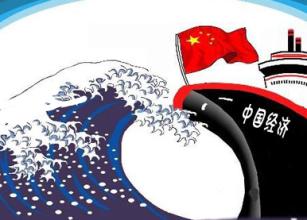
土地调控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目前地方建设用地扩张有所收敛,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均反映用地十分紧张,这有效制约了地方投资的扩张,可见土地调控比起其他手段更为有效。然而,土地也是近年来地方政府扩大投资、“以地生财”的主要动力源,因此,土地政策能否真正落实还有待时间的检验。我们不妨从最近几年的实践检验土地政策的效果。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央试图以整顿开发区为突破口,抑制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势头,减少“土地财政”带来的危害。2003年8月8日,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国土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察部、建设部、审计署组成的10个联合督查组开赴到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对土地市场秩序治理整顿工作进行联合督查,全面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这次清理整顿,虽然将全国6866个各类开发区减掉了70%,规划面积也压缩了近70%,但这次整顿非但没有遏止住乱占滥用土地的源头,反而产生新的违法违规用地。根据国土资源部执法局对2004年10月至2005年5月部分城市分片执法检查情况统计,违法用地占新增建设用地宗地、面积的比例分别达到61%和5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80%。鉴于此种情况,2004年出台了“垂直管理”措施,试图让省以下的国土资源官员摆脱地方政府牵制,以便更独立地监管土地使用。不过,实施“垂直管理”,有一个潜在的立论基础:上级政府比下级政府更英明更清廉,这一立论是有问题的。县、市级政府违法审批,省级政府未必就不会。不少国土部门管理松弛,有的甚至执法犯法,给不法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事实上,连续数年,四至九个部委联合督察,都难以从根本上遏制土地违法问题,现在却试图让一个部委的几个督察局担此大任,其效果如何,不难预料。 三、中国经济走出“滞胀”的路径选择 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通货膨胀,都与地方政府有很大关系,而地方政府之所以要主导投资、维持高度的GDP增长,与政府定位、财政体制及政绩考核体系有关。从当前的情况看,地方政府的行政开支与经济增长开支比较大。第一,吃财政饭的人太多,需要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第二,由于负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因此在基本公共品的财政支出方面比重偏低,而经济建设的开支较大。与此同时,财政体制迫使地方政府搞卖地财政。分税制将“财权上移”的同时,却将“事权下移”。这样一来,地方政府要做的事越来越多,但手中可支配的财力相对越来越少。加上不尽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地方政府的官员要想升迁,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土地财政”。因为,1994年分税制体制开了一个“口子”——土地出让金归地方政府。于是,地方政府通过征地,以每亩几万元的低价,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拿走,转手通过拍卖等方式出让,地价上升几十、几百倍以上。这种内在冲动,直接导致了“滞胀”。 因此,要从根本上治理“滞胀”,应该给政府松绑,淡化速度,突出发展。不能只用常规手段,需要跳出圈子,从根本上入手。 第一,顺应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思路,重新给政府定位,让政府部门退出经济建设第一线,转向公共服务职能。只有这样,才能让地方政府从根本上走出惟GDP马首是瞻的发展观,避免盲目竞争国内外投资、上项目,也缓解抬高产品价格的内在需求。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但是我国的基本公共品的财政支出比重偏低。2000年政府用于基本公共品的支出只占财政支出的43%,发达国家一般在70%。相反,中国政府公共支出越位很严重,譬如,经济建设费仍然占财政支出30%(预算外和没有列入预算的,可能高于这个数据)。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开支都非常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定位存在问题,导致机构臃肿、官员太多。市场经济要求“小政府、大市场”。政府应当退出经济建设实践,不直接搞经营性或者商业性的投资,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如公共道路、国防等等),宏观调控(即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维持全国统一大市场及经济运行的秩序)。做好政府定位之后,国家应当出台《国家行政和事业人员供养法》,属于百姓供养的各类机构和人员,需要定岗定员、规定标准、建立指标体系、严格经费拨款、制定审核监督办法和增加供养人员的程序,将供养机构和吃皇粮人数膨胀用法律的形式死死控制住。 第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以从三方面入手:鼓励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这不只是研究部门、教育部门要做的事情,实际上更需要企业去做,点点滴滴的技术创新积累起来,才会有技术的重大突破;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对于提供市场的基础设施、对于降低交易成本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大力发展;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降低工业化的成本。应让信息产业能够渗透到各个部门,改造这些部门,降低它们的生产成本,特别是交易成本。 (本文刊发于《学习月刊》2006年12月)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