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项副产品
老子所锤炼的道德,从出炉之日起,就有一些副产品。其中有三项副产品,我们认为,是不能不说的。副产品一:“圣人无常心”;副产品二:“无为而无不为”;副产品三:“小国寡民”。我们认为,其中的第一项副产品是至高至善的;第二项副产品是善恶并存的;第三项副产品则是消极或者说是“恶”的。
副产品一:“圣人无常心”。
“无常心”绝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要求人们不但不能固执一己之见,而且还要有一颗厚实博大的包容心,要有一个海纳百川的大胸襟。“无常心”这样的境界,恐怕只有把自己的心“修炼”到空灵、静虚、清灵境界的人才能达致。在老子看来,世俗中人,往往装满了自己的想法,固执拘泥,自以为是,刚愎自用,这样的心犹如一块顽石,不仅不可能突破自身,超越自我,往往还带着一孔之见、一己偏执,昂首阔步走向坟茔,步入“死地”。所以圣人应该“无常心”,解放自己的心灵,使自己达致意志的自由。(“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见《道德经·四十九章》)。所以老子在第十六章中说要“致虚极,守静笃。”这个“虚极”的境界就是一种“无”的境界,也就是“无常心”的境界。显然,“无常心”正是从“无”中体悟而来的。老子在第十六章中紧接着说:万物林林总总,纷纷纭纭,运作不息,纷乱异常,而我却要去反观、追溯它的源头,去寻找它们从何处来的根本,到何处去的规律,这就叫“知常”。“常”就是亘古不变的常规、常道。把握了事物运作的规律,溯及万物的根与源,就能懂得如何回复到静虚清纯的生命本真。能掌握万事万物的规律,能回归到生命本真,就能世事洞明,为人处事就不会妄动、妄作。能洞明世事,能把握道,就会懂得包容,就会有一颗公正透明的心,这才是健全的人格。拥有健全人格的人就是懂得天道的人。天道是亘古不变的,懂得天道,即使陷入绝境也不会有凶险。(“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这既是“无”的作用,也是“无”的高尚力量。圣吉在其书中引述欧白恩的一段话说:“真正成熟的人能建立和坚持更高的价值观,愿意为比自我更大的目标而努力,有开阔的胸襟,有主见与自由意志,并且不断努力追求事情的真相。”[1]因此,“无常心”是一种必需的修炼。如果我们模仿老子的话说,那就是,以其“无”心,是以处处是心,处处有心,处处用心。“无常心”是一颗开放的心,一颗自由的心,一颗坦然的心,一颗清纯如婴的心。
这样一颗“心”也正是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所提倡“修炼”并希望达致的境界。在我们看来,圣吉所倡导的“五项修炼”,除了“系统思考”这一项“修炼”外,——对于以“分解主义”为主流文化的西方人来说,学习系统思考确实是一种修炼;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拥有“系统思考”传统的文化中,这其实算不得是“修炼”。只不过,由于长期受西方主流文化的冲击,好些中国人已经数典忘祖了,当然得重新补补课。圣吉说的其余四项修炼:包括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体学习,其实都需要修“心”,在我们看来,则就是要修炼一颗“无常心”,一颗空灵、静虚、清纯的心,达致那种“无”的境界。对每个人来说,只有把自己这颗被世俗蒙蔽得几乎已经是尘封了的心重新打开,把心里装着的那一杯水倒空,把自己这颗有这样那样想法的心推向极点——“无”的境界,然后才能真正实现自我超越,才能不被自己长期以来积成的心智模式所束缚和困扰,真正实现神的空灵,心的自由,修炼成一颗“无常心”;对于团体来说,如果每个人的心都修炼到空灵、静虚、清纯的境界,每个人的心就成为了一张白纸,那么在这张白纸上将可以绘上最美最靓丽的愿景,增进团体学习也就显得举重若轻。
有人或许会说,这虽然在学理上看起来是可行的,但是在实践中,谁又能够达致“无常心”这样高的境界呢?同时,如果真的达到了“无常心”的境界,作为一个组织会不会因为有太多“心灵自由”的人,而使整个组织步入软弱涣散状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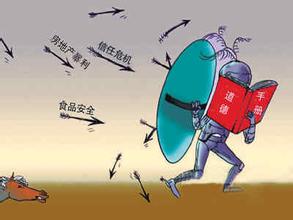
首先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通读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我们发现,组织中每一个把自己这颗心反推到极点——“无”的境界,修炼成一颗“无常心”,对于组织中的个体实现“自我超越”和改善“心智模式”肯定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圣吉在“自我超越”这一项修炼中,试图通过“真相”和“愿景”之间的“创造性张力”,来帮助人们实现这种超越。在我们看来,如果能够把一颗被各种世俗生活侵袭得千疮百孔的心,修炼到到象一张“白纸”那样的“无”的纯净空灵的境界,那么,“无”就成为了一面镜子,不仅所有事情的“真相”会原形毕露,而且,圣吉所说的那些原来业已拥有的思考方式、心智模式、隐藏在背后的假设甚至是潜意识层丝丝心灵的律动,都将会在一颗空灵、虚静、清纯得如一汪静湖的心海里飘浮而出。同时,“无”的境界与愿景之间所产生的创造性张力,将远比“真相”与“愿景”之间产生的创造性张力,要强大得多。因为,“无”的境界不仅更能够透视“真相”,而且肯定比“真相”离“愿景”的距离更远,创造性张力更强。因为,我们说过,“无”本身就是一个激发创造性张力的强大源泉,也是锤炼健全而崇高人格的源头活水。当一个人修炼到虚静空灵的“无”的境界时,那么,即使是一丝微细的恶念都会在虚静的心湖中泛起涟漪,使人产生罪恶感。所以,内心愈是虚静,愈是“无”,愈能唤醒人们沉睡的良知,愈能唤起人们良善的美德。圣吉自己也说:“愈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良知和价值观,愈容易与潜意识深深契合,或甚至有时就是潜意识的一部分。”[2]如此看来,人的潜意识层似乎都应该有良知和美德,那些恶习、恶念等是被世俗社会传染和玷污所造成的。而“无”的境界似乎比“潜意识层”更深了一层,可谓之“空灵层”。在这一“无”的空灵层,即使是潜意识层如果有丝丝恶念,恐怕亦难逃“无”的法眼,被曝光和裸露无遗。
总之,人性本来是一张白纸,修炼到“无”的境界,将能返回到这一张白纸的纯净状态,这才真正叫做“返朴归真”;同时,“无”的境界更能透视事件的“真相”,离“愿景”的距离也更远,因此,必然会产生更为强大的“创造性张力”。可图示如下:
创造性张力
“无常心”(无)真相愿景
创造性张力
只要把世俗的心复归到“无”的虚静空灵境界,“无常心”的境界就能达致。“无常心”是“以百姓之心为心”,因而是对“常心”、俗心的一种全面超越。无常心达到了心灵和意志的真正自由,这样的心不仅是幸福的,而且也是更为强大的创造力的源泉,是人类所应追求的美好愿景,因而也是文化修炼的最高境界。这就是我们对于前面第一个问题,即关于如何修炼“无常心”的回答。
现在我们来回答第二个问题。组织中的每一个个体如果真的都达到了“无常心”的境界,作为一个组织会不会因为有太多“心灵自由”的人,而使整个组织步入软弱涣散状态呢?我们也结合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的相关内容来回答这个问题。
圣吉《第五项修炼》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如美国汉诺瓦保险公司总经理欧白恩所说的“更适合人性的组织模式”[3]。他并引用了赫门米勒公司总裁赛蒙的话,表达了他的新型组织理想:“为什么工作不能够是我们生命中美好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把工作看作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而未能珍惜和赞美它?为什么工作不能够是人们终其一生发展道德与价值观、表现人文关怀与艺术的基石?为什么人们不能从工作中去体会事物设计的美、感受过程的美,并试着欣赏可持之恒久的价值之美?我们相信这些都是工作本身就具有的。”[4]也即要让工作本身成为赞美的对象,工作成果成为审美的对象,工作过程成为发展德性修养的场域。想象一下,这样一种组织是多么地合乎人性,在这样一种组织中工作又是一件多么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事!那么这样一种新型的“更适合人性的组织模式”是否仅仅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到底能否真正建立呢?
我们首先必须看到,相对于这种新型的组织,现代组织结构的机械性、非人性化是很值得反思的。有人说,西方现行的官僚制,是“由天才设计而由白痴管理”的一种体制。奥斯本与普拉斯特里克在他们所著的《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一书中评述道:“这听起来或许有些残酷,但其中却蕴含着真正的要义。在官僚机器的深处潜藏着一个‘控制’的怪胎。雇员只是高度规制化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工作被分解成不同职能并加以详细描述。管理者重在思考问题,而工人则依吩咐完成指派的任务。雇员行为由详细的规则和程序加以约制。监督者检查和监督员工的执行情况。”[5]在这种“‘控制’的怪胎”作祟下,对业主与管理者而言,雇员只是赚取利润的“一个齿轮”、一枚螺丝钉、一个工具;对于组织中的雇员而言,工作是为了赚取收入,工作中所赚取的收入是为了用来支持他们去做“工作外真正想做的事情”。也即是说,对绝大部分雇员而言,日常的工作并不是他们真正想做的工作。——这正是现代组织中绝大部分人的工作心态。这样的工作心态,是典型的消费者导向的工作观:工作是产生收入的工具;[6]这样的工作观,无论对于业主还是雇员来说,工作都只是赚取利润或收入的“工具”,当然就绝没有幸福与快乐可言。
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所倡导的“更适合人性的组织模式”,就是希望改变这种工具性工作观,所直接针对的,正是现代组织结构的机械性、非人性化,要求人们必须从“工具性的工作观转为较注重精神层面的工作观”,[7]进而企图建立一个使人达致精神愉悦、令人感到幸福快乐的组织。这种“转变”和“企图”是既富有开创性又具有现实意义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之:
一是在圣吉看来,只有注重精神层面的工作观,才能更充分地发挥人类的潜能。圣吉指出:“不管什么理由,我们对于追求精神层面所作的努力,远比不上对物质发展的追求。这是人类的大不幸,因为只有在精神层面得以发展的前提下,我们的潜能才能充分地发挥。”[8]因此,圣吉赞赏日本京都陶瓷公司创办人兼社长稻森胜夫的意见,即“提供员工物质的富足和精神的福祉同样重要”[9]。西方现行的官僚制组织结构,是在物质与精神二元分裂主义指导下建构的,所以往往只关注物质层面的富足而忽略精神层面,这是必然的。也因此,使组织中充满工具性工作观,身处组织中的人的精神长期缺乏关爱,人们的精神愉悦当然难以达致。以“一内涵二”思维观照物质与精神,它们是可以实现有机互动、可以相得益彰的。也正因为此,可以得出第二个结论,即更注重精神层面,可以彰显管理绩效。注重精神层面,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雇员的高层次需求。关于这一点,美国汉诺瓦保险公司总经理欧白恩是很有见地的,他指出:“工业时代之初,人们一星期工作六天,才能赚得足够的金钱,以取得食物与栖身之所。今天,我们大多数在星期二下午就达成同样的目标。传统阶层式的组织设计,并没有提供员工自尊与自我实现这类较高层次的需求。而现代组织必须开始关照所有员工这些需要,否则管理效果不彰的现象仍会继续下去。”[10]基于前述两点,又可以进一步得出第三个结论,即生活的美德与经济上的成功其实具有相当可能的兼容性。针对这一点,欧白恩通过自己的管理实践认为:“在我们寻求建立的组织类型中,人的自我发展与财务的成功是同等重要的。这与我们最基本的前提并不悖:生活的美德与事业的成功不仅可以相容,而且相得益彰。这与传统的商场信条相去甚远。”[11]也即是说,一个更适合人性的组织模式,必将能使“高尚的美德与经济上的成功”[12]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必能兼得鱼和熊掌之利。基于以上三点分析,可以这样认为,即一个更适合人性的组织模式,就是一个既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又能培育组织成员生活美德、提供人们精神愉悦的,令人感到幸福快乐的组织。
“更适合人性的组织模式”,也是一个真正实现了有机互动的组织。也即在这种组织中,将能真正实现老板与雇员、组织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有机互动。因为,这种组织是建立在物质与精神可以实现有机互动、可以相得益彰,即“高尚的美德与经济上的成功”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能兼得鱼和熊掌之利这样一种全新的理念之上的。因此,对于组织管理者而言,他们相信也必须相信,“每个人都是有智慧而完整的实体,都愿意为崇高的使命发挥精神力量”。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在这一点上存有疑虑,就必然会返归到韦伯“官僚制”和工具性工作观的老路,就不可能建立一个“更适合人性的组织模式”。业主与管理者不仅仅是为了赚取利润或者是利润最大化,他们的的基本工作应该是:“提供员工追求充实生活的工作环境”,使每个组织成员都有“创造性张力”的内驱力和“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冲动和行动。这是从工具性工作观转为注重精神面工作观的关键,而这实际上是要求一个组织在文化上要有全面的革新。新型的组织模式必然要求有新型的组织文化来支撑。这种新型组织文化的落脚点,是必须让员工有追求“充实生活”的内驱力,并为了工作而成为敢于和善于自我超越的人,工作并不仅仅是甚至完全就不是,仅仅为了赚取收入或者是为了去做“工作外”真正想做的事。工作本身就是他们真正想做的事。并为了追求充实生活和为了在工作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实现,而有一种“义无反顾的勇气”。他们说:“我们想要如此,不因为什么,只因为我们真心想要如此”于是,他们“同意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在其中他们不是互相利用而是互相帮助,如此每一个人的潜力都能充分展现”。这一点也很重要。一个更适合人性的组织,必然是一个具有高度自我超越、自我实现和学习精神的组织。圣吉指出:“‘自我超越’是个人成长的学习修炼。具有高度自我超越的人,能不断扩展他们创造生命中真正心之所向的能力,从个人追求不断学习为起点,形成学习型组织的精神。”因此,一个真正适合人性的组织,必然是一个真正实现了有机互动的组织,是一个真正的学习型组织,是一个更富创造力、更具崇高美德、更关心精神愉悦,更追求精神充实和生活美德又能取得辉煌经济成就的组织。[13]
“更合人性的组织模式”还将是一个真正“和而不同”组织。圣吉指出,要建立一个“更适合人性的组织模式”,就必须打破传统组织与雇员的“契约关系”,建立如赫门米勒前总裁帝普雷所倡导的组织与个人之间的“盟约关系”。这种“盟约关系”建立在对“价值、目标、重大议题,以及管理过程的共同的誓愿上面。盟约关系应是和谐、优美与均衡的。”而要建立“和谐、优美与均衡”的“盟约关系”,组织中通过“深度汇谈”展开“团体学习”是必不可少的。透过深度汇谈,人们可以“互相帮助,觉察彼此思维中不一致的地方”,可以发展出“一种超乎平常思维的敏感度”,这个敏感度“象是一个网目很细的网,能够搜集思维之流中不易察觉的意义”,它存在于“真正智力的根部”,因而也更能使参与者察觉彼此间的“不一致”。这种所谓的“真正智力的根部”实际上正是一种“无”的空灵虚静境界。愈是深入到这种“无”的空灵虚静的境界,就愈会富有宽容、博大、开放的胸襟,进而使人们不仅愈能察觉彼此间思维上的“不一致”,即对这种“不一致”愈富有敏感度,同时也愈能包容彼此间的“不一致”,在这种“不一致”上实现前所未有“和谐、优美与均衡”。因此可以说,愈是能达致“无”的空灵虚静的境界,汇谈便愈是能更深入,愈是能深入到“真正智力的根部”,进而也愈是能增进组织学习,愈是能产生组织内部“和合”的境象,进而真正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组织团队。欧白恩说:“我们不介意会议的结果是否会造成看法出现很大的分歧。重要的是,大家把自己的看法摊出来,即使你不赞同这些看法,它们还是有助于多方面考量,这个方式比起被强求达成协议,更能够使人们同心协力。因为他们都有主张自己看法的机会。只要学习的过程是开放的,而且人人都感觉被尊重,虽然最后是别人的看法获得采行,却能泰然处之。”欧白恩的这一段话,其实就是对“和而不同”的最好解释。由此可见,组织成员愈是能修炼到“无常心”的境界,将愈是达致组织内部的“和而不同”,也更能增进组织内部的“和合”,而绝不会导致软弱涣散。[14]
归结前述三点,更适合人性的组织,是一个追求崇高精神愉悦的快乐的组织,是一个有机互动的组织,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组织。而要建立这样一种组织,组织中的全体成员,都需要修炼一颗“无常心”。通过前文对于老子“无常心”的解读,我们自然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修炼“无常心”将能使组织及其成员更自觉地去追求精神的愉悦和生活的美德,也是建立一个真正有机互动组织的前提,是实现组织内部真正“和而不同”进而也更加“和合”的基础。
副产品二:秉持“无为无不为”
老子在《道德经》的第二、十、二十九、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三、四十八、五十七、六十三、六十四等十个章节中,共有13次论述到“无为”的主张及其妙用。依据老子逻辑,之所以要“无为”,是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三十七章》),大自然生养万物,遵循着看上去的确是“无为”的自然规律,而却结出了“无不为”硕果,所以效法自然之道,对治人事也应该“无为”,进而实现“无不为”的理想境界。用有机社会理论观照老子的思想,那就是任一个有机系统都是一个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调控的“自组织自系统”,所以对待任一个有机系统,无论是有机自然系统,抑或是有机社会系统,都不应该予以人为的外力干预。这是因为,一个有机系统能够实现“自治”,即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调控,一方面是不需要这种人为的外力干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由于缺乏对有机系统运行规律的掌握,外力干预往往只能适得其反。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也谈及,他说:对于任一个有机系统,如对一个“不断增强的环路”,你愈是用力去人为推动,“调节环路的反作用就愈是强烈,使你的努力愈是徒劳无功”[15]这是很显然的。因为任一个有机系统,它们都有自身的运作规律与规则,你既对它们的运作规则不了解,就武断地加以干预,强制地予以调控,其结果当然是系统对抗就愈强烈,使你达不到预设的目标;就即使你对某系统运作规则己了如指掌了,了然于胸了,其结果也可能是,你了解得愈是深入,掌握得愈是全面,你可能愈会赞叹自然造化运作规律的完美与“无为而无不为”的神奇,进而使你变得愈加不敢对它们有丝毫人力干预的念头,使你更加变得不敢“轻举妄动”。这正是老子所说的,“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四十八章》)。也即你对“道”了解得越深,你就越会遵循“无为”的“道”理。这也才是老子“无为”思想的真谛!显然,老子所说的“无为”是指要尊重自然的规律、自然的意志、自然的精神,这是其一;其二,老子所说的“无为”更重要的是要达致“无不为”,即“无所不为”,而绝不是真的“无所作为”。自然造化是“无为”的,然而又是“无所不为”的,这才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一命题的真意。
我们不禁要问:在现实生活中,“无为”能否真地达致“无不为”的理想效果呢?对此,老子为我们提供了三个“不”和三大“宝”。三个“不”是指:不刚,即要用“柔”;“不争”;“不敢”。三大宝是指《道德经·六十七章》所说的,“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三个“不”与三大“宝”,都是老子无为思想的体现,也是无为思想的运用。在老子看来,要达致无为而无不为的境地,就必须要知道三个“不”,要拥有三大“宝”。所谓“不刚”,是指不用刚亢进,而是柔以致胜,认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道德经·四十三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道德经·七十八章》);所谓“不争”,老子解释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二十二章》);所谓“不敢”,老子说:“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道德经·三章》)至于三大宝,老子在六十七章中是这样解说的:因为人有仁慈之德,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就能有勇武之行,——现实生活中恐怕没有一个在关键时刻能做出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是没有仁爱柔慈之德的;因为俭啬,平时克勤克俭,所以在关键时候能大方,——你看那些献爱心的人,往往是在日常生活中非常俭朴的,就是一个明证;因为不敢居天下人之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先人“忧”而后人“乐”,所以天下人能推他做万物的首长。——甘做人下人,吃得苦中苦,甘居人后,方能成为人上人。正是这个道理。而现在的人,没有仁爱之德却尚勇武;不懂得克勤克俭,却追求奢华;事事争先,不愿甘居人后,则无异于自取其咎,自寻死路,自陷绝境。(“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道德经·六十七章》))从现代主义、唯理主义那种认为人类能够认识一切(指世界拥有绝对价值与最终真理,人类依靠纯粹理性就能够认识一切)、干预一切、征服一切的观点来看,老子的三个“不”与三大“宝”,确实是“消极”无为的表现,但是这样对老子进行盖棺定论,实在冤枉,因为老子所倡导的三个“不”和三大“宝”,作为“无为”的法则,实际上是为了“驰骋天下”、为了“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为了实现“无不治”的理想,一句话正是为了“无不为”。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早就超越了现代主义,而直接跨进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唯理主义的怀疑与否定。更进一步说,老子的“无为”也不失为一剂医治后现代社会缺乏信仰与行为准则的良方,因为无论这个世界是否存在绝对价值或终极真理,你拥有了老子的三个“不”与三大“宝”,用柔不用刚,以让代争,勇于“不敢”,又能富有慈爱仁德与克勤克俭、“去甚、去奢、去泰”(《道德经·二十九章》)的美德,那么,这个多元主义社会就会更加和谐稳定,身处多元主义时代的人们,也就能做到“持经达变”,更加幸福快乐,而不至于如一只无头苍蝇,四处乱闯,盲干妄作。从这个意义说,老子不仅超越了现代主义而直接进入了后现代,而且是成功跨越了后现代主义而步入了后—后现代。显然,在老子看来,现代人这些什么什么“主义”的名字,花里胡梢,简直莫名其妙。名本无名,反朴归真,常道归一,可以说,以“无为”来达致“无不为”、“无不治”的理想,将永远能闪耀着智慧的灵光!
然而,我们盛赞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却也并不是就赞同老子本人的作为。据《史记·韩非列传》:老子写了《道德经》后,就扬长而去,“不知所终”。由此可见,把“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讲得如此透彻的老子,最终还是真地“无为”而“去”。或许他有着许多无奈,有其历史因由。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或许正是由于他的“率先垂范”与带头作用,中国历史上就衍生出了“隐士”文化。中国的那些古“圣人”似乎都有“隐士癖”,不管有无得“道”,是否真正悟得了“道”,现实生活中稍不如意就沓无音讯,“归去来兮”,归隐而去。这对于社会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现。在我们看来,中国的政治文化、政治哲学不发达,与这些懂得了些“道”理的人,动不动就归隐而去是有很大关系的。政治需要强烈的参与意识,“隐士”文化是直接冲击这种参与精神的,事实上还波及到了整个社会。无怪乎陈独秀在《卑之无甚高论》中慨叹:“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16]陈西滢则说:“中国人的毛病就是他们太聪明了,……中国人最初不管邻家瓦上霜,久而久之,连自己门前的雪也不管了,如果有人同住的话。所以,军阀政客虽然是少数,小百姓虽然受尽了苦,却不肯团结起来反抗他们。”[17]他们所批判的,其实都是中国人狭隘的个人主义,缺乏公德心与政治参与意识。就普通百姓言,中国如春秋时鲁国的曹刿这样的人太少了。据《左传》所载的“曹刿论战”一事来看,曹刿当是一民间人士,但是他这种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太少见了。就中国知识分子言,则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所颂扬的人是不是也太少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之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我们这里所指的是,如范仲俺所说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即不在其位,能谋其政的人是不是太少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秉承“入则独善其身,出则兼济天下”,也就是要么无所作为,独善其身,明哲保身,要么就无所不为,最好当然是君临天下。这使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了刘再复、林岗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设计》中所论及的中国人的“主奴根性”。要么做主人,要么不得已便做了奴隶。——那些“知士仁人”们,则因为做不了主人又不愿意做奴隶,所以最好的选择当然就是做“隐士”了。显见不争的是,正是隐士文化加剧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参与意识的缺失。而正是因为政治参与意识的长期缺损,便往往任凭“主人”们胡作非为,损公肥私,贪贿卖国,而当到了局面不可收拾之时,才起来颠覆之、推翻之、革命之,于是又来了一批新“主人”,同时又造就了一批新奴隶,以及不愿意做奴隶却因为错失了好多“良机”而做不了新主人的新隐士。于是,便交替出现了鲁迅所说的两样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18]而“隐士”们似乎在这两样时代里都因其明哲保身,而均能“做稳”,所以,中国传统知识们在不如意之时,便首选做起了“隐士”。这到底是“主人”的错?还是“奴隶”的错?抑或是“隐士”们的错?依我看,得各打五十大板,一共一百五十板,这样最合适,也最为公平。那些胡作非为的“主人”们当然该打,而且该狠狠地打;那些“奴隶”们,因为“怒其不争”也该打;那些“隐士”们则因其作为“先知先觉”者,却带坏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参与意识,应该与那些“主人”们一起狠打。
有人或许会说,如果说老子最终消极避世是值得批评的,问题却是,如孔夫子那样奔波一生,希望推行“仁政”,做一个救世者,但最终还是落了个“似丧家之狗”的下场,最后不得不慨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第九》)这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做“隐士”是情有可愿的。对此,高专诚先生对孔子晚年的消极厌世思想作了如下的评述,他说:“这种悲凉的气氛,从孔子开始一直笼罩着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造成这一情势的原因,主要是在政治权势的无穷压制之下,使那些所谓的‘士’阶层无法舒展其政治抱负,有时甚至是基本生存都会受到威胁。所以在那种时代,思想的真正价值,充其量只能在思想领域内存在,无法名副其实地与社会实际挂上勾;思想家本人,特别是在其生活的后期,只能保持自己的气节,作些无可奈何的叹息。这样,他们的思想,总是在勃勃向上的努力中,掺杂着些许悲凉的表征,蒙上一层凄楚的轻纱。儒家如此,道、佛诸家更不必谈。”[19]这里,高专诚似乎是要为传统中国的“隐士”们找借口,其是非我们在这里不想多作评述。但有两点却是值得一提的:一是中国哲学从孔子,其实是从老子的“无为”思想或者是更早以前开始,就笼罩着一股“悲凉气氛”,这是可以肯定的,并因此孕育出一批一批的“隐士”也是不容否定的。这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参与意识与政治哲学的发达,显然起到了极大的障碍作用;二是不论孔子的“仁政”思想和以仁为中心的“德行伦理之学”,如成中英先生所说有多么的完善,但正如他所指出的:“我们更无须讳言儒家伦理自汉武帝以后逐渐为封建专制的帝王所利用做为独裁统治人民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不但儒学被工具化了,而且也被僵固化了,成为封闭的行尸走肉。这是孔子后两千年来儒家伦理的不幸命运。它带来中国近代史的灾难,并在五四受到强烈的鞭策,此事也尽为人知。但这不应让我们对儒学的本来面貌与原始精神盲目相待。实事求是的态度应是:相反的,我们更有理由与责任还回儒学伦理的本来面目,认清它的真相,发挥它的真精神。”[20]对儒家思想要有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道家思想,我们同样也要有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不知道孔子本人对自己的思想,到底是不是有用错了的嫌疑,——后世是肯定用错了,但从老子对待自己的“无为”思想来看,显然有用错的嫌疑。因为他的“无为”本意上是要达致“无不为”,而实际上他自己最终也还是踏上无所作为的“隐士”之路。这显然就是用错的标征,而他提出的“小国寡民”思想,则更是用错自己“无为”思想明显体现。这正是我们要说副产品三。
副产品三:崇尚“小国寡民”。
我们在这里首先不能不说的是,文化是始终是善恶并存的。任何一种文化,看你从那方面去看,从那个角度去发挥。你从善的一方面看过去,往往完美得很;若从恶的一面看过去,它往往也就糟得很。我们在本书第二部分将阐述文化也是一个有机系统。任一个有机系统运作均遵循“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规律,因此均是善恶并存的。如老子的“无为”思想,如果从“善”的一面看去,我们已经说过,对治有机系统,不作强力干预,通过“无为”来达致“无不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办法。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在谈及关于“领导者是设计师”问题时,就引用老子的话,提出领导者应该在组织中实现“无为而治”的领导功能。他说:“今天,虽然领导者的设计师角色被人忽视,然而几千年前的哲人便曾对领导者的角色给予精辟的诠释。老子说,不好的领导者,会被人们瞧不起;好的领导者,会赢得人们的称颂;伟大的领导者,是让大家在事情完成时说:‘是我们自己完成这件事情的。’”(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十七章》)[21]这大概就是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最高境界了。在彼得·圣吉看来,领导者要达致这种“无为而治”的境界,就必须进行角色的转换,也就是要从传统管理者的“控制的怪胎”中走出来,转变组织的设计师。这因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来临,领导者面对的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雇员。正如彼德·德鲁克所说:“我们正在进入基本的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的知识社会,它现在和将来的基本经济资源将是知识。”[22]而所有的这些“知识”需要交流、激活、汲取,需要自由发挥,绝不是依凭“控制”所能奏效的。这是其一;其二是因为,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来工作,往往正如前文引述的欧白恩所说的,更多的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取得食物与栖身之所,而是有了需要获得尊重与自我实现这类较高层次的需求;其三是,随着顾客社会的形成与市场的饱和程度的提高,竞争的日趋激烈和无常,我们似乎只要学着费希尔(KimballFisher)在《领导自我管理团队》一书中提问方式,提一个问题,就可以知道传统领导角色转换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顾客和产品的质量呢?还是对员工的控制?”[23]在前述三个宏观背景下,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从“控制者”、“领航员”等转变成为一个组织的设计师,就显得尤为必要。
那么,领导者应该设计什么呢?我们认为,那就是要设计一种如奥斯本与默兰在《自我管理型团队》中所说的“有意义的环境”。这就是说,组织环境至少有两种:有意义的环境与无意义的环境。这种区分是十分必要的,它会使我们对组织环境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或许正是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那种“无意义的组织环境”之中,才使我们往往把工作场所仅仅当作是获取生存资源的场域,而绝无孕育意义与价值的可能,也没这种期待与奢望。组织的机械性、非人性化显然也正由此而滋长。于是,奥斯本、默兰对管理者与领导者角色进行重新定义,并阐述了领导者角色重新定义和转换对于创造组织活力的重大意义:
管理者的角色是什么呢?它被重新定义为团队和员工的开发者、教练、资源的分配者、赛跑裁判者,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和蔼的、善良的老式管理者。
………
领导的任务是使组织的工作有意义,员工被有意义的工作所吸引和激励,有意义的工作能给每个人带来最好的东西,并激励他们不断迎接新挑战。
…………
我们所试图开发的是组织的活力。活力是指能力、知识、意愿、性格等的自由发挥,是一种从未被汲取过的激情。活力必须被认为是由值得的,甚至是高贵的东西所激发。在志愿者组织中,工作的意愿和动力能使个人和组织的绩效,达到一个空前的水平。活力流动,不是因为企业需要它,而是因为组织环境允许它。比如创造力或艺术才能,我们不能够强迫获得,但是能够创造环境来诱导它。[24]
显然,营造有意义的组织环境正是彼得·圣吉所期望出现并致力培植的“更适合人性的组织模式”。我们说过,更适合人性的组织应该是一个快乐幸福的团队、一个和而不同的团队、一个有机互动的团队。而只有营造“有意义的环境”,才能让意义与价值内化于存在与实践之中,也只有将意义与价值内化于存在与实践之中,才能营造出一个意义或价值与存在或实践有机互动的组织,一个能使人快乐的进而能感受甚至触摸到幸福的组织;这样一个组织中成员,如果能再如我们所说的修炼到“无常心”境界,那么也就会更加“和而不同”,更加感觉到幸福与快乐。所以,可以肯定,这也正是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
那么,在具体操作层面,如何实施“无为而治”的理想呢?这就是西方管理研究者提出,并实施了十余年也取得了相当绩效的,建立“自我管理型团队”来实现“无为而治”的理想目标。
从有机社会理论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团队或组织,只要有人的活动参与,就会产生互动。这种“互动”能否是“有机”的,首先靠的正是意义与价值的参与,意义与价值是润滑剂、黏合剂(——这实际上便是组织文化的参与,这也正是我们在第二部人要论及的“文化全面质量管理”的理论基点);再进一步,靠的是如何引导、激发出这些意义与价值,使一个组织或团队的环境成为“有意义的环境”。这就是奥斯本、默兰所说的“开发组织活力”工作。而只有充满活力的和有意义与价值参与的组织才能真正成为有机互动的组织,成为一个有机互动的系统。针对有机系统,彼得·圣吉认为是不能用强力去推动、去干预的。哈耶克认为,我们所能做的是,“像园丁培植其植物那样,经由提供适宜的环境去促成社会的发展,而决不能像手工艺人打造手工艺品那样刻意地塑造其产品。”[25]奥斯本、默兰则认为要设计一种有意义的工作环境而不是去一味控制组织成员。他们所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那就是对待组织或团队这样一个有机系统,必须要让员工在有意义的环境下实现“自我管理”,进而实现“无为而治”的管理学最高境界。在我们看来,这也正是建立“自我管理型团队”的理论基础。
经过奥斯本和默兰十多年的实践,自我管理型团队大致是这么一种状况:组建自我管理型团队所要所做的工作,首先是要对传统的多层级的,主要是为了达到“控制”目标的组织结构进行扁平化重组和再造;其次是组成跨职能团队并对员工实施跨职能培训,使其成为“通才”。也就是拉塞尔·M·林登在《无缝隙政府》一书中所说的:“通过清除内部障碍、组建职能交叉的团队,为顾客提供一步到位的信息和服务”。因此,自我管理团队就是一个“无缝隙”组织,它将高层管理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基础上,自我规划、自我实施、自我评估本团队的工作。他们首要关注的是如何灵活而迅速地对顾客需求、顾客满意度做出反应,而不是组织“控制”、“监管”、“领导”者等这些“内部官僚”的需求[26]。因为大幅度地减少了管理层次,使自我管理团队能够跳出传统组织中的“控制怪圈”,并变得反应更灵活、信息更灵通、沟通更充分;因为有更多的自我决策、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权力,使他们更感觉受到了尊重,也使工作更富有跳战性和自我实现的成就感,并因此使他们对工作结果更负责;因为有更直接面对顾客的机会,使他们有更多的合理决策所需的各种信息,进而使他们能更迅捷而正确地作出市场判断和市场决策。等等。从理论上说,这样的自我管理型团队,如果再加之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中提出的,通过“共同愿景”的引导并增进“团体学习”,那么,这样的团队必将是真正是“无为而治”又能取得辉煌业绩。事实上,根据奥斯本与默兰十多年的实践表明,只要是那些需要团队密切协作与有机互动才能完成工作的组织里,而不是那些专业化程度很高且生产安全风险极大,员工需要数年努力和长期积累经验才能做好的工作场所,或者是在某些组织内部,对根深蒂固的工作规则的挑战会引发巨混乱等组织之外,自我管理团队的组建,的确给无数的经济组织带来一流绩效。奥斯本、默兰提到一个负责绘制企业业绩图的小组,自我管理型团队实施第一年,收入就上升26个百分点,其中物价上涨因素仅占5%;第二年继续增长。1995~1996年度结束时,统计结果显示,3年内收入增长共计195个百点,其中累计物价增长因素仅占15%。客户满意度也大幅提升,比利1991年的29%翻了三倍,1996年产品的质量和及时到位率都超过95%。[27]
归结上述,我们可以发现,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不仅仅是一种理想,或者甚至是一种空想,只要谨慎地、有效地、科学地付诸实施,是有可能实现并取得辉煌业绩的。这就是算是老子“无为而治”的善的一面。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从“恶”的一面看,老子却由此而得出了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的思想(“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道德经·十九章》),最后并得出了返归到“小国寡民”理想国的消极无为。显然,依据老子逻辑,这依然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论。因为既然“无为”可以达致“无不为”,那么“绝圣弃智”等以及返归“小国寡民”的理想国,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也是可以通过逻辑思考推理而出的。(“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八十章》)这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所谓的逻辑推“理”有时也是靠不住的,也就是康德所谓的“纯粹理性”是靠不住的。推“理”也得符合常“理”,这个常“理”就是理性与存在合一的产物。这里也可见康德理性与存在统一的危机;二是老子的错误不在于他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国这一乌托邦式的思想主张,因为正如陈国庆、张爱东所说: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代表了农民这个阶层的要求,即具有平等、平均的思想主张,……不代表腐朽的奴隶主贵族阶层的利益。”[28]在我们看来,老子的错误在于,他大有教导人们付诸实施和行动的意思。你看他在第八十章所讲的是多么地富有可操作性,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而我们又可以想象,不管老子的思想主张代表着谁,他的本意或许的确是有追求平等、平均的意旨,而且这样的“小国寡民”也可能的确能使社会和谐安定,能使生活于其中的人心境平宁安和,但如果真的按照他所说的实施,“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让“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显然是逆社会潮流而动,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显然起障碍,因此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如此看来,老子实在又不如柏拉图,他就曾直言不讳地说,他在《理想国》中所构想的“理想国”只是一个和谐、完美国家的理念,因为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是有差异的,所以他并不指望他所构想的蓝图能够真正百分之百地在现实中实现。他只不过是为一切不理想、不完美国家提供一个改良的模式,一个理应如此的标准,“一个幸福的国家”的“神圣的原型”。[29]从老子与柏拉图的对举中,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发现,理性与存在的合一有时也是善恶并存的。这种“合一”的文化,也即是曾仁强所说“一内涵二”的思维,想到了就希望能够做得到,一旦在现实中碰了壁,就心灰意冷。这才是我们在前文所说的,在中国产生“隐士”文化的根本所在。而中国文革时期喊出的“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更是这种理性与存在合一的文化结出“硕果”。
然而,就本书完稿之际,李航先生对于老子“小国寡民”思想,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他认为老子思想符合绝对光速宇宙观,宇宙在宏微、观领域都是有边界的,而且在“边界”处,往往“违背常理”:如速度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同的,但到宇宙宏观边界处,却具有绝对恒定的光速;物质通常情形下是无限可分的,但到边界处,即到了最微观处,就要受到测不准原理的限制;空间在通常情形下是连续而平滑的,时间也是连续而平滑的,但到边界处,时空会无限弯曲并且中止。这样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应该这样理解,即“道是可以被阐述的,但是它违反常理”;“名可名,非常名”也应该理解为,“可以给包括边界状态的事物以准确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和平常我们认为的名字不一致”。于是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虽然违背常理,但却是老子给出的“极端美好社会的边界条件”。超出这边界,社会就不可能“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然而,在老子看来,这个边界社会能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因此,也不失为一种边界社会的理想。而这是一种微观社会的一个边界;在宏观社会,其边界则便是“国家昏乱”。那么,中间态的社会是什么呢?那就是《论语》中孔子给齐景公说政时,所阐发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君要做得象个君,臣要做得象个臣,父要做得象个父,子要做得象个,这就是一个“有层次、有规范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与我们平常所认识的社会是一致的。在社会中,人人有自己的位置,不同位置的人各有不同的行为准则,这是一个以礼来规范的社会。在这里,孔子并没有涉及国家的大小,显然,无论大国小国,只要是需要社会层次的社会,就都符合这样的规律”。李航进一步认为,孔子说的是社会的中间态,而老子说的是社会的边界状态。老子在《道德经》许多地方都在谈论“边界”,因为,在老子看来,知道了违反常理的社会“边界”,就更容易在常态的社会中游刃有余,这就叫“知止可以不殆”(《道德经·三十二章》)。边界就是“止”。如果这样的解读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再也不能说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是反动的,倒退的。老子的“小国寡民”是要说明人类社会的最本真的原状,它象是一把尺子或者是镜子,用来衡量现实社会的“发展”状况,并有利我们在“小国寡民”社会的启发下,更好地界对治现实、对治社纷乱。这才叫“知止可以不殆”。但是,不管怎样,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在中华文化史上,的确产生了消极无为的影响,使中华文化隐隐约约弥漫着悲凉的气氛。这是不容否认的。而这看来既不是老子的错,——因为,如果李航的解读是正确的,那么,“消极无为”就不是老子的本意;也不是用的人的错,因为老子不讲常态,却去讲“边界”,当然容易引起误读、误导,而且即使误读、误导了也是可以谅解的。在我们看,最为根本的错却在于文化本身,在于文化始终是善恶并存的。就是一种最为至“善”的文化,一旦推到极致,推到“边界”,其“恶”的一面,就会无情凸现。[30]
至此,我们不能不提出一种基于我们所倡导的有机社会理论背景下的“动态相对主义”,或者说是“有机相对主义”的主张。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相对主义”,是静态的、无机的,因此是必须予以批判的;动态相对主义当然是动态的、有机的,因此就值得提倡。举例来说,孔子的“中庸”之道,本意是求人们为人处世时,要在动态之中去把握“中”,这就是所谓的“时中”,即要依“时”而守“中”,所以是动态的相对主义;而“折中主义”是一加一除于二的东西,就是一种静态地去守“中”的静态相对主义。再比如说,老子“无为”思想,你如能动态地去理解他所说的三个“不”、三个“宝”,如用“柔”、“不敢”、“不争”等,你也必须动态地去掌握,要把握一个“时中”问题,要不然,如果象武松那样在景阳岗上遭遇猛虎,你用“柔”,那是自寻死路、自陷绝境。所以只有动态地把握“无为”,掌握“时中”,才能展现“无为”的积极性,达致“积极无为”,你才能真正实现“无不为”的理想;而如若静态地去理解,你可能就会跟着老子逻辑,由“水”想到了“柔”,由“柔”想到了“不敢”,由“不敢”想到了“不争”,再由“不争”就会自然推理出“小国寡民”的主张来。当然,老子的《道德经》始终是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一点却是不容否认的。我们在这里只是希望读者能正确理解有机社会理论,运用动态相对主义去正确理解《道德经》。我们就用这一点“希望”来结束本章吧。
--------------------------------------------------------------------------------
[1]彼得·圣吉著、郭进隆译:《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2版,第171页。
[2]彼得·圣吉著、郭进隆译:《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2版,第193页。
[3]彼得·圣吉著、郭进隆译:《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2版,第168页。
[4]彼得·圣吉著、郭进隆译:《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2版,第172页。
[5]戴维·奥斯本、彼德·普拉斯特里克著,谭功荣、刘霞译:《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6]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第172页。
[7]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第172页。
[8]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第171页。
[9]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第168页。
[10]转引自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第168页。
[11]转引自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第172页。
[12]彼得·圣吉著、郭进隆译:《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2版,第171页。
[13]此段未标注引文参见,彼得·圣吉著、郭进隆译:《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2版,第168—173页。
[14]本段未标注引文参见,彼得·圣吉著、郭进隆译:《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2版,第173页,第276—277页,第220页。
[15]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第109页。
[16]《独秀文存》,卷二,125页,上海亚东图书馆,民国15年。
[17]《西滢闲话》《管闲事》,新月书店,1928年版。
[18]《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3页。
[19]高专诚著:《孔子·孔子弟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7-98页。
[20]成中英著:《合外内之道——儒家哲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21]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第393页。
[22]转引自杰克·D·奥斯本、琳达·默兰著,李松玉、赵辉等译:《自我管理型团队》,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23]转引杰克·D·奥斯本、琳达·默兰著,李松玉、赵辉等译:《自我管理型团队》,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
[24]杰克·D·奥斯本、琳达·默兰著,李松玉、赵辉等译:《自我管理型团队》,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145页。
[25]冯·哈耶克著、邓正来编:《哈耶克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页。
[26]拉塞尔·M·林登著:《无缝隙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27]杰克·D·奥斯本、琳达·默兰著,李松玉、赵辉等译:《自我管理型团队》,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页。
[28]陈国庆、张爱东注译:《道德经》,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252页。
[29]柏拉图著:《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3页。
[30]本段内容,大量参见李航著:《道纪》;来自:http://blog.sina.com.cn/u/3d97f564010000ym2006年3月9日15:30下载。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