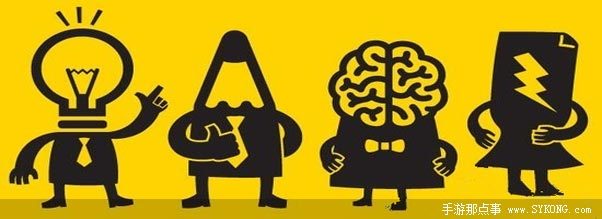十年前,知识经济已开始成为热门话题。著名管理学者,笔者的恩师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在1991年撰文于《哈佛商学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更是以日本公司对其“知识创造”理论的生动诠释,令“知识”这一关键词深入企业和学界。
熟悉野中的人都知道,“知识创造”理论是他几十年来“用脚走出来”的理论。1970年代,野中去美国加州伯克里大学求学之前,曾在富士通任职九年。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九年的企业的经历,为其对日本企业运营特点中“隐性知识”的把握,起了决定性作用。从美国返回日本后,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地奔走于各大企业间,从未停止过对日本企业管理特点的亲身体验。野中带研究生时,很少明说具体道理,而靠学生自己从企业访谈和课堂讨论中去领悟。他甚至拒绝使用电脑,认为电脑是当今对“显性知识”顶礼膜拜而忽视“隐性知识”的最具象的表现。“知识创造”理论的创建过程本身,正与野中知识理论中的中心思想相符:知识具有其隐性特质,如果忽视了“隐性知识”的发掘,便完全丧失了创造新知识的意义。
许多人说,日常生活中的野中在身体力行他的理论,我却以为,野中的理论是他所持有的基本理念的体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日本理念的写照。正是日本的特定的人文背景孕育了“知识创造”理论。在许多中国企业努力使自己向西方一流大企业的管理标准靠近的今天,这样一种与美式管理格格不入,但为世界所瞩目的理论,对我们持有何种启发?!
“知识创造”理论野中理论所强调的主要论点,就是商业组织内的“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通过“群体化”(Socialization)、“外在化”(Externalization)、 “组合”(Combination)、 “内在化”(Internalization)这样一种螺旋似延续的交互作用系统,实现新知识的创造。
隐性知识,是这一理论体系中最为关键的概念。但这并不是野中的独创。野中的贡献是将匈牙利出身的物理化学家兼哲人,迈克尔8729;波兰尼(Michael Polar1yi),所定义的“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的概念,运用到了企业组织的研究中。早在上世纪60年代,迈克尔8729;波兰尼著书《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提出任何知识都有其显性和隐性的两个特性。 “显性知识”是可以用语言文字和图像符号来表达的知识;而隐性知识则无法用言语逻辑表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例如,木匠教徒弟,许多技能无法言传,只能手把手地示范,然后由徒弟自己身体力行地去体验这些技巧。
野中主张,“群体化”的过程,是由“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传授。木匠以身教带徒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外在化”则完成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换,例如,工程师将脑中模糊的设想用图表最终明确地表达出来,是一个将“隐性知识”转变为“显性知识”的过程。“组合”的目的,是将“显性知识”与“显性知识”重新组合加工,以形成新的“显性知识”。学习小组的讨论会便可以达到这种目的:大家各自说出自己的理解,然后讨论出一个新的看法。“内在化”是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换。例如,读一本书,读者接触到的是显性知识;但不同的人从同样的内容中得到的启发却大相径庭。这是因为读到的内容最终会与读书者自身的理解相融合,成为当事人所持有的“隐性知识”。
“知识管理”:一个巨大的误解今天,无论在学界还是企业界,“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这一名词被广泛地使用着。但是,由美国企业率先掀起的追逐 “知识管理项目”的热潮,和随处可见的与企业知识管理有关的计算机软件,正在传播一个巨大的误解。
所谓“知识管理项目”的具体做法,就是通过强大的信息技术手段,对企业既存的技术资料等“显性知识”用各种IT技术来进行管理。虽然这些项目也涉及到对“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s)”的管理,但也只是停留在“显性知识”的层面。例如,通过电脑迅速调出具有某项专长的员工资料。这种知识的管理方法,完全忽略了对“隐性知识”的发掘。即使是单就对“显性知识”的“管理”而言,这种做法也是不完全的。根据迈克尔8729;波兰尼的定义,所谓的“显性知识”,在本质上也有其隐喻性的特质。 所以,“显性知识”充其量也不过只是知识的载体,人们只是通过这种知识载体接受传递过来的讯号。真正的知识,必须通过人的大脑与这些讯号的交互作用而建构新的理解,而重新生成。很明显,将“显性知识” (或说是知识的外显形式),视作了知识本身的“知识管理”的提法,无法真正达到对知识进行管理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本质上追求的是一种静态的“管理”,在既有的“知识”上做文章,而不去追究如何将新知识不断创造出来。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大多数“知识管理”项目的实现的是对“信息”的管理,而并非对“知识”进行管理。
尽管被视为“知识管理”界的泰斗,野中从一开始就反对“知识管理”的提法。1997年,美国施乐公司资助野中回到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商学院(Hass School)担任“施乐知识管理学教授”职位。 但是,野中拒绝接受“知识管理”这一说法,要求将自己的讲座教授(chair professor)的席位改为“施乐知识创新学教授”。结果最后野中成为这个商学院的“施乐知识学教授”。
正因为重视知识的隐性特质的存在,野中始终强调,知识是无法被“管理”的。所以落实到管理实践中,“知识创造”理论推行的是对“知识活动”,例如知识的采集、整理、审核、共享、交流、利用、创造等,的“管理”。企业可以通过设计一个特殊的组织机制(organizational mechanism),促进由“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不停顿地相互作用所负载的知识创造过程。所以,与“知识管理”不同,“知识创造”强调在重视“隐性知识”的基础上,对知识的动态变化过程进行管理。例如,日本公司中频繁实施的“员工换岗(rotation)”制度,能够促进员工对不同岗位的深入了解,从而提高企业中不同部门间的沟通效率。所以,在开发一个新产品时,技术部门能够很好地尊重理解市场部门所搜集到客户需求信息,而不只是以技术至上的心态来设计产品。这样,企业的新产品才能够用最新的技术来实现对客户要求的最大满足,最完善地体现企业知识的结晶。
“西方不识相”做了笔者五年导师的野中,从来没有说过这标题上的话,但却一直以他的身教传达着这个信息:西方风行的“知识管理”与“知识创造”理论的含义,完全背道而驰。如若归根结底,西方学界和企业界对如何管理“知识活动”的误解,与其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有趣的是,日本的几位世界著名的管理学者,全是在美国拿过博士的教授。与野中亲密合作的竹内弘高,和“人本主义”理论的始作俑者伊丹敬之等等。也许正是因为在美国的经历使得他们对两种文化的不同特性有着更加深刻的感受。回到日本后,这些学者学术工作重点中的一个明显的共同点,便是对欧美,尤其是美国企业中一些行为惯性的否定,和对日本企业与西方企业截然不同的一些特质的肯定。

野中的研究,将对这种肯定和否定的探讨提升了到了一个最鲜明的高度。“知识创造”理论从几个方面否定了美式管理的局限。首先,受制于西方源远流长的方法论,西方企业只认可“显性知识”,而倾向于无视一切没有转化成语言或符号的知识。由于明确的表达被视作交流的前提,“隐性知识”在西方企业的具体实践中,很难被归纳到知识的范畴里。其次,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中至高无上的个人主义,对知识创造所需要的集体的交流,形成障碍。另外,西方的方法论重“目的”而轻“过程”。所以西方企业偏向于对既有“显性知识”的管理,而并不真正涉及知识的创造过程。
“知识创造”理论对日本企业的肯定也集中在相互对应的三个方面。第一,东方社会与生俱来对“隐性知识”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成就了日本公司对“隐性知识”的大力发掘。第二,东方思想不主分裂与对立,对超越于个体的意义之上的“融合”的强调,尤其是日本社会中近乎极端的“集体主义”氛围,为“知识创造”过程中必需的人与人的相互交流,做出了充分铺垫。第三,在东方文化中,“目的” 是次位,只有“过程”才被赋予真实意义的。与亚里士多德的“终极目的”相对应,东方思想强调的是则“无止境”。所以,从来就与既有的知识相比,创造新知识才是最可贵的。
然而,隐性知识的“模糊性”,团体协调的“纠缠不清”,过程的“不可量化”,都是为“效率”至上的美式管理学界和美国企业在经营实践中所不屑一顾的。尽管在现代,“隐性知识”的概念曾由一个西方人(迈克尔8729;波兰尼)系统地阐述,但真正在企业管理思想上做出回应的却是日本人。萌生于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野中理论在中国企业的经营实践中是否较之在西方更具有其应用基础?让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逐点进行剖析探讨。
东方特质: “知识”和“知识生成过程”
如果说西方的文化背景妨碍了欧美企业对“知识”的理解,代表着东方思想的中国,则是“知识创造”理论精髓的哲学故园。所以中国企业在这个理论的运用上,应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与观念优势。中国文化注重感性,也就是知识的“隐性”特征。中国思想对事物的整体性与相互联系的强调,更是“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螺旋式相互作用的哲学基础。换言之,对“隐性知识”和知识创造过程中人的重要性的强调,在中国的儒、道、释、佛的哲学思想中随处可见。而东西方在所谓“知识管理”这个领域的差异,正可以由此归纳为两点:对知识这个概念和对“知识生成过程”的不同理解。笔者认为,体现在经营实践中,这种差异颇具代表性的特征,便是“分析”与“直觉”,“效率”与 “冗余”,以及对“个人”与 “团体”的对立。
西方的传统重视“分析”,对知识的“科学检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而知识必须表现为“显性”,是能够被“检验”的前提。东方的认识论却从来未忽视“直觉”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提倡直觉在认知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例如,老子被认为是中国哲学史上直觉认识方法的创立者,孔子的“默而识之”,则明确地对“直觉”的认识方法加以的肯定。禅宗的方法论,更是通过“顿悟”“棒喝”等实践,将对“隐性知识”的发掘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高度。
这种“分析”与“直觉”的对立,不仅在对知识的概念的定义上截然不同,也对于知识生成过程的认识产生大相径庭的理解。美国商学院中MBA教学的重点之一,就是要使学生掌握在商业实践中进行各种科学分析的技巧,培养学生树立一切都要用“数据”说话的理念。美国的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尤其擅长于将各种经营理念和实践模型化,然后向企业客户推广管理的“最优作法(best practices)”。在美国的管理界,持日本企业“毫无管理可言”之断言的学者大有人在,因为他们坚信,日本式经营中“直觉”大于“分析”的做法,是“不科学”的。然而,1980年代不断涌现出日本公司的世界性成功案例,为驳斥这种断言提供了最佳论据。美式的分析方法论在管理中的应用,也一再在中国市场的实践中受到挑战。1990年代后期,麦肯锡在实达和联通两个项目上遭遇的尴尬,应列作最经典的案例。
作为认识论的基础,西方的目的性和东方的整体性,对不同的文化对知识创造过程的不同理解,有很大的影响。 “冗余”,在西方企业中被认为是妨碍效率的大敌;而在野中理论中,却是知识创造过程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之一。实践证明,冗余的做法虽然有可能牺牲企业中短期的效率,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将会给公司带来极大的长期收益。野中曾举例松下电器的一位拜做面包的师傅学手艺的工程师。做面包的手艺看似与这位产品研究人员的工作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花在这项“无关”项目上的时间和精力,自然被视作“冗余”。但是,正是这一亲身经历,帮助这位工程师设计出来市场最受欢迎的自动面包机。日本公司中常见的研发方式也是一种对“冗余”效益的生动解释。许多日本公司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做一些看似毫无市场前景的项目,而且这些研发努力大都会以失败告终。以欧美的眼光来看,这是非常没有效率的表现。但是,日本公司正是凭借这样的实践积累了科研人才和经验,为将来最终开发出适应市场的产品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个具有高度凝聚性的集体,是野中知识创造理论必要条件。知识创造过程的本质,便是将凝结在每个员工身上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通过外在化、内在化、群体化和组合等转化形式,变为企业组织中共有的知识,并最终体现在满足用户的产品和服务中。这样的相互转化过程,如果缺乏“团体”的观念,是无法实现的。而西方对个人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个知识转化过程所必需的团体性。例如,美国企业中分工明确,每一名员工都像一个大齿轮上的一颗螺丝钉。这种分工细致的组织常态创造了效率,但同时,由于每个员工只对自己的一小摊任务了如指掌,对他人的工作毫无关心,很难实现通过企业组织的成员间的交互作用来创造知识的过程。
野中理论与中国式管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迈克尔8729;波兰尼的知识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回归”。中国企业无疑比西方企业能够更好地采纳构筑在东方认知论上的野中理论。例如,对中国市场的认识,对企业来说,很多时候是一种无法明确说明的“直觉”。这种时候,美式管理中强调的“量化”,对市场特性的描述丝毫不起作用。例如,农夫山泉面世时,饮用水市场已是强手林立。按对市场进行量化分析的套路,后来者应该采用低价进入方式。但农夫山泉却以与高于竞争对手的卖价成功地打入市场。这就是农夫山泉对市场的直觉认识:在中国这个迅速开放的市场,消费者对“优质”的追求心理正在形成。对“优质”进行暗示的略微高价,正是对一个难得的竞争瞬间直觉的把握。这种迅速而准确的把握,为美式商学院所教授的分析手段所无法胜任。
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特殊历史阶段,无疑令商业实践中充满“隐性知识”。和农夫山泉一样,许多成功的中国企业正是利用了自身这种对“隐性知识”的熟捻,把握了外国大企业无从推敲的机会。西方企业完善的分析体系,能够处理的只是“显性知识”;而对在中国竞争的企业来说,中国消费者日常生活中的需要,和这种需要的瞬息变化,在许多时候都是“隐性知识”,无法以量化的模型进行计算和计划。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在西方一流商学院得到“顶级”训练的“海龟”们,往往在回国后,根本无法以其“卓越的才能”驾驭商场竞争。
但是应该看到,东方文化中与知识有关的隐性特质,对知识创造中的组合和外在化过程都是一种妨碍。野中也一直呼吁日本企业适当地调节这种特质,从而保证两种不同知识特性的相互转换。中国企业的东方背景有助于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将个人的“隐性知识”进行群体化。这种群体化,能够很好地维持一个传统手工作坊似的小企业。但是,西方文化却更加适合将个人掌握的“隐性知识”通过系统化处理的“外在化”过程,使之变为每个组织成员都能够分享的“显性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发展一个现代化的大企业。然而,一个具有活力的企业,必须不断地再将这种既存的“显性知识”转移到每一个员工身上,成为企业员工所有的“隐性知识”。这种转化,可以说是“集体主义至上”的日本企业的擅长。而中国企业却不一定具有这个优势。最后,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企业不断将各种“显性知识”通过“组合”,具象到最终产品和服务上。这一过程,也正是对“显性知识” 能够井然有序地把握的西方企业的擅长。
许多企业正逐步认识到“直觉管理”的局限。为了在与世界一流的企业看齐,在与外国企业的激烈竞争中更上一层楼,中国企业没有间断过对西方公司的管理经验的努力学习。例如,许多企业聘请国外咨询公司,希望得到最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无疑,这是中国企业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但是,在吸取西方对“显性知识”的成熟管理的优势的同时,我们的企业不应忽视,学习西方的同时,应该从自身的特性和成长过程发掘出什么?
虽然“知识创造”理论的哲学基础源自于以中国传统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但是日本的民族性予以了这个理论许多独特的前提。中国企业不是日本企业。所以对野中理论的应用,也应如同对其他管理经验的学习一样,要取舍有度。例如,野中所倡导的知识的“群体化”的过程需要许多磨合时间。而当今中国市场上激烈的竞争格局和瞬息万变的变化,很难让企业拥有“冗余”的奢侈。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完成“知识创造”过程中的这一重要环节,是我们的企业和学者应该探讨的关键之一。而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所具有一些特点,足够令日本企业望洋兴叹。例如,野中强调 “异质”的成分对“知识创造”过程的推动。而过分强调集体优势、“扼杀”个人风头的日本企业组织中,往往具有知识“同质”化的毛病。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企业,从出生或再生的那一瞬间开始,不断有“异质”知识,不断从崭新的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外国企业的竞争压力中涌现。
无疑,中国企业具有野中所倡导的“知识创造公司”的一些得天独厚的特质。但是,这并不是实现“知识创造”过程的充分条件。虽然我们存在优势,如果无法找到一个适合自身特点的力度去努力,那么,无论是学习欧美企业还是学习日本企业,任何企业都有可能在 “邯郸学步”中,削弱其与生俱来的能力。
野中的理论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日本企业能够打败美国企业并不是因为日本企业变成了美国企业,而是日本企业找到了自己的运营特点,并发扬光大。期待不久的将来,中国企业也会以自身的特质,傲然面对全球化的竞争。我以为,这是野中理论带给我们的最大启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