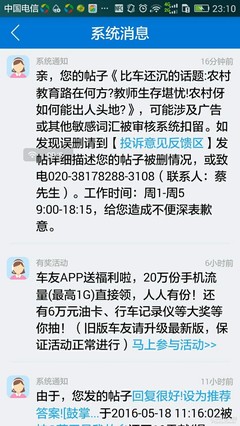无论出于尊重的需要(黑格尔)还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这种指向在以往或当今始终是普遍的事实,以经验的眼光来测度,将来也会继续存在;我所指出的这种指向便是革命;我说的这种革命,不只是刀光剑影、血留成河的暴力革命,同时也将经济自由主义及其由于人类自身其他因素造成人们的伤害归于革命的范畴。这样与其他人所表述的概念应该存在本质的差异。也算是一种新“革命”学说。
将革命归咎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扩展,这已经受到其他学者的批驳,在此将不赘述;然而将革命归咎于自我实现的副产品,这无疑是十分有道理的。
我认为,自我实现的需要或尊重的需要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但是对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无度纵欲的真相,却缺少一种深层次的认识。由此,在对自我无法正确地审视,我们难以对自我的缺点正面批判的情况下,在这个过程中或结尾,则随意地将目光转向了其他:或是将革命的原因归咎于天灾,或是人祸。而忽视了我们本身的弊端和缺憾。那么,这样的结果便是,我们不论是经济革命还是暴力革命的对象,所意识到的也将是他者是敌人:我们革他们的命,他们革我们的命。 作为一种价值批判哲学,我认为批判者和批判对象的阐述都是有一定价值。可是我们的表现并非能够认识到一种学说的局限性:在某时某地,它可行,具有价值;在某时某地它不可行,不具有价值,甚或可能带给人们伤害。而今的马克思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弊端与长处我们已经有所察觉。但我们缺少的就是将一种学说教条化的粉碎或对诸种学说的连贯性与包容性,及其对于它们之间的互补性或相对真理的探索。虽然我们在持续探究着,但这种探究的深度和兼容性确实值得怀疑。如果我们查看一下我们的争论的激烈程度与复杂背景,将会深有感触:我们的争论盲目而偏激,实质已经掩盖了真相,对于认识事物的本真不但无益而且还有害;也很容易晓得偏见是多么根深蒂固;自我反思是多么难得;宽容或交流对于我们是多么欠缺,并且格外难能可贵;革命对于我们是多么不可或缺,并且是灵汤妙药。 因此,“革革命的命”,对于任何人而言,都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并且很容易就可以宣布胜利。它要求我自我实现时允许他者的实现;我赢得尊重的同时,也必须尊重他者;我所认识的事物和坚持的观点都有局限性,因而需要求大同存小异等等。而这,由于我们尚不能祛除自身的疾患,精神漏洞尚未填补,“革革命的命”也将是长期持久的系统工程。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