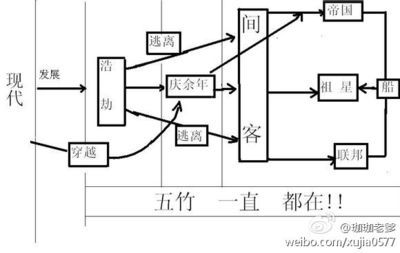过去两百年,知识分子的影响稳步增长。在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世俗知识分子地位的上升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回顾漫长的历史,在许多领域内,这都是一个新的现象。诚然, 知识分子 开始是指教士、书记员,还有占卜者。从那时起,他们就宣称自己制导着社会。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是宗教文化的卫道士,所以无论他们是天真质朴,还是老于世故,他们对于道德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革新,都必然受制于外部权威确定的准则和既定的传统。他们不是也不可能具有自由的精神,成为思想的探险者。(《知识分子》P1)
如果以前知识分子的地位并非很高,随着社会进展,知识分子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目前知识分子问题在思想界和学术界以及全社会逐渐引起高度重视,成为社会热点话题。这不只是人们认识到以往贬低知识分子为臭老九、歧视知识分子是错误、不理性、不明智的,社会的飞速发展也说明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人类解放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人类逐步寻求独立、自由与民主解放的启蒙者、先行者、牺牲者;也是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怀疑勇气、社会正义与道德、反抗和追求真理的不怕流血、牺牲精神使得人们予以关注、景仰,并且信任这支队伍,支持知识分子的正义之举。当然由此引起的知识分子地位的提升也是人们对知识分子另眼看待的一个原因。虽然人们习以为常将知识分子挂在嘴边,由于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不是很清晰,平时人们所认可的知识分子与官方存在着差异,思想界和学术界的表述也不一致。知识分子的定义也显得特别混乱。人们在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存在着诸多疑问、错误认识。而学术界对知识分子的组成 那些人应该归属于知识分子行列,知识分子究竟是群体还是个人,及其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没有彻底梳理清楚。自然知识分子也值得研究一番。 按照葛兰西的阐述,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的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例如教师、教士、行政官吏,这类人代代从事相同的工作。(赛义德,[Edward W Said]《知识分子论》P11) 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依据葛兰西的观点都存在于体制内,他们经常是以服从体制,顺从体制,背叛自我,建构者的面目出现,而不是以批评体制,反抗体制,表现自我,解构者的面目出现。古代或现代的体制内的文化人按照葛兰西的界定,都应该归属于知识分子的行列。葛兰西在《狱中杂记》中讲: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虽然人们平时所认定的知识分子大致也可以归属于这个行列,这种比较宽泛的知识分子界定,虽然使得知识分子队伍看起来特别壮大,不过并未起到知识分子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实质作用。不过一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没有发挥知识分子作用也就不能称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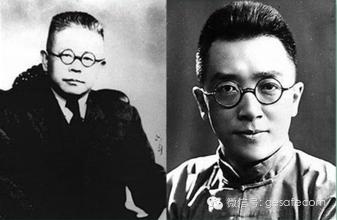
由于国家或体制对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垄断地位,使得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国家或体制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或理念。在中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等世界各国家这种知识分子都相当多。譬如:歌德担任过魏玛公国枢密参事,哈耶克执教过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洪堡也曾经担任过普鲁士驻罗马教廷代办;而中国历史中所存在的如今人们普遍认同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他们不但生活于体制内,而且决大多数属于官僚阶层,如道家的鼻祖老子作过负责管理典籍的周守藏室之吏,庄子曾经担任过漆园吏,儒家的孔子曾在鲁国任职大司寇,法家的李斯任职丞相,商鞅任职秦国的宰相,墨家的墨子曾为宋国大夫,屈原曾经在楚国任职三闾大夫等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传统的知识分子概莫如此。但是作为产生于官僚阶层的知识分子并未妨碍他对社会的建构与批评责任。不过中西还是存在很大差异,西方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相对要自由一些,不象中国的教育是由国家垄断。中国的体制内的批评就显得格外委婉、无力。这也是与他们身在体制内有关,如果批评丝毫不掩饰,过于激烈,官职不但无法担任,身家性命也很难保。所以他们的批评就很僵硬,他们的活动也缺少活力,活动范围也十分有限。与目前的批评性知识分子群体存在比较大差异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始终将建构社会,找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不只是仅仅批评、解构社会 作为自己的主要社会责任。譬如,孔子的儒家学说中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申不害言术、商鞅言法、慎到言势、韩非子合法术势,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产生于官宦阶层的知识分子,不但没有如目前批评性知识分子所倡导的仅仅行使批评权利,而且在批评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建构阐述自己的学说,他们有的也在设身处地参与社会建构。譬如历史上有名的王莽变法、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虽然由于各种因素没有成功。但是知识分子所发挥出来的建设才能是后来的知识分子可望不可及的。即,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注重批评,而不是建构理论,将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缺少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作风。因而,如今的知识分子给人们的印象就是隔断了与普通大众的联系。实际现在的建构与解构已经不成正比,世界主潮也是相对消极的解构占主流。即便是资本主义的批评家,共产主义的理论大师马克思、恩格斯也未能摆脱此种状况,使得自己的学说臻于完善,摆脱局限性。但并非只是如此,现代也有解构与建构共同存在一身的知识分子,也不乏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并且成功的案例,譬如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与斯大林,陈独秀和卡斯特罗,萨特与哈耶克等等。按照赛义德的话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所代表的知识分子角色是这样的:他接受过历史语言学的专业训练,既是意大利工人阶级运动的组织者,而且在自己从事的新闻业中也是最具反省意识的社会分析家,他的目标不只要造成社会运动,而且要塑造与此运动相关的整个文化形成(cultural formation)(《知识分子论》P11)。以葛兰西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事业不只限定在追求观念、思想自由和奋不顾身批评社会、参与运动为观念献身的精神上,还多了一层塑造社会文化的责任,建构社会的责任。也就是他在社会中发挥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可喜的是,现在西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已经逐渐衰颓,建构性后现代主义(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已经开始引起人们关注,并且为很多人接受。 第二类是有机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在葛兰西眼中,这类人与阶级或企业直接相关,而这些阶级或企业运用知识分子来组织利益,赢得更多的权力,获得更多的控制(《知识分子论》P11),有机的知识分子现在也比较多,如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知识分子论》P12),公关人员、企业形象策划人员、会计人员、记者、企业经理、律师、税务师等等都可以归属于知识分子行列。由于葛兰西对知识分子定义比较宽泛,很多人都可以和知识分子靠上边。当然他所说的这两类知识分子也是平时人们所认可的知识分子。在中国语境下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拥有某一学科文凭或职称的人,研究员和专家是知识分子,讲师和教授是知识分子,即便中专生或者大学生也是知识分子。并不管他的职业属性、学术造诣高低、社会作用。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没有了贵族色彩,知识分子完全成为很普通的大众形象。由于有机的知识分子在现代产生的比较多,那么我们将他们叫做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无不可。 而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存在着很大差异,譬如现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更活跃,追求自由的心态更强烈,摆脱压抑的愿望比较高,传播新知识的能力比较强,接受的新观念比较快,他们有意无意地引导着群体思维,改变着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由于国际交往、交流逐步广泛和合作领域日渐增多,地域限制、文化界限被打破,促进了友谊和信任等方面的建构。有机的知识分子对国际社会作出的正面工作是传统的知识分子无法匹敌的。海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说: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别部门的专家。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必须特别有聪明才智来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四章)。如果按照海耶克规定的知识分子涵义,这些可以很快接受新观念和传播新思想的都可以归于知识分子的行列。但是我们也不应该乐观,有机的知识分子虽然为社会进步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不过随着知识分子地位的提升,形成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责任的背叛和知识分子的失落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学术界的注意:美国社会学家古德诺(Alvin W. Gouldner)几年前就说知识分子是新阶级,而掌理知识者现在很多已经取代了旧式的有产阶级。他们在地位提升以后,已经固步自封不再发挥对社会的有力批评和道德权威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古德诺也说,知识分子随着地位的晋升,也不再是向广大公众发言的人了;相反的,他们成为他所谓的一种批评话语文化(a culture of critical discourse)的成员,每位知识分子,书籍的编辑和作者,军事战略家和国际律师,所说、所用的语言都变成专业的,可为相同领域的其他成员所使用,而专家与专家之间的共通语言是非专业人士大都难以理解的。(《知识分子论》P15)如今有机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具有能力 向(to) 公众 为(for) 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知识分子论》P16)已经不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向他的公众做清楚有力的表述 。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无意地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 。(《知识分子论》P17)知识分子也不再向民众言说、呐喊,勇敢地指证或抵抗,进行人文关怀,为正义和真理献身的精神已经彻底失去了。所谓普遍的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 他们的地位已经被 特殊 的知识分子( specific intellectual)所取代。(《知识分子论》P16)作为社会良心、正义、自由、道德化身的批评性知识分子让位于专家、学者、公关人员、空中小姐、企业主管等等,这不能不说是知识分子的悲哀。 上面葛兰西和哈耶克所说的,也是人们认为的知识分子定义相对宽泛一些,目前国际思想界虽然对知识分子定义的阐述存在着不同标准,不过现在思想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标杆已经不再那么宽松,而是要求相当高严格,限定得特别紧。并非上述的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可以随便入住这个象牙塔。譬如时代周刊(TIME)的知识分子定义就比以上严谨得多: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观念而追求观念。如霍夫斯泰德(Richard Hofstadter)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Christopher Lasch)说知识分子乃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四章)。《时代周刊》相对于葛兰西和海耶克包括平时人们对知识分子宽泛的定义就要苛刻得多。就体制内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附和、顺从、不敢批评的表现就无法进入知识分子的行列。实际上海耶克和葛兰西给我们提供的只是知识分子的大致概念,而《时代周刊》所说的知识分子是海耶克和葛兰西所说的知识分子里面的精英,代表性人物。依照《时代周刊》严谨并且苛刻的条件,可以归属于知识分子的只是凤毛麟角。而法国学者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所要求的知识分子甚至比《时代周刊》还要苛刻:他们(知识分子)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以某种方式说: 我们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 (语出《新约·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知识分子论》P13)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 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知识分子论》P12)知识分子是独立特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接了当地责难的。(《知识分子论》P15)就这种不是凡夫俗子所能为的抛弃物质利益而为信仰生活、真理献身的精神已经将很多自诩为知识分子的挡在了门外。这种知识分子不但需要抛弃既有物质利益,也需要以不在这个世界的角度,勇敢地对各种现象进行批评,来支持、维护的正是这个世界的真理与正义的永恒标准。(《知识分子论》P12)依此标准,即便搜罗历史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历历可数。不过朱利安·班达也提供了可以归属于他限定的知识分子行列的典型人物,如斯宾诺沙(Benedict de Spinoza, 1632-1677)、伏尔泰(Jean francois Arouet Voltaire, 1694-1778)、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等等。朱利安·班达对懂得知识但不是知识分子和真正的知识分子进一步他的独特观点,班达所举的例子显示他并不支持这种观念:完全抽离的、超乎世俗的、象牙塔里的思想家,极为孤立并献身于深奥、甚至可能是玄奥的题材。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知识分子论》P13)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他们是具有象征性的人物,其特征在于坚决远离现实的关注。(《知识分子论》P14)殷海光先生对此阐述道:做一个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典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 只问是非,不管一切 。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希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 精神食粮 。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取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时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难免的事。依这推论,凡属说话务求迎合流俗的读书人,凡属立言存心哗众取宠的读书人,凡属因不耐寂寞而不能抱真理到底的读书人,充其量只是读读书的人,并非知识分子。(《中国文化的展望》十四章)殷海光先生和朱利安·班达一样,也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 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的寥寥无几。殷海光先生接着说:在现代西方,罗素是十足合于这两个条件的。史迪文逊(Adlai Stevenson)显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就我所知,明朝李卓吾勉强可作代表。自清末严又陵以降的读书人堪称知识分子的似乎不易造一清册。而且,即令有少数读书人在他们的少壮合于这两个条件。到了晚年又回头走童年的路,因此不算知识分子。(《中国文化的展望》十四章)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 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而更加苛刻的是班达的观点,班达是这样为知识分子定义的:班达所认为的知识分子就成为独立特行的特殊群体,他们的身份是一般人无法企及的,而且是他们代表着社会的良心,按照班达和殷海光的观点,可以归属于知识分子这个象牙塔群体的微乎其微,布鲁诺(Giordano Btuno,1548-1600)、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 )、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李贽(号卓吾,1527-1602)应该属于这样的知识分子。
而对于生活在体制外批评氛围相对宽松且性情悲观、沮丧,属于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美国社会批判家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 1916-1962)指出了知识分子也可以生存于体制内发挥着知识分子的批评责任:独立的知识分子不是怀着沮丧的无力感面对边缘地位,就是选择成为为数不多的圈内人。这些圈内人不负责任、自行其是地作重要的决定。 (《知识分子论》 P24)针对人们对存在于圈内的知识分子履行批评责任的疑问,赛义德说: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向社会宣扬的是理念或观念,并不意味主要为了强化自我或颂扬地位,亦非有意服侍有权威的官僚机构和慷慨的雇主。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而这使得个人被记录在案并无所遁形。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知识分子论》 P23)实际这种圈内人也存在不少,他们的进步思想也不可忽视。譬如鲁迅先生曾在中华民国政府任职,也并未停止他锐利的批评;洪堡在担任普鲁士官员期间,也没有停止发表不同的声音;这样的知识分子还很多,即便现在也仍然有不少开明人士在体制内做着发挥着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过这里有一个知识分子很避讳的为谁服务的问题。加入体制内或者说成为圈内人给人们一种模糊印象,好像他们已经被安抚、招安,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本色。实际并非如此,他们也是为人类服务,并没有缺少批评责任。
知识分子不但要行使批评政治的责任,而且也必须行使批评社会等的责任。因为一种文化的形成并非仅仅从政治这一个角度可以解释的:知识分子属于他们的时代,被资讯或媒体工业所具体呈现的大众政治的代表簇拥同行;愈来愈有力的媒体流通着形象、官方叙述、权威说法(不只是媒体,而且是要保持现状的真个思潮,使事情维持于现实上可被接受、批准的范围内),而知识分子只有借着驳斥这些形象、官方叙述、权威说法,借着提供米尔斯所谓的揭穿(unmaskings)或另类版本(alternative versions),竭尽一己之力尝试诉说真话,才能加以抵抗。(《知识分子论》P25)与以往的表述不同的是,赛义德更进一步将对大众文化的批评作为一种知识分子必须的社会责任,而粉碎揭穿刻板印象也正式成为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这种言说的自由也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言说自由,所谓的粉碎刻板形象,挖掘出遗忘的事情,连接起被切断的事件,举述原来可以用来避免战争及之而来的残杀的另类作法。(《知识分子论》P25)也就无从谈起。赛义德(Edward W Said)所定义的知识分子与《时代周刊》、班达和殷海光的观点也极其相似: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开场合这么说。(《知识分子论》P25)赛义德的行动也为知识分子的定义做了注脚,他为《撒旦诗篇》的作者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拉什迪辩护的时候,遭到伊斯兰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死亡警告,但是他丝毫不畏惧。他也经常参加各种演说,宣传自己的主张。用行动来实践知识分子的批评责任。 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按照以上各观点的综述,应该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是独立特行的,不趋炎附势,不附和其他人的观点,不因他人的威胁而妥协,甚至可以为观念而献身;积极投身于批评工作、揭穿真相、沟通交流;以人道主义、正义和自由的高度阐述自己的主张,敢于讲真话,言行一致,他的观念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各自都有自己的思想,他是没有朋友的人,他们又是一个群体,因为的责任和目标相同。他们既可以是专门家,也可以是普通民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