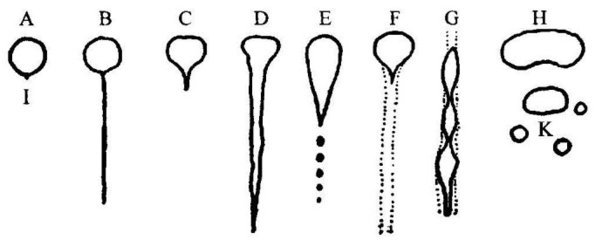流亡者赛伊德:知识分子与东方主义
陈岩锋第一我认为,东方社会(就地理位置而言)在国际上比较知名的学者有两位,一位乃日裔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另一位乃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得华·赛伊德(Edward W. Said)。就离开本土这个层面上而言,他们两位都是“流亡者”。虽然都是流亡者的身份,但是阐述的观念却存在不小差异。具有福山思想代表性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是以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建立自由民主社会以至形成“历史的终结”为主题,而赛伊德认为自己的主要观点是在对西方傲慢与偏见的反动中,建立融合各民族文化反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多元化国际社会。即所谓的“共存”(coexistence)社会。二人对建立未来国际秩序的阐述在某种程度上虽然看起来有些类似,但是貌合神离,差异特别巨大。赛伊德是反对福山“历史的终结”论断的。他将福山的论断视为粗暴和武断的,甚至是极端错误的。这点按照赛伊德的观念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原因造成的,那就是福山出生在早已属于西方社会的日本,这个政治概念的,文化概念,历史概念的西方;而萨伊德不但出生在巴勒斯坦,这个地理位置上的东方社会,同时也是政治概念的,文化概念,历史概念的东方社会,与西方曾经有激烈或者正在激烈冲突的东方社会。那么,他们的观念都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萨伊德的观念与福山存在根本的差别,打上了深刻的东方色彩、阿拉伯色彩也理所当然。虽然我这样依照赛伊德的观念来说他们的差异有决定论的涵义,也无法证实是否可取,不过萨伊德的后殖民主义者身份造成了他与福山的不同见解也不可不说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或者说这样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赛伊德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分析,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的终结理论都以暂时失败或者永远失败(因为再也无法回到以前那种理论状态)而显现,他认为福山的终结观念错误也很合理。也许有其它目前我们未知的原因造成了这种抵牾也很可能。我们也就不做过多而无谓的猜测了。赛伊德反对福山的论断是肯定的。赛伊德在多种场合,不但富有激情地批评了福山的论断,同时也批评了其他类似福山的“终结”观念,即“意识形态的终结”等等。认为它们是带有地域性的意识形态,必将过时而成为历史的垃圾。赛伊德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这两个学派都是错误的。我的意思是说,意识形态继续存在。当然,“历史的终结”是胡说八道,因为历史继续使我们惊讶。当代历史一直动荡不定,以致“历史的终结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国家”这种荒唐的观念只可能产生在美国。我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依然在考量“意识形态的终结”。塑造出那个术语的贝尔(Daniel Bell)是我的同事,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与他很熟。当然,随着冷战的结束,或如美国所说的,当“我们”赢得了冷战时,意识形态就已经消亡了。但我认为现在美国和世界上许多非欧洲的地区都出现了许多批判的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地区,经济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依然没有正视、处理许许多多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政治的问题。我认为“意识形态的终结”这种说法的吸引力很快就会过去,我们将回到现存的意识形态的大脉络--资本主义--并检视它。《知识分子论》P110赛伊德在批评终结理论的时候并没有进一步追究自由与民主这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可调和性和复杂性及其导致的负面效应,显得理论低气不足而意犹未尽,不过难能可贵的是,他已经指出了资本主义实现人类目标的有限性和世界本身的多样性给资本主义带来的诸多难题,终结理论的荒谬与不可实现的原因。虽然赛伊德批评了福山的过分乐观或者按照他说福山乃“胡说八道”的观念,所谓的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历史的终结”的论断,但是他并非就此悲观与绝对化,就是主张社会乃“文明的冲突”或者“社会的冲突”的论断,亦即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文中或拉尔夫·达仁道夫(Ralf Dahrendorf)、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和科塞(Lewis A Coser)的论断。同样,他也认为这种冲突理论不但跟福山和贝尔的终结观念一样是武断的,也是极端错误的:福山“历史的终结”的主张(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sis)和利奥塔“宏大叙事的消失”的说法(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grand narra-tives")风靡一时,但几年过去了,还有什么比这些更不吸引人、更不真实的呢?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那些冥顽不化的实用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这些人编造出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或“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之类荒诞不经的虚构。(《知识分子论》P7)我们从赛伊德对福山和亨廷顿等西方学者独树一帜的批评中也不难看出他的观念:既不承认“历史的终结”和“宏大叙事的消失”,也不认可什么“文明的冲突”、“社会的冲突”和建立什么“世界新秩序”。而是认为社会是冲突与交流并存的,世界本身就是多元化的;应该在尊重各个民族习惯的基础上,达到共同存在的局面。而在这个问题上,赛伊德认为首先解决的便是作为西方对东方的压制和殖民及其霸权主义。由此,他对西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对西方社会的严厉批评也给他打上了反西方的烙印。我们暂且不论这种反西方的封条是否属实,不过,虽然现在赛伊德和福山都生活在西方社会代表性的国家美国 ,但是在美国的境域却很不同。就作为东方人为饱受西方蹂躏早已失去话语权利的东方社会言说,反对西方“文化霸权”(?)而言,赛伊德卷牒浩繁的论著证实了他属于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者,和索尔任尼琴一样,被西方人视为生活在西方的“不正常的人”(福柯语)或“他者”,真正的“流亡者”,他在西方并没有找到认同感,归属感;而福山则不同,他的论著证实了他已经成为东方的真正“不正常的人”,也不是真正“流亡者”,在美国找到了归属,被西方人视为“自己人”:福山已经彻头彻尾地融入了西方社会。我们在此暂且不评论他们这种举动的是非功过及其他们的策划是否可以兑现,我们把这个话题留给以后的人来评说。但是,无论未来社会是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也好,还是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的“文明的冲突”也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也好,或者历史的发展有一种出乎预料的结局显现也好(阿伦特?),首先,作为世界有机构成的东方及其诸领域都应该有属于东方的位置与属于东方的发言人,而不是所谓的东方学家代言东方;其次,赛伊德利用福柯的理论指出了西方的东方学家的话语垄断地位及其滥用这个话语权力给东方造成的巨大伤害,从世界多元化和尊重弱势群体权利的意义上来说,赛伊德的贡献是福山无法匹敌的。何况,赛伊德又是一个身体力行且丝毫不避讳既批评西方又批评东方社会的著名知识分子。究于此,我也就无法想象在今天的东方人中还有谁可以与之匹敌。因此,2003年9月24日赛伊德的逝世,不啻对于赛伊德诞生地的巴勒斯坦--东方是一重大损失,对于赛伊德一直持严厉批评态度,需要一个“敌人”做参照物的西方,即便对于日趋多元化的世界也是一大损失。我们将为失去一个为东方阐述的东方人感到万分遗憾和惋惜并不为过。第二“萨伊德1935年11月1日出生于耶路撒冷,在英国占领期间就读巴勒斯坦和埃及开罗的西方学校,接受英国式教育,1950年代赴美国就读一流学府,获普林斯顿大学学士(1957)、哈佛大学硕士(1960)、博士(1964),1963年起任教哥伦比亚大学迄今,讲授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知识分子论》)由于赛伊德出生在民族冲突最为激烈且民族问题最为复杂的耶路撒冷及其美国在1967年阿拉伯与以色列战争期间及其对待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上所持的态度给他造成明显有失公允的印象,并且他作为一名非常有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格外关注伊斯兰及其巴勒斯坦民族解放和西方社会及其以色列之间的民族问题,因而,赛伊德一生的言行及其大部分著作也是贯穿着这两条主线:一条是民族认同问题,另一条主线则是知识分子问题。例如《康拉德与自传小说》(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1966)、《开始:意图与方法》(Beginnings:Intention and Method,1975)、《东方学:西方对于东方的观念》(Orientalism:Westerm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1978)、《巴勒斯坦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1979)、《巴勒斯坦问题与美国语境》(The Palestine Question and American Context,1979)、《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看待世界其他地方》(Couering Islam: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1981)、《世界·文本·批评家》(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1983)、《美国知识分子与中东政治:萨伊德访谈录》(American Intellectuals and Middle East Politics:An Interview with Edward W.Said,1988)《认同·权威·自由:君主与旅人》(Identity,Authority and Freedom:The Potentate and the Traueller,1991)、《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流离失所的政治:巴勒斯坦自决的奋斗,1969--1994》(The Politics fo Dispossession: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Self-Determinatinon,1949-1994.1994)、《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1994)《和平及其不满:中东和平过程中的巴勒斯坦》(Peace and Discontents:Essays on Palestine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1995)等等著作就是赛伊德两种思想的结晶。赛伊德兴趣广泛,还著有音乐批评专著《音乐之阐发》(Musical Elaborations,1991)。
第三目前国际社会知名的知识分子全部都是老年人[譬如,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美国作家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等等],赛伊德也是其中一位颇有知名度的知识分子。这批行将就木的知识分子始终不渝地遵守和发扬着左拉(Emile Zola)在德雷福斯(Dreyfus Affair)案件中《我控诉》(又名《知识分子宣言!》Manifesto of Intelligenty。虽然该文并未出现这个词语)一文所展现的传统知识分子或者公共知识分子精神。不过,这种精神遗产随着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去世逐渐淡薄了,传统的知识分子也成为了“濒危动物”。拉塞尔·贾克比(Russell Jacoby)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版(1987年)的《最后的知识分子:学院时代中的美国文化》(The Last Intellectuals: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一书中虽然描述的对象是美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消失,但是纵览世界,事实证实,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围扩展一下,或者把时间推迟一下,在其他地域也大幅度存在这样的情况,并非美国独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知名的知识分子已为老年人垄断,精神遗产将要失传了。他们这一代成为了“最后的知识分子”:
卡杜辛在研究中收集到了很多有趣的和不那么有趣的资料,包括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的名单。1970年的10名重要的知识分子是:丹尼尔·贝尔、诺曼·乔姆斯基、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欧文·豪、德怀特·麦克唐纳、玛丽·麦卡锡、诺曼·梅勒、罗伯特·西尔弗斯、苏珊·桑塔格,以及并列第十名的莱昂内尔·特里林和埃德蒙·威尔逊。除了桑塔格(1970年她37岁),其他人谁也不年轻。即使知识分子的名单扩充到“前”70名,其中还是没有青年人,这使卡杜辛深感烦恼。应该说,他的研究方法并没有错。《最后的知识分子第一章 消逝的知识分子?》“[名单上]没有青年知识分子,这个事实不是一个‘错误’,它反映出这一时期美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结构,”卡杜辛总结道。青年知识分子只是没有出现在文化生活中,哪怕是某个时期。更有甚者,老朽的“精英”今天并没有退位,他们自20年前以来一直占据着显赫位置。“1970年的美国知识精英,”卡杜辛说,“基本上还是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走红的那批知识分子。”(《最后的知识分子第一章 消逝的知识分子?》)贾克比最后指出:准确地说:在过去的50年里,知识分子的习性、行为方式和语汇都有所改变。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不像过去的知识分子面对公众,现在,他们置身于某些学科领域中--有很好的理由。他们的工作、晋级以及薪水都依赖于专家们的评估,这种依赖对他们谈论的课题和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要产生相当的影响。《最后的知识分子》前言以旺盛的精力和清醒的头脑从事写作的知识分子,在纽约和旧金山可能像低租金的租房一样罕见。在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前,昔日混迹于城市的大街和咖啡屋里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现在他们已经被高科技知识分子、顾问和教授--这些常人所取代了。当然,这些人也许很有能力,他们的能力可能超过那些知识分子,但他们决不能丰富我们的公共生活。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的生活都在校园里,他们直接面对专业同行,而别人既不知道他们,也无法接近他们。这显然是一种隐患,也是一种威胁;今天的公众文化依赖的是正在衰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一种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正在与他们的继承者失之交臂。《最后的知识分子》也许,在重新构建的城市环境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条线索。到20世纪50年代末,不仅城市的居住条件改变了,城市的知识分子和放浪形骸的文化人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最后的波西米亚式的人--垮掉的一代--和最后的城市研究者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意味着一种文化形态正在消逝,而另一种形态正在生成。在高速公路将各个州连成一片的时代,垮掉的一代就是波西米亚人。这一代人过去后,城市的波西米亚群落和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就成了历史,而不是活生生的现实。50年代的城市研究者--简·雅格布斯、珀西瓦尔·古德曼和保罗·古德曼、威廉姆·H·怀特、路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出现危机的时刻奋起作战;他们代表了对有教养的公众负责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第三章 去郊区的路上:城市研究者和垮掉的一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消失是由于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造成的。自从十九世纪初以来科学技术取得丰硕成果以后,人们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生活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人们认为可以理性地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亦即从各种束缚中得到了解放,并不再认为“上帝”存在或者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且彻底构建了人类学意义上的“人”来抵制“上帝”(尼采,海德格尔,福柯有专门论述)。由此,尼采代表世人借助疯子的疯话喊叫出“上帝死了”,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也提出世界的“除魅”(deenchantment)。不过,与此同时,与人们设想和经受的情境不同,这种理性化也是泥沙俱下,既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从高处规范我们行为的理想国受到了质疑和践踏;作为人类的超感性领域的圣殿老化了,剥落速度逐渐加剧并且开始坍塌;人们并没有因为自己认为可以理性地管理自己的生活而从此得到解放,而是被另一个束缚所笼罩,这就是工具理性。马克斯·韦伯不但指出了这种精神的没落,同时也指出了再造这种精神的祸害: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卿卿我我之气有余而巍峨壮美不足,这绝非偶然;同样并非偶然的是,今天,唯有在最小的团体中,在个人之间,才有着一些先知的圣灵(Pneuma)相感通的东西在极微弱地搏动,而在过去,这样的东西曾像燎原烈火一般,燃遍巨大的共同体,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如果我们强不能以为能,试图“发明”一种巍峨壮美的艺术感,那么就像过去20年的许多图画那样,只会产生一些不堪入目的怪物。如果有人希望宣扬没有新的真正先知的宗教,则会出现同样的灵魂怪物,惟其后果更糟。学术界的先知所能创造的,只会是狂热的宗教,而绝对不会是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学术与政治》(Roscher and Knies)P48)这种精神变动是相当剧烈的,即便左拉等人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继承了传统教士的角色,提出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及其捍卫最高价值的观念,虽然在二十世纪中叶知识分子取得了举世盛名,同时也造成了如韦伯所说的灾难性的后果,但好象也只是回光返照,根本无法阻遏工具理性和物质主义的冲击:传统的价值逐渐没落,理想国覆灭了,一切都在重构,虚无主义观念充斥着社会的每个角落。就连对知识分子问题情由独衷的赛伊德也不得不承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俗的知识分子的主要目标有了重大变化,重点从乌托邦主义转入了享乐主义。”(《知识分子》P415)“知识分子猛然离开旧式的乌托邦理论而转向眼花缭乱而又越来越野蛮的享乐主义时,确实有一些可悲的伤亡者。”(《知识分子》P442)实际上,伤亡的何止一些。“上帝死了”即精神家园的丧失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一种灾难。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一文中详细地剖析了尼采所提出的“上帝死了”即理想国覆灭的前因后果:“从本质上看,‘上帝死了’这句话中的‘上帝’这个名称是表示超感性的理想世界的,后者包含着尘世生活的高于这种生活本身的目标,并且从此这般地从高处规定了尘世生活,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是从外部规定了尘世生活。但如果这种纯粹的、由教会规定的信仰烟消云散了,尤其是,如果信仰学说,即神学,在其充当存在者整体的决定性解释的作用方面受到了限制和排挤,这样的话,也还绝不是那种基本结构分崩离析了--根据这种基本结构,一种深入超感性领域的目标设定过程才掌握了感性的尘世生活。“上帝的教会圣职的权威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良知的权威,突兀而起的是理性的权威。反抗这种权威而兴起社会的本能。向着超感性领域的遁世为历史的进步所取代。对宗教文化的维护被那种对文化的创造或对于文明的扩张的热情所代替。创造在以前是圣经的上帝的事情,而现在则成了人类行为的特性。人类行为的创造最终转变为交易。“……我们在形而上学这个名称那里想到的是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结构,是就存在者整体被区分为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并且感性世界总是为超越性世界所包含和规定而言来考虑的。形而上学是这样一个历史空间,在其中命定要发生的事情是:超感性世界,即观念、上帝、道德法则、理性权威、进步、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文化、文明等,必然丧失其构造力量并且成为虚无的。我们把超感性领域的这种本质性崩塌称为超感性领域的腐烂(Verwesung)。(《海德格尔选集》第775页)我在此长篇?倦沟刈?述海德格尔对于尼采“上帝死了”的阐述,不只是图得方便,而是我们从海德格尔的阐释中,可以很清晰并且确切地察觉“上帝死了”的过程及其深刻涵义。海德格尔最后总结道:“上帝死了”这句话包含着以下断言:这种虚无展开自身。‘虚无’在此意味着:一个超感性的、约束性的世界的不在场。虚无主义,‘一切客人中最可怕的客人’,就要到来了。”(《海德格尔选集》第771页)“上帝死了”,或说超感性世界的陨落,按照韦伯的说法便是理性化或者理智化的拓展,按照我们的观念便是理想国坍塌,不但是形而上学的终结,也是最高价值即上帝--“甚至在基督教神学中,人们也把上帝,即作为最高的善的最高存在者(sum-mum ens qua summnm bonum)规定为至高的价值”。(《海德格尔选集》第780页)--的陨落。所造成的后果就是虚无主义的展开,一切被把握为价值,一切从所谓理性为出发点:虚无主义不外乎是这样一种历史,在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价值、价值的确立、价值的废黜、价值的重估,是价值的重新设定。最后而且根本上,是对一切价值设定之原则所作的不同的评价性设定。最高的目的、存在者的根据和原则、理想和超感性领域、上帝和诸神--所有这一切被先行把握为价值了。”(《海德格尔选集》第780页)。自从尼采借助疯子喊叫“上帝死了”和马克斯· 韦伯提出世界“除魅”以后,二十世纪的发展前所未有而出人意料地突飞猛进,一个世纪的成就(无论是在用科技手段屠杀还是建设)甚至超过了几个世纪的总和。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类日渐掌握了各种科学技术,与此相反,精神上(如尼采和韦伯所说)却变本加厉地丧失领地。人们的精神空虚是空前的。这种现象不但在西方如此,即便在今天看来十分落后和保守的伊斯兰世界及其东方同样也受到了强大冲击。与此同时,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关注理想问题,而是与他们所推测的一样发生了重大改变。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很多也不再坚守自己的信念,而是随着世俗社会的改变而改变。社会已经进入多元化的后现代时期以后,那种对理想国向往不但成为众人耻笑的对象,也成为历史的尘垢。“根据后现代的看法,宏大叙事被具有地方特色的情境(local situations)和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所取代:后现代的知识分子看重的是能力(competence),而不是像真理或自由这类的普遍价值。” (爱得华·赛伊德,Edward W Said,《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三联出版社,2002年4月,P22)因此,我们在了解了这段痛心疾首的历史和这个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以后,认为赛伊德这样的知识分子如今成为一种非常珍稀的物种并且随着他们年龄的老化以至灭亡也就不会感到意外了。实际上,传统的知识分子及其精神断了香火也不是一个新奇的话题,而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编年史家哈罗德·斯特恩斯(1891-1943)在他1921年的著作《美国和青年知识分子》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不但法国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认为知识分子“已经不存在”,只是谈论知识分子的人很多(由此说明,知识分子不多了,或者说根本没有了,他们已经成为了一种历史):我觉得“知识分子”这个词很怪。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知识分子。我遇到过写小说的人,治病的人,在经济领域工作的人,创作电子音乐的人。我遇到教书的人,绘画的人,还有我从不知道他们干些什么的人。可就是没有遇到过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我遇到过很多谈论“知识分子”的人。从他们的言论中,我总算对那是个什么东西有点印象了。这并不困难--他是相当人格化的。他对差不多任何事情都怀有负罪感:无论是说话,保持沉默,什么也不做,或者什么都做……简言之,知识分子是判决、课刑、谴责、放逐的原谅。(《权利的眼睛》,P102-103)而且如上所述美国学者拉塞尔·贾克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学院时代中的美国文化》一书中也提出了“知识分子的消失”:那种纯粹为“波西米亚精神”而生存的知识分子已经式微了。虽然在贾克比之前几年(?)美国学者艾尔文·古德纳(Alvin Gouldner)在《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New Class)一书中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改变了面貌,成为一种新兴阶级,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发挥着作用:20世纪,在所有成为正在形成的世界社会经济秩序组成部分的国家中,一个由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这两者并不相同)组成的新阶级,开始了与原先控制着社会经济领域的集团的竞争,这些集团由商人或政党领袖组成。无论是在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第三世界,由苏联及其卫星国构成的第二世界,还是由北美、西欧和日本这些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第一世界,一种新的阶级斗争和新的阶级系统正在慢慢地形成(《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P1)。马克斯· 韦伯认为: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也可以是“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这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当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同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这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对立。(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学术与政治》(Roscher and Knies)P107)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公共或传统知识分子,作为为学术或思想而生存的知识分子(在此我们引申一下)遵循“信念伦理”,而为政治而生存的知识分子遵循“责任伦理”,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新阶级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具有“理念人”的角色,这也就是作为新阶级的知识分子不再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根本原因。他们已经不再是福柯所称谓的“普遍的知识分子”,而是“特殊的知识分子”,被世俗或者其他利益集团收编。也就是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为“信念伦理”生存的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少,并且有消失的迹象。实际上,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的一点也就是这种遵循“信念伦理”的精神,而且其他学者也在重申这种精神,这已经成为知识分子具有代表性的精神。很多学者也是根据这一点来批判到底是不是知识分子的: 此外,俄语中“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这个术语,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有了,后来渐渐地传人了英语,或至少成为英语中“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这个词意义的一部分,深化了其反派的色彩。为俄国革命铺路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界定为“与政府疏离并和政府敌对”。这一段历史给随后的一些讨论增添了色彩。一些思想家想越过这一段过去的历史;其他的则想重申这段历史。当H·斯图尔特·休斯展望知识分子的未来的时候,他也回顾了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的历史。(也许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纵观了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然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则有所不同,它把原先的许多色彩消褪了。有关知识分子的讨论没有停止,但说法却变味了。过去人们曾把知识分子说成是批判者和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现在却把知识分子当作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阶层来谈论了。说法的变化表明了生活的转变。当然,这个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重新陈述这个问题却揭示了生活的重构。知识分子越来越不作为独立的作家或诗人而生活了,他们更多的是作为专业集团、利益联盟,或许是一些阶级而存在。对于一些像艾尔文·古德纳这样的人来说,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的“新阶级”组成了“现代社会最进步的力量”。欧文·克里斯托尔却不同意这个观点;新阶级是一个“雄心勃勃而又遭受挫折的阶级”。《华尔街杂志》的一个编辑发现--或是产生了这样的幻觉--“由商业帝国创建的许多巨大财富现在都已经被知识分子占有了,而且,正被用来……攻击商业并提升这个新阶级”。《最后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采用了这种以为精神而生存为批判是否为知识分子的标准,那么传统或者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江河日下,他们所创造的精神河流逐渐干涸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残酷现状。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领域只剩下耄耋的学者在支撑着场面,后继乏人也成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不过,虽然后现代主义时期已经不再关注柏拉图主义,知识分子也成为一种边缘话题,只剩下他们几位老者支撑着,但是他们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却没有心灰意懒,而是一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赛伊德就是其中一位意图重新树立知识分子信念的言说者和实施者。因此,赛伊德是反对利奥塔所谓的“宏大叙事消失”和贾克比“最后的知识分子”的论断的。他在《知识分子论》中阐述道:在里根政府即将届满时,一位名叫贾克比(Russell Jacoby)的不满现状的美国左翼知识分子出版了一本书,激起了很多的讨论,其中多为赞同之词。此书书名为《最后的知识分子》,主张是下述无懈可击的论点:在美国“非学院的知识分子”(the non-academic intellectual)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群怯懦、满口术语的大学教授,而社会上没有人很重视这些人的意见。贾克比心目中往昔知识分子的典型本世纪早期大都居住在格林威治村(相当于法国巴黎的拉丁区),通称为纽约知识分子。这些人大都是犹太裔、左翼(但大都反共),以笔耕为生。……根据贾克比的说法,类似的人物已经被各种各样战后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消除殆尽:逃向郊区(贾克比的论点为知识分子是都市的生物);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不负责任,率先提出退出及逃避人生中的指定岗位的观念;大学的扩张;以往的美国独立左派逐步流入校园。《知识分子论》P62、63贾克比再三回到他对于知识分子的观念:“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他说类似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沉默寡言、无法了解的课堂内的技术人员。这些人有委员会雇用,急于取悦各式各样的赞助者和部门,披挂着学术证件和社会权威,然而这种社会权威并未促成辩论,只是建立声誉和吓唬外行人。这是个很悲惨的景象,但正确吗?有关知识分子消失的原因,贾克比的说法正确吗?我们能不能提供更正确的诊断?赛伊德就贾克比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首先,我认为责难大学,甚至责难美国,是错误的。此外,身为知识分子未必就与学院认识或钢琴家的身份不一致。至于说美国特别使知识分子的生活变质,这种指责也有争议,因为今天举目四望,即使在法国都不再是波西米亚人或咖啡馆里的哲学家,而已经成为另一种很不同的人物,代表着许多不同种类的关怀,以很不同、剧变的方式来代表。P64赛伊德认为知识分子改变了面目在其他职位上发挥着传统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过他并没有说今天的知识分子究竟是否已经不如以前了,实际上他是在故意回避这个问题。赛伊德指出对知识分子的威胁原因并不高明,实际上我们与其将他的观念认为是原因,还不如说结果更恰当。他认为: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特别的威胁,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都不是来自学院、郊区,也不是新闻业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而是我所称的专业态度(Professionalism,也可译作职业态度)。我所说的“专业”意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P65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威胁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这些压力中的第一个是专门化(specialization)。2,专业知识和崇拜合格专家的作法则是战后世界中更特殊的压力。3,专业态度的第三个压力就是其追随者无可避免地流向权力和权威,流向权力的要求和特权,流向被权力雇用。4,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担忧极权政府体系对于思想和知识自由的钳制,但在考虑奖赏知识的一直顺从、奖赏乐于参与政府(而不是科学)所建立的目标的这种体系对于个体知识分子的威胁时,却未能同样挑剔,研究和水准鉴定相应地遭到控制,以便获得并维持较大的市场占有率。赛伊德认为,为了对抗“专业化”可以采用当然“业余性”来解决。当然,以所谓“业余性”抵制“专业化”的观点也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无非重申了德雷福斯案件中的知识分子精神:“无论持何种主张的知识分子都明确或不明确地要求他介入的权利,并常常,用他们的话说,表示愿意承担他们的义务,而且还为他们影响的能力进行辩护。”《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P8尽管这些压力普遍可见,但都可以用我所谓的业余性(amateurism)来对抗。而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饿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P67
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认为身为社会中思想和关切的一员,有权对于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因为这个行动设计他或她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国家与其公民和其他社会互动的模式。此外,身为业余者的知识分子精神可以进入并转换我们大多数人所经历的仅仅为专业的例行作法,使其活泼、激进得多;不再做被认为是该做的事情,而是能问为什么做这件事,谁从中获利,这件事如何能重新连接上个人的计划和原创性的思想。P71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可以说是赛伊德继承并发扬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不过是精神决定论的产物。而忽视了工具理性的冲击力。他所阐述的知识分子涵义和遵循的原则,也是与德雷福斯案件传统的认识一样。赛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首先叙述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所认定的知识分子的含义:按照在社会中的作用可以分为传统的知识分子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与有机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然后叙述了班达在《知识分子之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一书中的观念:“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潮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P12)最后赛伊德综述了一下他们的观点,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应该是这样的:根据我的定义,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共场合这么说。(P25)如果我们留意他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和他在其他文章的阐述及其自己的行动,他这种思想的形成与他的巴勒斯坦的身份有必然的联系,不过他所定义的知识分子含义,并不是如我们想像的那么狭隘,而是有所超越。无论是对民族国家问题还是知识分子的消失,他都是保持着一种乐观和宽容。而这种乐观和宽容对于我们也是非常需要的。他在《知识分子论》中所阐述的知识分子的角色,也代表着这种思想。第四“生活在别处”是法国著名诗人兰波的一句名言,被捷克流亡作家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采用,做了一部书的名字。昆德拉属于离开了熟悉的故土捷克的流亡者,也就是所谓“生活在别处”的人。就离开故乡而言,赛伊德也是,福山也是,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也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也是,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也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马克思(K.Marx)也是,奥地利作家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 )也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Freud)也是,英国作家奈保尔 (V. S. Naipaul)也是,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也是,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是,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 . Brzezinski)也是,美国纳博科夫(Vladmir Nabokov)也是,犹太人也是,很多巴勒斯坦人也是流亡者。历史上由于战争、疾病、民族问题等等原因很多背井离乡的也是流亡者。作为流亡者或者流亡者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命运很悲惨,他们的命运一般是与灾难,受到惩罚被逼迫而离开故土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与故土产生了距离,与新居产生了陌生感:流亡者存在于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伤感,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精于生存之到成为必要的措施,但其危险却在过于安逸,因而要一直防范过于安逸这种威胁。P45不过,虽然流亡者在肉体或/和精神上遭受了一定的打击,但是他们也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好象应了孟子的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那么为什么知识分子流亡者能取得那么骄人的成就呢?赛伊德认为作为流亡者起码有以下几种好处促成了知识分子功成名就:因为流亡者同时以抛在背后的事物以及此时此地的实况这两种方式来看事情,所以有着双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情。知识分子的立足点第二个有利之处,就是比较能不只看事物的现状,而能看出前因。视情境为因偶发的机缘而生成的(contingent),而不是不可避免的;视情境为人们一连串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人类造成的社会现实,而不是自然的或神赋的(因而是不能改变的、永恒的、不可逆转的)。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流离失所意味着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在寻常职业生涯中,“干得不错”(doing well)和跟随传统的步伐是主要的里程碑。流亡意味着将永远成为边缘人,而身为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必须是自创的,因为不能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对于受到迁就适应、唯唯诺诺、安然定居的奖赏所诱惑甚至围困、压制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是一种模式。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但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像、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事物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边缘的状况也许看起来不负责或轻率,却能使人解放出来,不再小心翼翼行事,害怕搅乱计划,担心使同一集团的成员不悦。当然,没有人能摆脱牵绊和情感,而且我在这里所想的也不是所谓的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free-floating intellectual),其技术能力完全待价而沽。相反,我说的是:知识分子若要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不被驯化,就得要有不同于寻常的回应:回应的对象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是暂时的、有风险的事,而不是习以为常的事;是创新、实验,而不是以威权方式所赋予的现状。流亡的知识分子(exilic intellectual)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P57赛伊德认为流亡者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对比的偶像,而作为流亡者在这种对比中,所采取的态度是平衡的,不存在偏移: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而这种觉知--借用音乐的术语来说--是对位的(contrapuntal)……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对位的;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P1)
赛伊德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说明了流亡者身份的特殊性:我是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个美国人,这所赋予我的双重角度即使称不上诡异,但至少是古怪的。此外,我当然是个学院人士。这些身份中没有一个是隔绝的;每一个身份都影响、作用于其他身份。……因此,我必须协调暗含于我自己生平中的各种张力和矛盾。P3一方面你争取代表自己的权利,要有自己的民族性;但另一方面,除非这些是连接上更宽广的实践(也就是我所谓的解放),否则我是完全反对的。P3赛伊德将流亡的含义扩大化,将那些不在权力中心的人士视为流亡者:流亡既是个真实的情境,就我的目标而言也是个隐喻的情境。……甚至一辈子完全是一个社会成员的知识分子都能分为所谓的圈内人(insiders)和圈外人(outsiders):一边是完全属于那个社会的人,在其中飞黄腾达,而没有感受到强烈的不合或异议,这些人可称为诺诺之人(yea-sayers);另一边则是谔谔之人(nay-sayers),这些个人与社会不合,因此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把知识分子设定为圈外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况加以解说--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倾向于避免、甚至厌恶适应和民族利益的虚饰。对这个隐喻意义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跑,一直未能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来,无法回到某个更早、也许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而且,可悲的是,永远无法完全抵达,永远无法与新家或新情境合而为一。P48这种情况就造成了所谓的无家可归的感觉,一方面自己的故乡回去很难,一方面在新居住地有一种生疏感,不过这样一种身份也打破了限制,也就是促进了融合,站在更高的角度上看世界。而这个位置是属于自己独有的:缪塞几乎在两个世纪前,就已经指出,“伟大的艺术家是没有国界的”。在两个世纪前,这些话是富于战斗性的话,是战斗口号之类的话,是在易受骗的、未成熟的并因而也是傲慢自大、威猛好斗的爱国主义的震耳欲聋的鼓吹中写下的。大量的政治家,在“一个法制,一种语言,一个世界观,一个历史和一个未来”的民族国家的建设中,展示着他们的使命。许多诗人和画家,正在为培育和滋养精神的新芽,为复兴长期死亡了的民族传统,或为构想出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全新的民族传统,提供它的英雄的先辈们的故事、画像、颂歌和英名(这是一些整个民族共同享有、爱护、珍惜的东西,并因而是一些能将共同生活提升到共同归属的层次的东西),并通过推动活着的人们去牢记和景仰他们的先烈,并让他们对保卫先烈们的遗产而感到荣耀和自豪,来为增强活着的人们对这一归属的美好和幸福的认识,而履行着他们的职责。在这一背景下缪塞直言不讳地断言,具有所有战斗和反抗口号的特点:这句话召唤着他的作家伙伴们,拒绝与政治家,与鼓吹边界要严密守卫、战壕要刀枪林立的宣扬者的雄心勃勃的事业进行合作。我不知道缪塞是否凭直觉,发现了这种民族主义政治家和杰出的思想家决定要建立的博爱的自相残杀的能力,或者说,我不知道,他说的话是否只是对狭隘范围、落后状态和偏狭心态的心理反感和厌恶情绪的一种表达。然而我们现在读起来,无论当时是哪种情况,由于有了事后的认识优势,由于把它放在放大镜下,我们发现它沾上了种族清洗、灭绝、屠杀和累累坟茔的污点。缪塞的话,看来既没有丝毫失去它的主题性,挑战性和紧迫性,也没有丝毫失去它最初的争论性。现在和当时一样,他的话,目标指向作家天职这一核心,并用这一对任何作界的存在理由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来对他们的道德良心提出挑战。(P319)在他与卡瑟琳·马拉波(Catherine Malabou)合作出版的《林荫小道》(Contre-allée)一书中,雅克·德里达(Jacpues Derrida)要求他的读者在旅途中去思考(to think travel),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去“思考旅途”(think travel)。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去思考那个向着未知之地而离开自己的家的远去的行动,但是又必需承受这个“未知之地”等待这你去承受的所有的风险、快乐和危险(甚至是一去无回的危险)。(P321)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讲,德里达保持着一种“无国家”的状态。然而,这并不是说他没有文化上的祖国。恰恰相反:“文化意义上的无国家”意味着他不止有一个国家,在两种文化之间的十字路口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德里达变成了并依然是一个外国佬(métèque),一个文化混血儿。(P322)在文化的交汇地上建立一个自己的领地,证明是它们--来让语言检测它在别的地方很少交流的东西,来洞察它的其他未被注意到的特性,来发现语言能做什么,以及发现是什么东西可能使得语言永远不能表达和传递内容--最能想象得到的需要所在。正如克雷斯蒂安(Christian Delacampagne,Le Monde of 12 March 1999)指出的,正是从这一建立在文化交叉口上的家园,德里达才产生出了这些激动人心、开阔视野的见解--它们是,关于含义的固有的多元性和不可决定性的见解(在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一书中),关于来源的不纯性的见解(在De la grammatologie一书中),关于交流沟通永恒的不可实现性的见解(在La Carte postale一书中)。P323葛蒂索罗和德里达的中心观点与缪塞的中心观点不同:这位小说家和那位哲学家一致表明伟大的艺术没有祖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艺术,和艺术家一样,可能会有很多祖国,而且可以肯定地或很多人还不止一个祖国。恰恰不是无家可归,只是他要掌握在许多国家他都要熟悉这个国家的情况的诀窍;掌握在每一个国家,他同时既要是局内人又要是局外人的诀窍;要把熟悉和密切与一个外来人批判的目光结合起来,把参与、卷入和超然独立结合起来的诀窍--这是一种定栖人口不可能学到的窍门。学会这一技巧是流亡生活意想不到的事:按字面意义来严格解释,一个流亡者,是指一个在某地生活(in)可是又不属于(of)那个地方的人。由这一状况(即就是这一状况)所致的不受束缚,表明这个如在家一般的感觉,是人为的和未完成的,并表明,母语是一个几代人,和总是比他们的任何读物都要更为丰富、永远期待着的再一次被取出的经验宝库之间的,永无休止的信息流。(323)
第五
当理性没有完全醒过来的时候或是再次入睡,差别就产生了:这是没有公开的信条。它使后启蒙(Post-Enlightement)自由主义者对人们追求完美无缺思想的个体能力的明确信任,具有可信性。我们,这些人,被认为具有任何人在选择正确道路时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而一旦对道路作出了正确选择,这对我们所有的人而言,证明都是相同的道路。笛卡儿的主体(subject)和康德的人(Man),由于有了理性的武装,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不会犯错误,除非他们因为被诱惑或被推开而偏离了理性开辟的笔者的道路。不同的选择,是由历史大错沉积而成的--是叫作偏见、迷信和错觉的脑损伤的结果。不像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理性的简明一义的(eindeutig)判断,判断上的差别有着集中的渊源,培根的“幻象”(idols)存在于人们一起乱转和搅扰的地方:存在于剧场中,市场和部族的庆祝活动中。释放人类理性的力量,就意味着从所有的那些东西中解放出来。(P261)
如果依照鲍曼所指出的,那么理性对于我们的确是一件非常难得的礼物,但是又是随时给予我们的礼物。毕竟我们的表现不是整齐划一,也不是对事物有一种统一的认识。但在某点上我们还可以达到共识。就像现在我们评价赛伊德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而这种见解同样也是充满着偏见和错误,当然也有一定的理性羼杂着。即便对于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涵义有不同的解释,对他们的责任也有着不同的见解,我们在这个问题是也是无法统一的。这种缺乏理性的认识也就是导致我们差别的根本原因。但是,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为理念而生存,他们的行为是超越民族国家这个界限,并且是为这些理念而生存的,这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是理性的,也就是没有差别的,有一个共识。这种认识同样也存在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问题上。在此,我们暂且抛开从德雷福斯案件中所呈现的超越民族界限,单纯为了捍卫一种崇高的价值不谈,我们看看赛伊德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是否与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的认识存在差别,也就是是否失去了理性的灯塔的指引。首先我们先梳理一下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民族认同或者说民族共同体)这几个概念。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详细地厘清了这个问题:人们认识到,在近来的共产主义兴起之前,在现代民族建设(nation-buiding)丑陋多刺的外表内,有着一个值得珍视的东西,伊赛·伯林(Isaiah Berlin)认为,除了它残酷的和可能的血迹斑斑的方面外,现代的“祖国”还有着它人道的值得赞扬的方面。相当普遍的是,在爱国主义(Patriotsm)和民族主义(nationlism)之间作出的区别。通常情况下多半是,爱国主义是这一对对立物中的一个“标志性的、引人注目”要素,而民族主义令人讨厌的现实,却被当成是“非标志性的”要素:爱国主义--与其说是经验性的不如说是假定的--是民族主义(如果加以驾驭、教化和在道德地位上加以提升的话)可以但又不是的事物。爱国主义是通过否定民族主义者观点(nationlistalism)中最不令人喜欢和最不体面的特点来加以描述的。考拉考茨基认为,民族主义者想要通过敌对行为和对其他人的仇恨而假定部族的存在,并相信他自己民族所有的灾难都是外国人侵略的结果,并因其他民族没有恰当地尊重它却很好地对待本民族,而对所有其他的民族抱有深刻的仇恨,在这个时候,爱国主义者因“对文化多样性尤其是对种族的和宗教的少数派的宽宏大量的容忍”而显得引人注目,就像它愿意并准备告诉它自己的人民一些并不中听的事情一样。尽管这种不同是好的,并且在道义和认识上值得赞美,然而它的价值和意义,多少被这一事实所削弱:这里相互对立的,与其说是两种有可能被接受的选择的对立,还不如说是崇高的思想和不光彩的现实之间的对立。大多数希望他们被指定的同道成为爱国者的人,极有可能会强烈谴责认为体现了爱国主义立场的那些东西,例如证明是两面三刀、出卖国家或是情况更糟的那些东西。那些特别吸引人的东西--对差异的容忍,对少数派的友好和接受,以及说明真相的勇气,无论它们是多么地令人不快,--在“爱国主义”不是“问题”的土地上,在共和国公民身份足够牢固,不用担心爱国主义已是问题,更不用说认为它是一个紧迫任务的社会,都相当普遍。当《没有幻想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without Illusions,University of Press,1966)一书的编者纳德·雅克(Bernard Yack),在他批评《对国家的爱:论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For Love of Country:An Essay on Patriotism and Nationlism,Oxford Uninersity Press,1995)一书的作者维罗利(Maurizio Viroli)的一篇文章中,用自己创造的一句格言来诠释霍布斯的思想时,这并非不恰当。他的这句格言是,“民族主义是不讨人喜欢的爱国主义,而爱国主义却是讨人喜欢的民族主义。”确实,我们很有理由这么认为,除了这些东西--我们对在承认或否认它们时所表现的形式,或是这一表现形式的不存在,或是此时面有愧色的程度,或此时良心的谴责所怀有的兴趣和热情--之外,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很少有其他的什么区别和不同。是他们的名字导致了这种差别,而且这种被造成的差别基本上是修辞上的差别,与没谈论的现象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区别,而只是与我们在谈到的其他方面基本相似的强烈情感时的方式,有所区分而已。然而,正是这种情感和它们行为上的后果与政治后果的实质,而非没用来叙述解说它们的语言,才是至关重要的,并影响这人们共同相处的性质。在回顾了爱国主义历史所讲述的英勇事迹之后,雅克得出结论认为,无论崇高的爱国情感是在什么时候“发展到共同情感的层次”,“它都是爱国主义者展现出来的强烈的而非温和的情感”,而且爱国者能够超越几个世纪地表现出“令人难以忘怀的、值得赞扬的高尚品德,而在他们的品德中,对外人的温和同情和支持,并不突出”。尽管如此,对言语修辞上的差别的意义,和它偶尔产生的强烈的实际反响,我们并没有丝毫的否认,一个词被创造出来是用衡量“存在”(being)的问题,另一个词却是用来衡量“生成、转化”(becoming)的问题。总的来说,“爱国主义”是要赞扬人们的“不结束性”(unfinishedness)和易适性(更为准确地说,是“可塑性”[reformability])的现代信条:因此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宣称(无论这种可能性在实践中是否得到保持),“紧密团结、携手合作”的号召是一个开放性的长期有效的号召:加入这一队伍,就是一个既定选择的事情,而且他所要求的只是,作出正确选择并在此后的任何情况下都对它保持忠诚。相反,“民族主义”倒更像是加尔文主义的救赎观或是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自由意志思想:它几乎不怎么信任选择--你要么是我们中的一元,要么不是,而且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要改变它,你很少能做点什么,或许是根本无能为力。在民族主义者的叙事中,“归属”(belonging)是一个命中注定的事情,而不是一个被选择是命运或是一个生活计划。它可能是一件生物遗传的事情,就像现在民族主义中或文化传统中流行的“文化主义”的变体一样--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在这个或另一个人在开始走路或说话之前,这个东西都早已决定好了,因此,留给个体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要么是张开双臂真诚地欣然接受命运的安排,要么是起来反抗这一命运的安排,并因而成为某人召唤的背叛者。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这种区别,超越了仅仅是修辞上的差别,并成为政治实践领域里的一个问题。根据列维·斯特劳斯(Caude Lévi-Strauss)的术语学,我们可以这样说,第一种方法更有可能激发起“吞噬策略”(把陌生人“吞没掉”,从而失去它们自身的特殊性、差异性),而第二种方法通常与“把不适于成为我们”的人“吐出来”的“禁绝策略”结合在一起,要么通过把他们禁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有形界线内,或禁闭在文化禁令的无形界线内,要么通过把他们赶到一起,放逐他们或是强迫他们离开,就像当今在种族清洗和净化的名义下所做的那样,从而把他们隔离起来。然而,思想逻辑很少和事迹逻辑结合在一起,因而在言词和实践之间,没有任何一对一的关系,而且这两种策略中的每一种策略,都可能与两种修辞的其中一种缠绕在一起。记住了这一点,就算是深谋远虑。(《流动的现代性》P274)通过鲍曼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剖析,虽然它们在运作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分别是“吞噬策略”和“禁绝策略”,不过他们最后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无法分割的,或者也可以说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联系为一体的。鲍曼在这段文章中还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也就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人为构成的,并不是一种天然的联系,而是在现代才产生的。但这里也有一种难以摆脱的联系,那就是有些自然的,我们生活于这个人为构造的民族国家里,这是我们无法选择的。赛伊德在他的文章中多次使用了福柯《知识考古学》和《临床医学的诞生》、《性经验史》等等所展现的事物是人为构造的等等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不过,我们现在提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或者民族认同问题,这里也有一个很根本原因,也就是这个共同体可以给我们提供安全的保障。但是这个共同体也是构造而成的。“为了存续下去,它们需要得到保护,它们也需要求助于它们自己的成员,通过个体的选择来确保生存,并为这一生存承担个体的责任。在这一意义上,所有的共同体都是假定的(postulated);是在个体选择之后而非选择之前,是计划的东西而非现实的东西,在实现产生。”(P263)鲍曼认为民族主义或民族共同体被我们屡试不爽,由于这种原因制造的:首先,“种族源源”(ethnicity)与人类联合体的任何其他的基础都不同,有着“吸收历史”(naturalizing history)的有利条件。有着把文化历史表现为“一个特定身份的事实”、把自由表现为“被理解的(和被接受的)需要”的有利条件。其次,把民族团结的原则置于其他所有忠诚之上的民族国家,是现代时代共同体唯一的“成功历史”,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使得追求共同体地位的努力,具有某种程度的说服力和效果的唯一存在的实体。P269虽然我们知道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民族认同这些东西是虚构的,但是不可否认这样一种真实,我们每个人从出生都带着族裔的血脉、烙印,这是难以摆脱的根本,难以抹杀的历史沉淀,我们一般对自己的民族国家也维系一种本能的亲近感,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观念。不过,我们从这种构造中也应该认识到,民族认同或民族主义问题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理性地看待问题的重要标准,同样也是衡量知识分子是否理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准绳,当然也是衡量是否为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标准。那么作为一个比较知名的知识分子,赛伊德的表现是否很理想或者说很理性呢?我们知道,贯穿赛伊德一生的言行,并且与作为流亡者身份的知识分子密切相关的另一个主题是民族认同问题。这方面主要显示巴勒斯坦民族和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问题上。民族问题主要保存在他的著作中东研究的三部曲,即《东方学》和《巴勒斯坦问题》及其《报道伊斯兰》之中。影响比较大,同时也是在国际社会引起反响和争议比较大的作品是《东方学》。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他也探讨了民族问题。这方面保存在该书的第二章。赛伊德对共同体的认识是具有前瞻性,并且是符合理性的标准的。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所阐述的思想就是这样的他首先批评了知识分子在民族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他指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但要保持自己批评/批判的权威,而且要同各种狭隘的观念争斗领地,赛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批评知识分子的失职:当今知识分子处境之难处在于他们已经把自己的道德权威让给了他所谓的“集体激情的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collective passions”)。这是个先见之明的词汇,其内容包括了宗派观念、群众情绪、民族主义的好勇斗狠、阶级利益等。(P13)赛伊德不但批评了知识分子在民族问题上的丧失了主动性,在此同时,而且指出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在民族问题上应该着眼于世界,着眼于未来,“我们需要从目的社会(telocratic society)走向波柏尔(K.Popper)所说的开放社会(open society)”,不应该因为民族的原因而降低自己的批评力度或者不予批评。“班达的名著《知识分子之背叛》给人的印象是:知识分子存在于一种普遍性的空间,既不受限于民族的疆界,也不受限于族裔的认同。”(28)这点与苏联--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1994年从美国回到以后,在车臣问题上的言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赛伊德认为知识分子的批评应该摆脱民族或种族观念束缚,并不针对某一部族、国家、个体,而应该针对全体人类,将人类作为表述对象。即便表述本民族或者国家、个体的灾难,也必须和人类的苦难联系起来,和每个人的苦难联系起来表述。“若要维护基本的人类正义,对象就必须是每个人,而不只是选择性地适用于自己这一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国家认可的人。”(《知识分子论》P80)“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 (《知识分子论》P41)实质上,如果知识分子坚持了这种原则不但避免了知识分子批评过程中的偏激,也可以从人类的角度看待民族、国家冲突与个人灾难的构成的关系。这样也可以称为理性的观点。赛伊德认为:“像印度的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或古巴的马蒂(Jose Marti,1853--1895)那样伟大的知识分子都是典范,虽然他们一直是民族主义者,但绝不因为民族主义而减低他们的批评。”(《知识分子论》P39)但是赛伊德并非民族虚无者,在民族认同问题上做无原则性的妥协。他认为现在提到民族主义还是非常人道的,也就是可以捍卫自己尊严。他在批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世界泛政治化教育的同时,也在寻求作为东方人应该为东方发言:“知识分子应该使用一个民族的语言,不只是为了方便、熟悉这些明显的理由,也是因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希望赋予那种语言一种特殊的声音、特别的腔调、一己的看法。”(《知识分子论》P29)而不能够像马克思所说的“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被西方的东方学家及其东方学而替代或者抹杀。在此同时,他也批判了西方社会的武断指责,他说:“但是在这些讨论出现在美国主宰的西方联盟所提供的后冷战(Post-Cold War context)中,而且当中已经出现一种共识:复苏的或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取代了共产主义,成为新的威胁。这里,集体的思考并未使得知识分子成为我所描述的质疑和存疑的个人心灵(这些个人代表的不是共识,而是以理性、道德和政治的立场,遑论方法论的立场,来怀疑这种共识),而是使得知识分子异口同声回应盛行的政策观点,加速使其成为更集体的思考、愈来愈不理性的说法:“我们”遭到“他们”威胁。结果是不容忍和恐惧,而不是知识和共同体。”(32)他同时也指责了西方社会对伊斯兰世界的简单勾画和绝对化,或者说对伊斯兰世界的妖魔化,而不顾历史事实,忽视伊斯兰世界世界的负责性和多元化特征。“今天在与伊斯兰世界打交道时情况正是如此。伊斯兰世界有十亿人,数十种不同的社会,六七种主要的语言(包括阿拉伯文、土耳其文、伊朗文),这些都散播到三分之一个地球上--但是英美的学院知识分子却只把它们称作“伊斯兰”,这种说法不但太过化约,而且在我看来不负责任。他们借着单单一个字眼似乎就把伊斯兰当成一个简单的客体,对于上下1500年的伊斯兰历史提出概括的看法,大谈伊斯兰教与民主、伊斯兰教与进步是否相容,并妄加论断。”(32)他对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批评进行的反批评保留在《东方学》一书中。他在本书中对东方学者及其东方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以至被很多西方学者称为反西方,被很多东方人称为民族主义的说客。代表了东方人的利益。赛伊德认为:民族认同策略是我在《东方主义》(又译作《东方学》)一书及我的新著中所分析的帝国主义文化事业的核心。其基本观点在于,承认并笃信东方人和非洲人与欧洲人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譬如,一位法国或德国学者试图分析中国人的主要心智特征时,他往往只用部分精力讨论这个题目,他真正着力说明的实质上是中国人与西方人思维有天壤之别。所谓中国思维或希腊精神此类令人难以捉摸的人为建构的东西由来已久,我们对它并不陌生;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形成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传统和不同民族的源头所在。但唯独到现代社会,它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而在此之前的任何历史时期,民族性这个问题都没有引起人们如此之大的兴趣。诚然,那时整个世界还没有变得像今天这样狭小,社会尚无定形,全球化规模也未达到现在的程度。今天,民族认同策略所获得的重视,令人叹为观止。推本溯源,这主要起因于帝国主义的经验。18世纪末,现代帝国主义扩张在全世界范围发生,殖民主义开始强调法国人或英国人与殖民地人之间的差异。正是这种极具对立性的民族差异造成了在同一国度中作为某个相同种族成员的人民与排斥他们的国家之间的分裂。这一点,过去是,今天仍然也是我们认识帝国主义的特征之一。究其要害,无非是那个冥顽不化的论点,即每个人都不可改变地成为某一种族或族类的成员,并且,除了作为自体存在外,该种族或族类则永无可能被他族同化或接受。所谓东方性、英国性、法国性及非洲性,还有美国特性等便由此杜撰而来,好像每个说法的背后都存在着一条恒古不变的柏拉图式的真知灼见。 民族主义就是该教条的产物之一。(《认知的策略》)《东方学》代表了他的这种思想,在他的观念中,东方学就是西方认为构造的,并没有一个实际的对象: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其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甚至殖民体制和殖民风格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基础。(P2)东方学有三种含义:1,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的含义;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在大部分时间里,“the Orient"(东方)是与“the Occi-dent"(西方)相对而言的,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即以两者之间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P4东方学的含义一直摇摆于其学术含义与上述或多或少出自想象的含义两者之间,18世纪晚期以来,这两种含义之间存在着明显、小心翼翼的--也许甚至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交合。接下来我要谈的是东方学的第三个含义,与前面两个含义相比,这一含义更多地是从历史的和物质的角度进行界定的。如果将18世纪晚期作为对其进行粗略界定的出发点,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我发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和《规约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chment)中所描述的话语(discourse)观念对我们确认东方学的身份很有用。我的意思是,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体系的学科,而在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时期,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像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P4因此,东方学不只是一个在文化、学术或研究机构中所被动反映出来的政治性或领域;不是有关东方的文本的庞杂集合;不是对某些试图颠覆“东方”世界的邪恶的“西方”帝国主义阴谋的表达和表述。它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它不尽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世界由东方和西方两大不平等的部分组成),而且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谋划--它通过学术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或社会描述将这些利益体系创造出来,并且使其得以维持下去;它本身就是,而不是表达了对一个与自己显然不同的(或新异的、替代性的)世界进行理解--在某种情况下是控制、操纵、甚至吞并--的愿望或意图;最首要的,它是一种话语,这一话语与粗俗的政治权利决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是在与不同形式的权力进行不均衡交换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并且存在于这一交换过程之中,其发展与演变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制于其与政治权力(比如殖民机构或帝国政府机构)、学术权力(比如比较语言学、比较解剖学或任何形式的现代政治学这类起支配作用的学科)、文化权力(比如处于正统和经典地位的趣味、文本和价值)、道德权力(比如“我们”做什么和“他们”不能做什么或不能像“我们”一样地理解这类观念)之间的交换。实际上,我的意识是说,东方学本身就是--而不只是表达了--现代政治/学术文化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与其说它与东方有关,还不如说与“我们”的世界有关。P16不过赛伊德所讲的这些知识分子批评前提,虽然他在冒着生命危险批评阿拉伯世界时表现得相当不错,但在种族主义即东西方问题上,他却并未做到客观公正,亦即未能遵守这种原则。这也引起了学术界不少非议。受到了很多批评和驳斥。乔治·E·马尔库斯和米开尔·M·J·费彻尔批评道:爱得华·赛伊德(Edwrd Said)在他的《东方学》(1979)这部著作中,大刀阔斧、不加区分地攻击了西方在表述非西方社会时所发展出的写作风格,只在某一点上,简略提及人类学大师之一克里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似乎对他有某种好评,也把当代文化人类学列于他的抨击名单之外。但在提到人类学时,他虽含糊其词,但却清楚地表现出有意将谴责和批评应用于所有的西方人(包括人类学家)对于异文化的描述之上。他特别地攻击使西方作者处于主动地位、使他们描述的对象处于被动地位的修辞学手段。据他的看法,作为被描述的对象,非西方人的心声和愿望通常是被置于由西方殖民主义者或新殖民主义所统治的世界来看待的。这样一来,修辞学的手法不仅成为西方人统治的一个范例,而且成为加强西方人对非西方人的统治和支配的手段。甚至,修辞学的手段本身也是一种权力的运用和发挥,它通过否认与作者不同观点的同等有效性来剥夺主体表达对立观点的权力。潜隐于这种修辞学手段之中的,是对当代阿拉伯人、希腊人、埃及人或玛雅人的贬低。这种贬低是将他们与古代祖先进行比较联系而进行的。在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全盛时期,东方的历史被宣称是古希腊、法老时代的埃及、或“古典时代”伊斯兰的衰落与式微过程。直到今天,东方学研究,在否认这些光辉遗产对当代文化所具有的内在价值的同时,还过多地强调这些遗产乃是衰微和崩溃的古代文明的残余。用19世纪英、法国会议员们的话来说,“白人的责任”在于要将这些落后于时代的人们从几个世纪的衰败、疾病、愚昧和政治腐败中拯救出来,在于用教育儿童的办法来教育这些非白人社会里的人们。赛伊德发现这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广泛存在于当代现代化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之中,他被西方政治决策者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人物所信奉。但是,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指出我们如何可以超越文化界限、充分地表达其他民族的心声,也没有提示读者这种可能存在的选择。在进行批评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以同样的修辞极权主义(rhetorical totalitarianism)手法去反对他所选择的论敌。他不承认西方除了统治支配他人之外还有可能怀有别的目的与动机,不承认在表述方式问题上西方人内部存在分歧,不承认公开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时代以后,西方修辞已经发生许多历史性的变化。更有甚者,他没有认识到,东方学的对象即他所要辩护的民族内部也存在政治、文化分化。在他的著作中,这些被作为描述对象的人们,并没有比在其他西方作者的著作中享有更多的、独立自主的声音。赛伊德自己在立场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地道的两面性,恰恰说明了他是异文化的写作和学术研究的政治场合的产物。他一方面是一个巴勒斯坦人,另一方面又是美国大学里一位杰出的学者;赛伊德既是一个被赶出家园的、被统治支配的社会文化中的一员,也是一个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文化中的一名特权知识分子。赛伊德的《东方学》终究是选择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战术,因而他的作品和论点也出现了问题。在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情况下,赛伊德就认为,像人类学这样一些学科,承担着对不同于西方的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进行权威表述的任务,其写作中反映出来的与西方不同的文化,常常比东方学所描述的世界较为可信。不过,对于那些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而言,赛伊德论辩中提出的观点毕竟是有力的,他们如要对赛氏的批评作出反应,其迫切的任务依然是对传统写作方式进行反思,对新的方式提出实验性的试探。【马尔库斯和费彻尔(George E Marcus / Michael M J Fischer)《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三联书店,1998年3月,P18】第六通过以上的剖析,我们不难看出赛伊德所表现出的非常明显的作为“流亡者”的公共知识分子特征:
知识分子不应该为自己而生存,他的行为是属于公共的。而他在公众领域,就应该有自己特殊的身份对生活现象进行干预:知识分子的精神是独立的,他不会因为其他情况而改变自己的观念,成为“他者”的傀儡,甚至为了捍卫一种理念而不关注其他人的观念,或者可以因此与世俗“反目成仇”。这也是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精神和责任: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a private intellectual)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形诸文字并且发表,就已经进入了公共世界。仅仅是公共的知识分子(a public intellectual)--个人只是作为某个理念、运动或立场的傀儡、发言人或象征--也是不存在的。总是存在着个人的变化和一己的感性,而这些使得知识分子所说或所写的具有意义。最不应该的就是知识分子讨好阅听大众;总括来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P17)在知识分子的责任方面,我们也很容易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到赛伊德认为独立或者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履行的职责。赛伊德认为:“杰出的知识分子总是有自己的时代具有象征的关系:在公众意识中,他们代表成就、名声、荣誉,而这些都可用于持续不断的斗争或投入战斗的社群。”(P40))这点赛伊德还是做到了,甚至他也为自己所作出的感到沾沾自喜。“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了提升生命,本质上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的知识。”(赛伊德,Edward W Said《知识分子论》P1)针对巴勒斯坦问题上,赛伊德做得已经超过一个普通人的作为。他不但批评了美国的政策,同时也批评了阿拉法特的独裁统治。为了为拉什迪甘冒生命的危险而在所不惜。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已经做出了按照他所说的这些行为。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虽然赛伊德在这些方面已经做出了非凡的成就,也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他也还指出他并没有做到:“知识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化约式的类别(reductive categories)。” 他做得并不完美,或许我们这样来探讨有些苛责于人的色彩,不过为了他所说的,也是知识分子奉行的信条“在这样的社会文化里,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不再受无谓的前例、禁忌、复杂意结、人身神话等等的束缚,而是以合于人生的德目及理知为指归。”(《知识分子论》P2),我们不得不指出他在有些问题上的偏差。或者按照鲍曼的话来说,非理性的观念。我们不得不看到他有时候是叛徒。也就是背叛了捍卫最好价值的信念。首先,譬如在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他只看到了公共知识分子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面而忽视了,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故意或是不故意地忽视了知识分子的理想化所造成的灾难。“近代史中的主要革命,知识分子无役不与;主要的反革命运动,知识分子也是无役不与。知识分子一直是运动的父母,当然也是子女,甚至是侄甥辈。”P16我们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由于有了历史的教训,也不得不对他们过于理想化的设计生活而产生怀疑。当然,这也并不是我们不相信他们的理由,而是我们在相信知识分子的时候,也应该多一个心眼儿,审视他的作为可能带给我们的究竟是灾难还是美好的局面。其次,在引用福柯理论的问题上,马克思,韦伯,即便对于他理论的祖师爷福柯也大加鞭鞑。赛伊德在《米歇尔·福柯,1926--1984》一文阐述到:“他的不足也十分明显,尽管我认为他们并不会对他的观点的品质和力量造成严重的危害。例如,他的最引人注目的盲点,就是他对他基本上局限于法国的材料与他得出的表面上普遍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毫不在意。而且他对他的著作与同样面对着的排斥、限制和控制问题的女性主义或后殖民主义作家的作品之间的关系似乎也缺乏真正的兴趣。实际上,他的欧洲中心论几乎是总体性的,仿佛历史本身只在一群法国和德国思想家中间发生。(《福柯的面孔》P10)再次,起码在这个人为构造的民族认同问题上,他反对的东西实际上也是自己坚持的东西。这点是非常遗憾的。当然也是我们在谴责他的时候难以做到的。然而我们也不得不看到,他的反东方学的《东方学》情绪大于理论。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而对福柯的责难,更是显得神经过敏。什么都以单纯的角度出发,这种单调造成的谬论是很低级的。毕竟无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好,还是作为社会或者人类学者也好,理性地看待问题是起码的要求。很显然,亨廷顿敏锐地看到了文化差异将在未来的时间 里悄然加剧,所有社会在处理国内和国际问题时都将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在文化上。然而有一点判断不能令人信服,他认为文化差异将必然是冲突的根源。恰恰相反,不同文化在相互作用时产生的对抗往往带来创造性的变革。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信任》P6研究社会学和进行社会学的著述,它的目标,是要以不同的方式揭示,少些痛苦或没有痛苦地生活在一起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每天都在被压制着,被忽视着或是被怀疑着。
在进行社会学研究时的研究方法上,在参与性方法和“中立性”方法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选择。不介入式(non-committal)的社会学,没有任何存在的可能性。在今天实践着的许多种--这些种类从坦率的自由主义,一直向坚定的共产主义扩展--社会学中,追求一个道德上中立的态度,将会是徒劳无功的努力。社会学家,可能会忘记或是否认“世界观”对他们工作的影响,可能会忘记或否认世界观对人们单独或联合行动的影响,而其代价仅仅是丧失其他的每一个人每天都要面对的对选择的责任。社会学的任务,就是为了人类的延续,而务必保证这些选择是真正自由的选择,并使得这些选择继续是,越来越多地是自由的选择。《流动的现代性》P337很可惜,赛伊德并没有那么令人称心。不过,这个问题也并不是我们指责赛伊德就可以改变的。我们这样指责他也有与他犯同样错误的嫌疑。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怎么谴责这样的偏激,而是反思一下造成这种偏激的成因。这才是相当紧要的。赛伊德在《认知的策略》一文中说:法诺(Frantz Fanon)是人们公认的几名最雄辩的世界反帝斗争的倡导人之一,在他的著作里,他对不加节制的民族主义深持怀疑。这一点,粗心的读者很容易忘记。当我们阅读他的《世界蒙难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一书时,我们很自然地被前几章中描述的暴力所吸引,但是,我们不应忽视,在该书的后几章节,法诺对民族主义作了尖锐的批评,称其为民族主义意识的陷阱,并明确指出这是个谬论。他认为,民族主义固然是反殖民斗争的必要激励,但当殖民者撤离之后,民族意识就必须立即转变成“社会意识”。 法诺无情地抨击了独立后民族主义政党的种种弊病,他批评了那种对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他反对所谓的首都中央集权化,并提出要彻底消解其神圣性;他的批评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对官僚、技术权威及那些滥用口号的宣传者的批评。他指出,他们混淆视听,损坏民众的常识,掠夺了他们的参与意识。早在奈保罗(V.S.Naipaul)以前,法诺就曾对模拟政治和孤立主义提出过反对意见。他认为它们是产生荒诞和病态政权的温床,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这类政权在阻碍民主自由运动的同时演变成古罗马禁卫军式的、权力膨胀的专制国家;同时它们也产生了像蒙博托、阿明和萨达姆这样专横跋扈的独裁者。法诺曾预言,继续依赖形形色色的后殖民政府及其对新独立国家人民主权性喋喋不休的说教,而未能完成从民族主义到真正解放之间的转折,其结果注定要穿新鞋走老路,新的政治经济压迫丝毫不亚于旧的殖民政权。 法诺给我们提供的最使人折服的观点就是他对纯粹建构在民族认同策略之上的政治孤离主义和模拟性民族自治的批判。他认为,民族认同这一提法延续得太久,在完全不合时宜的情境里被长期滥用。这一现象在理论层面上的体现就是,自由和地位的符号与象征被当成事实本身:为了被人关注而想被人关注。在实际中,这便意味着,你仅仅成为一名独立了的后殖民阿拉伯人、黑人或印度尼西亚人其本身并无实质意义,这个称呼既非革命的纲领,也非革命的进程,更非革命的理想,它只不过是个比较方便的起点,真正艰巨的工作也许刚刚开始。赛伊德能认识到这一点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当然我们还应该采取一种质疑的态度:希望像说得那样做。虽然赛伊德生活在西方,由于带有殖民地色彩的东方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他的批评并非如我们想象地那么客观,也并非如萨伊德自己所说的已经彻底排斥了厚此薄彼的态度,他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有些言论甚至有失公道,显得偏颇,但是我们却不应该由此忽视了他所作出的非凡成就。毕竟他的缺憾还是很少。毕竟人无完人。即便我们像赛伊德责难福柯责难赛伊德,我们也可以说他的缺憾是微不足道的。他的精神遗产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并没有武断。赛伊德的逝世,世界上从此又少了一个尖锐批评的知识分子,又少了一个为东方言说的东方人,作为现在已经成为珍稀物种的传统知识分子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损失。不过,虽然赛伊德已经逝世,但是这种事业却不应该断了烟火。虽然现在传统知识分子后继乏人,但是我们也希望赛伊德的逝世能带给我们一种良好的结局。不但知识分子一如既往地尽职尽责要从超越国家等狭隘的观念上着足,每个人也应该汲取历史教训批评社会现象的同时,负责地生活。2003.10.13 本文没有成稿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