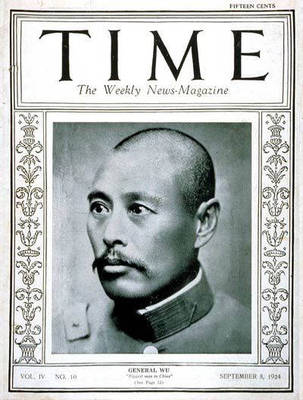台北的101大楼,登临一望即天涯,因为它是当今世界第一高楼。说到此,却让台湾东森媒体的副总裁垂头丧气:在台湾,人们很自卑,总想搞些世界第一来证明自己。笔者安慰他说:放心,不单是你们这样,在大陆也有类似情况。上海即将投入建造的浦东世界金融中心,高度计划超过101大楼,将再创世界第一,打破吉尼斯记录。一种非理性的狂热正在蔓延。海信50万元向全球黑客挑战,春兰号称要做“世界的春兰”,海尔要“国际化”,蒙牛“全球招聘新总裁”……很多营销人要大造各种破记录式的策划。爱“大”、爱“第一”,笔者称之为“吉尼斯思维”。这并非中国祖传的老病。一切似乎来自于一个根源:中国当代经济高速发展增添的国民底气。20年来年平均8%的增长率、超1000美元的人均GDP,制造业中,冰箱、彩电、洗衣机、空调、玩具,甚至橡皮筋、人造圣诞树的产能统统世界第一。人们戏称,美国人从早晨起床,到晚上入睡,均离不开中国制造的商品。自然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手中有钱,豪气冲天。这种经济的强势甚至逐渐蔓延为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粪青们”积极鼓噪国际政治上的强势话语权;“文青们”愤怒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偏见;“学青们”开始抱怨,中国如何错失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良机。

aihuau.com是中国人才有这种“吉尼斯”病症吗?未必。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是种“亚洲病”。很多人知道,1980年代的日本经济高涨,于是很多日本人开始“日本可以说不”,并试图用金钱的权势来证明自己:买下了诸多的世界名画,包括凡·高的《向日葵》;买下好莱坞的派拉蒙电影制片场;买下纽约世贸大厦的部分股权,甚至有日本商人想买下美国的象征—自由女神像。然后,是韩国。经济的成长开始让韩国人大力追求世界的认同。但大宇、三星等“英雄企业”开始出问题了,甚至,在科研领域也爆出黄禹锡这样的“科学英雄”的丑闻。文化的反思将是整个亚洲的使命。2004年,笔者在澳大利亚游荡。在DFS(全球免税商店)疯狂购物的,几乎全部是亚洲人。有趣的是,有人告诉笔者:当初是日本人在这里大把花钱,然后是韩国人、香港人和台湾人,现在则是大陆人。这种感觉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即使是相对淳朴的澳洲人,笔者有时候也能感觉到,他们对中国有着很幼稚的偏见。而现在,我们有钱了,我们有世界最大的这样和那样,往往不自觉地成为笔者教育澳洲人的说辞。作为一个研究、也经常参与行销操作的学者,笔者发现,聪明的跨国公司们在中国很快地理解了这种文化心态。一家跨国企业宣称,把“全球研发中心”设在中国;另一家公司宣称,要把亚洲总部设在上海。这往往能赢得人们的好感。美国的百威啤酒在中国大肆宣传,“美国销量第一”,现在则说“世界啤酒之王”。为什么呢?因为“老乡不识货,专拣大的摸呀”。世界最大的月饼、最大的锅、最大的青铜鼎、最大的裤子、皮鞋、最大的广场、最大的大场面……有个所谓的著名的策划人,为一家酒类企业策划、制造了世界最大的大白鲨充气模型,因为那个酒的品牌,就叫大白鲨。也许,从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脱亚入欧”运动开始,这种追求“吉尼斯”的“亚洲病”就形成了。从边缘到核心,追求西方认同的思维,偏狭地走进了一种追求“吉尼斯”式的一鸣惊人的死胡同。其实,西方的深刻就在于,工业革命实现了科学、技术、创新是最大生产力的梦想。知识与创新并不表现为“量”的积累,而恰恰是打破、突破。所以,施莱格尔们,很早就提出了“小的就是好的”的创见;同时,这也就是赫尔曼·西蒙盛赞那些产能占全球总量75%以上,却从不大声叫嚷自己的企业为“隐藏的冠军”的真正原因。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