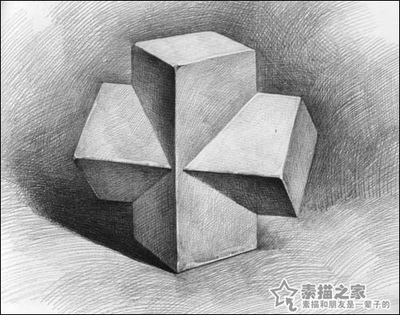文章节选自作者出版作品《全新思维》
1942年早冬,奥地利当局在维也纳围捕了几百名犹太人,其中包括一位名叫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的年轻心理学家。当时,弗兰克在心理学领域内已经是一位崭露头角的人物,他提出了心理幸福(Psychological Well-being)的新理论。他和妻子,蒂莉(Tilly),事先已经预见了这次围捕,因此他们尽力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保存下来。在警察闯进家门之前,蒂莉把维克多写的手稿缝进他的外衣内衬里。之后,他们夫妻俩被逮捕,并发配到了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中途维克多一直穿着这件外衣。来到集中营的第一天,他一直保护着自己的书稿。然而,到了第二天,纳粹党卫军没收了他的衣服,从此以后弗兰克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手稿。在接下来的三年,他们辗转于奥斯威辛和达蒙(Dachau)集中营,其间他的妻子、兄弟、父母都死于毒气室。弗兰克重新将自己的理论草草地涂写在偷来的废纸片上。直到1946年,盟军解放集中营一年后,这些皱巴巴的废纸片才被发现,这就是上个世纪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著作的雏形——弗兰克的书,《追求人生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在《追求人生的意义》一书中,弗兰克描述了自己如何在繁重的劳动、森严的守卫与饥饿中幸存下来的。但是,这本书并不仅仅是对生存的叙述,它也开启了一扇人类灵魂的窗户,指明了生命的意义所在。根据自己在集中营的真实经历,以及其他狱友的遭遇和精神感受,弗兰克详细阐述了他被捕前就开始研究的理论。他认为“人们关注的并不主要是获得快乐或者逃避伤痛,而是找到生命的意义。”促使人类存在的根本驱动力正是对意义的追求。弗兰克的方法——被称为“理念”的“存在分析治疗”(“logotherapy” for “logos”),就是希腊语“意义”的含义——很快就掀起了心理疗法上具有影响力的运动。弗兰克和其他人一起,试图在乏味而又恐怖的集中营生活中找到生命的意义。我最喜欢弗兰克在书中一页写道:“我知道,在思念心爱的人的时候,一个在世界上一无所有的人仍能发现自己的幸福,尽管这种幸福只能停留很短的时间。”他表明,即使是在苦难中,你也能发现生命的意义——毫无疑问,在苦难中,生命的意义就能体现出来。对意义的探寻是我们所有人存在的动力——外部环境和内心感受的结合将会让这种意义浮出水面。最后一点是这本书的关键——在今天也很有实用性。21世纪早期,种种力量刺激了人们对生命意义前所未有的探求。首先,贫穷和疾病问题仍然存在,发达国家大部分人都已经摆脱了生存的危机。正如我在第二章描述的,我们生活在物资充足的时代,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无法与之相比。人们不必为生存苦苦挣扎,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之中。如果弗兰克和他的狱友能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找到生命的意义,我们无疑也能在生活富足的舒适中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aihuau.com其他力量也在发挥作用。我在第三章提到,庞大的婴儿潮一代现在达到了人口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一代人的寿命比上一代人的更长,使他们更重视自己的精神追求和重新估量生命的价值。恐怖主义的威胁,让人们感慨生命的转瞬即逝,警醒人们寻找生命的意义。同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数据泛滥,让人们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掀起了人们探寻生命意义的热潮,也刺激了人们寻找概念时代必备的六种能力的欲望。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我在第二章简要提到过,称这个时期是“第四次大觉醒”(Fourth Great Awakening)。他写道:“精神上(或非物质的)的不公平现在和物质上的不均衡一样,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甚至比后者更严重。”他的言论和弗兰克在半个世纪前的观点一致:“人们有足够的物质条件生存下来,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他们掌握了生活方式,但是却没有意义。”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一位备受尊敬的密歇根大学政治学者,查阅和比较了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众多国家的政治观点,发现了一个相似的理念。每次进行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时,他发现答复者更加关心精神上和非物质方面的问题。例如,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58%的美国人说他们经常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而对物质上的思考却少很多。在对德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的调查中,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英格尔哈特认为,高度发达的世界运行规律变化十分微小,“人们的价值观正从‘物质主义’(强调经济和物质保障是最重要的)向‘后物质主义’(强调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更重要)逐渐转变。” 格雷格·伊斯特尔布鲁克(Gregg Easterbrook),一名美国记者,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更加大胆深刻的描述:“从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的转变正史无前例地进行着——它波及了成百上万个人——最终可能会被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首要的文化发展。” 不论我们怎么描述这个时代——“第四次大觉醒”,“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或是“精神需求”——结果都是一样的。意义已经成为了我们工作和生活的中心。探寻意义很显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并不能像买食谱一样有现成的烹饪法——打开一袋面粉,加入水,然后搅拌。对于个人、家庭和公司来说,能采取两种实用的、全面思维的方式开始寻找生存的意义:开始认真对待精神追求,寻找真正的幸福。认真对待精神追求麻省理工学院十分重视精神性。正如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埃里克·蓝德(Eric Lander)告诉人们的,科学仅仅是了解世界的一种途径。在很多不同领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精神性——并不一定指宗教,而是更大程度上指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部分。确实,信念——并不是宗教本身,而是比我们自身更大的、蕴含在某些事物之中的信仰——可能深深印在我们脑海中。也许并不奇怪,这些信念似乎贯穿我们的右脑半球。例如,安大略劳伦森大学(Laurentian University)神经学科学家迈克尔· 波辛格(Michael Persinger)进行了一项受人们争议的实验,这个实验使用了一种叫做“上帝的头盔”(God helmet)的装置。波辛格将这个头盔牢牢地戴在受试者的头上,用电磁放射线扫描他们的右脑半球。大多数受试者都反映感觉到了上帝或万物之主的存在,这个实验再次证明了,精神上一些神秘的思想可能是我们生物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同时,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安德鲁·纽伯格(Andrew Newberg)在修女们进行冥思,忘我地宗教祷告与上帝交流的时候,对她们的大脑做了扫描。扫描出来的图像表明,在这个时刻,大脑自我意识的那部分相对来说不太活跃——这是因为感觉到自己和某种更强大的事物连为了一体。这些科学家们的研究产生了一个新的领域,神经神学,旨在探寻大脑和精神感受之间的关系。正如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Caltech)的精神学学家史蒂文·库沃茨(Steven Quartz)所说:“对我们生物学结构的种种研究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我们是社会的产物,渴求认同感和存在的目的。”我们至少应该认真对待精神性这个问题,因为它能改善我们的生活——尤其在我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以及过度满足)的时候就显得更加有价值。例如,现代生活中的一些疾病——压力、心脏病等等——能通过精神疗法减轻。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倍受争议的领域。如果你想仅仅依靠精神性来战胜癌症或者让受伤的骨头修复,那结果将会是不堪设想的。但是,一种全面思维的方式——将左脑主导的理性和右脑主导的精神结合起来——会很有效。正如我在第三章提到过的,美国一半以上的医学院现在开设了精神与健康的课程。根据《新闻周刊》(Newsweek)的报道,“72%的美国人说他们喜欢和自己的医生谈论信仰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医生甚至开始对病人的精神状况进行记录的原因之一。这当然是一个微妙的话题。但是正如杜克大学教授哈罗德·科尼格(Harold Koenig)接受《宗教新闻服务》(Religion News Service)采访时说的,“我们现在和20年前的处境一样,那时医生要对病人的性生活做记录。” 科尼格估计,5%到10%的美国医生都对病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精神状况调查记录。像叙述医学,这种精神与健康疗法的兴起,在医学领域是一种大规模的趋势,它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种特殊疾病的载体。另一个开始重视精神力量的领域是商业。如果概念时代到处充斥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那么对精神的追求就会更加有意义,很多人将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满足精神需求。五年前,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马歇尔商学院(Marshall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伊恩·米特罗夫(Ian Mitroff)和咨询顾问伊丽莎白·登顿(Elizabeth Denton)发表了一篇报道,名为《美国公司的精神审查》(A Spiritual Audit of Corporate America)。该报告采访了将近100位公司主管关于精神力量对工作的影响后,得出了一些令人惊奇的结论。大多数主管对精神性的定义差不多——并不是指宗教,而是作为“寻找生命目的和意义的基本欲望”。而且很多主管十分担心工作中体现的的语言可能会冒犯宗教信仰多样化的员工,因此他们尽量避免和员工谈论这样的话题。米特罗夫和登顿同时发现,雇员们其实很渴望将他们的精神价值(体现整个人的价值而不是自身的某种功能)融入到工作中,但是往往不能达成所愿。读了这份报告,你几乎能看到一股对精神力量渴求的洪流在公司总部外边就被阻挡住了。于是有人抱怨:如果这股精神的洪流早被释放的话,公司将会发展得更好。米特罗夫和登顿也发现,重视精神力量并将其和公司目标结合起来的公司业绩胜过那些不注重精神力量的公司。换句话说,将精神力量运用于工作场所并不会使公司脱离自己的目标,而会更有利于公司实现自己的目标。越来越多的公司认识到了这点,我们也能看到,人们越来越重视工作中的精神需求——个人从工作中获得的精神满足同他获得的薪水一样重要。根据最近一项美国的调查,超过五分之三的成人认为,精神上获得更多满足能改善他们的职业生涯。同样地,英国智囊机构罗菲帕克(Roffey Park)的年度管理调查显示,7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更加有意义。在过去几年里,许多组织相继成立,例如工作情绪协会(Association for Spirit at Work),许多重大事件也接踵发生,例如商业精神会议(Spirit in Business Conference)的召开。我们也看到,在商业风险投资领域,精神的力量帮助那些追寻意义的人实现他们的理想,变得更加出类拔萃。回顾一下第二章提到的蜡烛行业,或者想想瑜珈馆的兴起,新教会的书店,以及环保车丰田普锐斯(Toyota Prius)和美体小铺(Body Shop)的化妆品。博学多才的福布斯杂志(Forbes)出版人里奇·卡尔高(Rich Karlgaard)说,这是下一个商业周期。第一个商业周期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质量革命,然后发生的就是卡尔高称之的“廉价革命”,它极大地降低了商品的成本,使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拥有手机和使用互联网。“那么,下一个商业周期是什么呢?” 卡尔高提出疑问并解释,“意义,目的,更深的生活体验。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词汇来形容,但是它们都说明了对这些生活质量的消费欲望正在上涨。记住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以及维克多·弗兰克对人生意义的追寻。”认真对待幸福
“幸福,”维克多·弗兰克写道,“不能被追随;而必须被追求。”但是我们从何来追求幸福呢?自从人类懂得思考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们。现在,心理学领域开始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答案了——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教授马丁·赛里格曼(Martin E.P.Seligman)博士,他是“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运动的始作俑者。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学院派心理学关注了很多事物,但是并不包括幸福感。心理学研究疾病、骚乱和机能障碍,却几乎忽视了什么才能让人们感到满足和有成就感。自从1998年赛里格曼接管美国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以来,他就开始慢慢在新的领域进行研究。赛里格曼和当时许多科学家一样,将注意力逐渐转向研究人类的满足感和康乐福利,开始揭开让人们感到快乐的秘密——并且鼓励其他人认真看待幸福感。根据赛里格曼的理念,幸福感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一部分源于生物学。我们从一出生,就有相对固定和自然的安康感在我们的基因上留下了烙印。有些人一事无成,而有的人成就斐然。但是,我们所有人都会知道如何才能到达个人发展空间的上层部分——在这里我们能找到自己的幸福。赛里格曼认为,在所有能激发我们幸福感的事情当中,首当其冲的有:令人满意的工作,避免消极情绪和负面事件的产生,结婚以及拥有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同样重要的还有感激之情、仁慈之心和乐观主义精神。研究表明,和幸福感没有多大关系的因素是挣更多的钱、接受很多教育或者居住在适宜的气候环境中。把这些因素一一列出来,能帮助我们创造赛里格曼所谓的“愉快的生活”(Pleasant Life)——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保持积极的生活心态。但是,愉悦的生活仅仅只是通往享乐主义的一个阶梯。更高的生活水平应该是赛里格曼所谓的“有益的生活”——利用自己的“独特优势”在你生活的主要领域获得满足感。它能让你的工作从被斯塔茨·特克尔(Studs Terkel)描述的“周一到周五如同行尸走肉”转变为一种召唤。“一种召唤是我们工作最令人满意的形式,因为我们是为了满足自身精神需要来完成工作,而不是为了它带来的物质利益,” 赛里格曼说,“我预计,享受工作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将会超过它带来的物质回报,成为我们工作的基本原因和动力。”有益的生活也对商业有好处。“幸福感的增加能提高生产率,带来更多的收入。” 赛里格曼写道。甚至还有一些新兴的管理学院正以积极心理学为原则创建。但是,有益的生活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有第三种形式的幸福感,是人们无法逃避的,那就是对意义的探寻……知道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并且运用它们为比你更强大的某事物服务,” 赛里格曼说。通过这种方式超越自我的做法,和那些虔诚的修女与修道士没有多大差别。社会的繁盛与物资的充足让更多人投入到对意义的追寻中来,伴随着越来越多人乐于这么做,探寻意义将会成为我们生活和个人意识的中心。在过去的十年中,有一本并不厚重的商业畅销书,它的名字有点奇怪:《谁动了我的奶酪?》(Who Moved My Cheese?)。它讲述了一个商业寓言故事,在全世界的销售量高达几百万册。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两个老鼠般大的小矮人,哼哼(Hem)和唧唧(Haw),他们住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矩形迷宫中,并且非常喜欢奶酪。经过几年的寻找,他们在迷宫的一个地方找到了很多奶酪,但是有一天,他们醒来却发现珍贵的奶酪不见了。有人动了他们的奶酪。对于这个发现,哼哼和唧唧有不同的反应。哼哼一直嘀咕着,想等待有人把奶酪送还回来。唧唧也很着急,但是他更现实,想去迷宫里寻找新的奶酪。最后,唧唧说服了哼哼,他们必须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等待奇迹的出现。从此以后,两个小矮人又过上了快乐的生活(至少直到他们的奶酪又被人动了的时候)。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当生活发生改变时,最明智的反应不是等待或者抱怨,而是面对问题并解决它。我并不反对《谁动了我的奶酪?》的观点,但是我不赞同它所做的比喻。在概念时代,可以说,亚洲的发展和自动化的兴起可能在不断地夺走我们的“奶酪”。但是,在物资充足的年代,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矩形迷宫中。今天,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更恰当的比喻应该是“螺旋形迷宫”(labyrinth)。错综复杂的矩形迷宫(mazes)和螺旋形迷宫(labyrinths)通常会被人们混为一谈,其实他们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截然不同。一个矩形迷宫通常分隔为多个互相隔绝的密封舱,路径复杂,并且很多路都是进入死胡同。当你进去后,你的对象很容易逃跑——速度和你一样快。一个螺旋形迷宫是由螺旋形的步行跑道围成的。当你进去后,你的目标就是顺着通往中心的路径,停下来,回转,然后往回走出去——不论你选择什么样的速度。矩形迷宫是待解决的解析难题;螺旋形迷宫是移动冥想的一种形式。矩形迷宫能让人失去方向感;而螺旋形迷宫则是中心明确的。在矩形迷宫中,你可能会迷路;但是在螺旋形迷宫中,你可能会迷失自己。矩形迷宫需要运用左脑,而螺旋形迷宫能释放右脑的能量。现在美国有超过4 000个公共的和私人的螺旋迷宫。它们兴起和流行的原因有很多,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本书后面我也会涉及一些。“在现在这个年代,很多美国人都喜欢去教堂寻找精神上的安慰,越来越多人重新发现螺旋迷宫是进行祈祷、反省和抚平情感创伤的途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这样记载。到处你都能找到螺旋迷宫:瑞士的市区广场,英格兰的绿色村庄,从印地安那州到华盛顿州到丹麦的公园,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大学,以及一些举办宗教仪式的场所,例如曼哈顿的河边大教堂(Riverside Church)、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National Cathedral)、奥尔巴尼的卫理公会派教堂(Methodist churches)、圣何塞的唯一教教堂(Unitarian church)和休斯顿的犹太教会堂。在医院和其他医疗场所也有螺旋迷宫——就像下面这幅图中的螺旋迷宫,它位于巴尔的摩(Baltimor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湾景医学中心(Bayview Medical Center)。不久以前的一个早晨,我就在一个螺旋迷宫中漫步,它是由边长四英寸的方砖围成的,由面积相似的白色正方形圈成八个同心圆,环绕着直径大概二英尺的中心区域。顺着外沿的方砖上印着几个词:创造,信念,智慧,信心。来访者经常从中选择一个词语,然后在向中心逼近的过程中重复念着,仿佛在默念冥想的咒语。我开始走进这个迷宫,朝着左边方向,走完了第一圈。我环视四周,看见一侧是几栋医学中心的大楼,另一侧是停车场。我觉得自己只是在一个圆圈里面漫步。于是我又继续前进。为避免分心,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步。我将视线都集中在形成步行通道的两条曲线上,并以尽可能慢的速度行走。两条线始终环绕着我。过了一会儿,我感觉有点像在一条又长又空旷的马路上行驶。不需要花太多注意力,我的意识就能领着我向前走——让我感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平静。这种体验,可能并不令人惊奇,和第六章描述的绘画课以及第八章的欢笑俱乐部的感受很相似。它阻止了我左脑思维的力量。“螺旋迷宫释放了右脑的能量,”设计和修建约翰霍普金斯迷宫的大卫·托尔兹曼(David Tolzman)说,“当左脑试图用逻辑思维在迷宫中艰难前行时,右脑丰富的创造性思维已经发挥了作用。”将螺旋迷宫发展到人类文明高度上来的是劳伦·阿托斯(Lauren Artress)博士,她是旧金山格雷斯大教堂(Grace Cathedral Church)的牧师。几年前,她去法国查图斯大教堂(Chartres Cathidral)参观,看见一个直径42英尺的螺旋迷宫深深嵌在教堂中殿的地面上。 当时,几把椅子将迷宫覆盖住了,这个迷宫已经有250年没有被使用过了。阿托斯将这些椅子移开,走进了迷宫。后来,她将这种螺旋迷宫的概念引入了美国。现在,她已经在格雷斯大教堂里安置了两个流行的螺旋迷宫,并且创建了一个叫做“Verditas”的部门,专门为教堂和其他组织提供螺旋迷宫的培训和成套材料。“我们生活在用左脑思维的世界……为了迎接下一个世纪的挑战,我们必须整合另一个完整的世界。”阿托斯说道。当人们走进螺旋迷宫,他们的“意识就会从线性向非线性转变”,并且发现“自己深刻、本能、典型的一面”。这种体验和进入矩形迷宫的感受不一样,她说:“螺旋迷宫能让你看见自己完全不同的一面,不只是停留在解决问题的表面或感受。”即使最具代表性的螺旋迷宫它的形状也很重要。“圆形是全体或个体的原型。因此,当人们步入螺旋迷宫,他们就已经开始看到自己的整个人生了。”大约40家医院和医疗中心现在都有螺旋迷宫——大部分都是因为共情作用和叙述技巧已经开始渗透到医学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分析的治疗方法尽管绝对必要,但是它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了——而那些曾被人们忽视的新方法却让病人身体好转。全面思维导致了约翰霍普金斯迷宫的出现,它成为了世界上最好的医疗设施之一。它的建立者希望能创造一个独特的地方,让病人、他们的家属和医务工作者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放松”。它可能会奏效。在螺旋迷宫的遗址,有两个风化了的笔记本,里面记录了通过迷宫的人们的感想。它们见证了迷宫给人们带来的慰藉和深刻意义。其中有经历了痛苦或挑战的医生和护士,也有要进行外科手术的病人家属,他们来到这里进行祷告、思考以及摆脱烦扰。病人们也在笔记本里写下自己的心路历程——就像下面这段文字,是我在来这之前的前几天刚留下的:我和其他人一样闯过了迷宫,并在此写下自己的感想。对于我来说,一个星期之前的外科手术,意味着我生命新篇章的开始。走进这个迷宫,我心中默念的词就是“信心”。我相信自己将会有一个新的未来。螺旋迷宫并不能拯救世界,我在书中讨论的六种能力也不是万能的。信息时代正向概念时代转变,左脑主导的思维模式正向右脑主导的思维模式转变,除了培养逻辑和分析能力之外,我们还要增强文艺才能,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维克多·弗兰克告诉我们的,完美的生活并不是担惊受怕地去寻找奶酪,而是像走迷宫一样,过程本身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