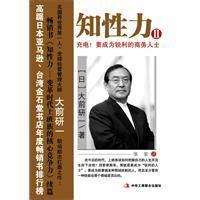文章节选自作者出版作品《制药业的真相》后来,布什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的143个成员国中独树一帜地反对放松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专利保护。美国只允许贫穷国家为几种有限的疾病制造它们自己的通用名药,而不能进口。由于那些最需要药物的最贫穷的国家根本没有能力建立生产工厂,这实际上是一个空头承诺。大型制药公司的魔爪已经伸向了政府的各个层面。最能够体现这种影响力的,恐怕就是2003年末将处方药福利加入到医疗保险计划中这件事了。最初的医疗保险并不为门诊病人的处方药付费,因为在1965年设立这项计划的时候,对这种福利并没有什么需求。人们在那时并没有服用像现在这么多的处方药,而且其价格也便宜得多。但是,现在老年人一般每天都要服用五六种药,每年支付数千美元的药费。由于老年人是选民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因此两个政党都希望能在2004年大选之前提出一项药物福利。再看看议会干了些什么。它们通过了一项法案,明确地禁止医疗保险运用它的强大购买力来争取更低的价格。医疗保险对药物价格没有发言权,它将不得不购买那些昂贵的模仿性创新药而不是性价比更好的药物。它甚至不能将价格限定在平均批发价格上,而现在医疗保险正在按平均批发价给那些在医院或医生诊所开出的药进行补偿。为了保证医疗保险对药物价格不构成影响,这项福利不仅仅靠医疗保险、还靠众多的议价权力更小的私营公司来执行。医疗保险将会资助这些公司,但是除此之外起不到别的作用。大型制药公司真是大走鸿运!其他任何一家大型购买团体——从美国退伍军人署系统到安泰人寿保险公司(Aetna)和通用汽车公司——都可以为更优惠的价格不断协商,但是医疗保险不行——它可能是最大的买主了。这项禁令不仅意味着市场扩大了,而且对价格几乎没有限制。这项法案一通过,大型制药公司的股价就直线上涨,而此前则经过了漫长的下跌过程。投资者知道这绝对是利好的消息。对老年人和其他公众又有什么消息呢?恐怕没那么好。该法案最初计划在10年之内花费4 000亿美元——或者说是一年400亿美元。其中四分之一的款项都只能算贿赂款项——数十亿美元用于让雇主们不要降低退休人员的福利,数十亿美元给私营的保险公司让它们给老年人设保,数十亿美元给了医生和乡下医院以获得美国医学会和美国医院协会的支持,等等。这样每年就只剩下300亿美元来购买药物。这有多大好处呢?没有多少。实际上,按照目前的增长率,几年之内,不断增长的药物成本就将会将这点福利抵消殆尽。另外,这项福利实施起来如此复杂,日常的管理费用很快会将剩下的资金消耗殆尽。aihuau.com在讨论这项法案期间,白宫就将成本预算提高到5 300亿美元。后来据说,医疗补助和医疗服务系统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简称CMS)的总精算师在该法案被通过的5个月前,曾将成本定在5 500亿美元,这么长的时间足够议会进行充分考虑。但是,据说政府向议会隐瞒了这一估计,直到该法案顺利通过之后才公布。事实上,这项福利给老年人带来的好处极少。尤其在初期,许多老年人每月支付的保险费和可扣除条款(保险单内的条款之一,免除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承受的损失赔偿最初的规定金额——译者注)比他们能得到的还多。由于成本上升(它必然会上升),饱受赤字困扰的议会不得不通过挤榨医疗保险计划中的其他部分,来满足该项福利的支付要求。老年人可能会发现不论他们是否签署了药物福利计划,每月B部分的保险费(取自他们的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都上升了。可扣除条款和共同负担的款项增加了。而且其他的医疗保险服务可能也不得不缩减药物福利方面的支出。但是,请记住,议会同意推迟到2006年才执行该福利,到那时布什政府已经不需要为后果负责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医疗保险的处方药福利计划。但是,它应当由医疗保险计划自己来执行,这样它们就可以像其他大买主一样来议价了。所有的老年人都应当享受所有性价比高的药物的福利保护。医疗保险应当有一个性价比较高的药物的处方集,就像那些大型私营的保险公司一样。只有这样,医疗保险处方药福利计划才可能比现在更节约成本,并且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服务。如果这么简单就能把事情做好,那么为什么议会不改正错误呢?答案就是,制药业太强大了,所以议会要优先考虑它们的利益。基本上,政府是听它说了算的。用参议员理查德·德宾[Richard J. Durbin(D-Ill.)]的话说:“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这个游说者,紧紧地把议会攥在了手中。”这个指控性质很严重,但是事实也确实如此。大型制药公司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议会通过一个可以进行价格协商的医疗保险处方药福利计划。议会则心甘情愿地将纳税人的钱交给制药公司和医药福利管理公司。大型制药公司把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哄得很高兴,在白宫和议会都吃得开。但是,共和党显然对其更加青睐。1999年,《纽约时报》报道,时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吉姆·尼科尔森(Jim Nicholson)写信给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海姆保德:“如果希望我们继续通过有利于你们行业的法律的话,我们就必须保持顺畅的沟通。”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将公众至于何种境地。海姆保德现任驻瑞典大使。据说,他在2000年的竞选中为共和党提供了超过20万美元的资金,并且要求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其他管理者和他们的家属每人为乔治·布什捐赠了一千美元。该公司总共为共和党提供了200万美元的资金。他们之间的“沟通”的确十分顺畅。付出的代价大型制药公司通过一些很老套的手段和几种新手段来制造它的影响力。其中当然包括游说,不过,大型制药公司将游说用到了一个新高度。另外,大型制药公司几乎对每一场可能影响其利益的政治运动都有献金。最近,该行业又将很多资源用于建立和资助所谓的“草根”组织,以便扩大它们在媒体上的影响力。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些手段。特殊的说客制药业在华盛顿拥有最大的游说团——这说明了一定问题。2002年,它雇佣了675名说客(比议会议员的人数都多)——许多人是从华盛顿138家游说公司招募来的——花费了超过9千1百万美元的成本。这些说客的职责就是在华盛顿的权力机构的走廊上徘徊,伺机为制药公司的利益服务。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在华盛顿也有办公室,2002年其全职员工120名,花费的游说成本高达1千4百万美元,拥有112名游说者。根据消费者拥护团体公共公民的报告,从1997年到2002年,该行业花费在游说上的资金高达4亿7千8百万美元。制药公司的说客通常都神通广大。2002年,他们中间包括26位前议会议员;另外还有342位曾经在议会工作过或者与政府官员交情匪浅;20位曾经是议会办公室的主管,这中间有掌握实权的官员,诸如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比尔·托马斯[Bill Thomas(R-Calif.)]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奥林·哈奇。说客尼克·立特菲尔德(Nick Littlefield)是曾经供职于健康、教育、劳动和退休委员会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D-Mass.)]的总律师。一些说客与议员有直接的关系,包括斯科特·哈奇是参议员奥林·哈奇的儿子,以及前参议员伯奇·贝赫是参议员埃文·贝赫[Evan Bayh(D-Ind.)]的父亲,同时也是《贝赫—多尔法案》的缔造者。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两位前主席(其中一个现在是密西西比州的州长)也加入了制药公司的游说团。你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即使没有巨额的政治献金,政府和游说团之间的这道旋转门保证了该行业在华盛顿广受关注并且耳目众多。似乎没有人关注明显的利益冲突问题。先看看参议员哈奇。从1991年到2000年,他从制药业收到的游说献金是最多的,并坚定不移地在参议院中为其服务。他的儿子斯科特在一个叫做帕里罗马尼(Parry Romani)的游说公司工作了许多年,该公司的主要客户是制药公司。2002年,他自己开了一家“沃克·马丁&哈奇”(Walker Martin & Hatch)公司,在当年就表现出了非凡的业绩。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多数业务来自想得到奥林·哈奇支持的制药公司。它的客户包括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和葛兰素史克公司。现在来听听哈奇父子是怎么说的。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儿子说:“我并不认为我在(议会或政府的)办公室里受到了什么不同的待遇。我并没有觉得他们认为‘哦,这是参议员哈奇的儿子。’我想他们看到的是三个辛勤工作的绅士并且因此而尊敬我们。”果然如此吗?相反,父亲似乎更现实一点。他告诉《洛杉矶时报》:“斯科特是我的儿子,我自然希望他的客户能对我做的事情感兴趣。”慷慨的献金制药业对政治运动十分慷慨。1999年到2000年选举期间,制药公司直接的政治献金达2千万,还有6千5百万的“软”资金。过去,制药公司给两党的资金基本相等,而现在80%的资金捐赠给了共和党。不过,剩下的资金给主要的民主党人也足够了。市民组织共同事业促进会对20世纪90年代制药业献金的最大受益者进行了调查。它发现并不出乎意料,在参议院中,参议员哈奇名列第一,第二名是后来成为参议院主要领导的参议员比尔·福斯特[Bill Frist(R-Tenn.)]。在众议院,名列榜首的是众议院议员比尔·托马斯,下来是众议院议员南希·詹森[Nancy Johnson(R-Conn)]。但是一些有权势的民主党人也享受了该行业所给的巨大好处,这些人所在的州是大型制药公司的根据地,包括前参议员罗伯特·托里切利[Robert Torricelli (D-N.J.)]和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 (D-Conn.)]。举个例子,1999年托里切利提议了一项法案,以帮助先灵葆雅公司的畅销药和其他一些药物更容易地获得专利延期。根据共同事业促进会的报道,该法案是在托里切利任主席的民主党参议员竞选委员会收到先灵葆雅公司的5万美元献金的第二天被提起的。参议员哈奇为该法案召开了听证会。他当时正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并乘坐着先灵葆雅公司的湾流 (Gulfstream)喷气式飞机在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讲。该公司还雇佣了斯科特·哈奇所在的那家游说公司。后来,很显然该法案让美国议会十分为难,就不了了之了。制药业还支持了各种先锋社团,这种社团往往自诩为草根组织。其中的一个“追求更好的医疗保险的公民”,从名字来看,似乎应当是一群老年人为了提高他们的医疗保险待遇而成立的组织,但其实根本不是如此。1999年成立之后,该组织在1999年至2000年的选举期间花费了将近6千5百万美元来阻止针对制药公司的各种形式的价格管制。该组织的的执行主管提姆·赖安(Tim Ryan)是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建议委员会的主管。其成员也与制药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联合老年人协会在2002年的选举中为有利于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议题广告”(issue ads)支付了大约1千8百万美元。搜集这些广告的不是别人,就是提姆·赖安。当越来越多的人对制药业不满时,制药公司也越来越隐藏在这些先锋社团背后。这些团体与我在第八章描述的病人拥护组织很相像。正因为它们表里不一,所以非常有效。制药业对政府的影响力显然渗透进了布什政府。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是西尔列(G. D. Searle)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董事长和主席,这家公司后来与法玛西亚公司(Pharmacia)合并,而法玛西亚公司后来又被辉瑞公司并购。米切尔·丹尼尔斯(Mitchell E. Daniels)是前白宫预算主管,同时也是礼来公司的高级副董事长。总统布什在上任之前也在礼来公司的董事会里供职。这种关系是如此紧密,使得每年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年会看上去都像是华盛顿官员的秘密会议。例如,2003年的年会,到会的有总统布什、卫生与公共事务部秘书汤米·汤普森(Tommy Thompson)、前FDA委员马克·麦克莱伦(Mark McClellan)以及共和党参议员竞选委员会主席参议员乔治·艾伦[George Allen (R-Va.)]。得到的回报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讨论了一些有利于制药业的议会法律条文,从《贝赫—多尔法案》开始到1980年的《斯蒂文森—魏德勒法案》。这些法案使制药公司可以从国家卫生研究所赞助的研究中获益。《贝赫—多尔法案》的本意是要鼓励基础研究向实践运用的转变,但是,总体而言,该法案是否成功还有待商榷。当然,该法案通过之后,生物医药专利显然迅速增加了。但是,许多批评家认为实际效果可能与预期的恰恰相反。通过鼓励将一项新技术的几乎每个方面都申请专利,虽然尊重了商业秘密,但是实际上可能会降低科学信息的分享程度、阻碍对新科学技术的开发。而且它显然没有执行这一条规定,即经学术机构授权获得的药物在“合理情况下应当公开”。这条规定被制药业、学术医药中心、国家卫生研究所和议会彻底忽略了。限于篇幅,对于大型制药公司从与之合作的议会那里得到的所有好处,我只着重讲几点。我们在上一章中了解到,有几条最有利可图的法规都是与扩张药物的垄断权有关的。还有一些是关于重大的税收优惠的,这样世界上最赚钱的制药公司只需要将其收入的很小一部分用于纳税。有一条规定最近正讨论得热火朝天。1987年,在制药业的压力下,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除制造商之外的任何人从其他国家进口处方药——即使药物是美国制造的也不行。正是这项法案阻止了人们从加拿大获取更便宜的药物。还有一些议会的行动是针对FDA对该行业的监管能力的。例如,1997年的FDA现代化法案就是对制药业的巨大让步。该法案降低了该机构批准药物上市的标准(例如,有时仅仅用一个而不是两个临床实验就可以了)。但更重要的是,议会并没有授权FDA在批准新药时要求将新药与旧药进行比较测试。正因为制药公司只需要将新药与安慰剂做比较,才造成了该行业现在可以靠模仿性创新药维生的局面。不然的话,制药公司将别无选择,只能努力去研制真正的创新药物了。议会给大型制药公司的最隐秘而又最大的礼物,就是授权由制药业赞助的私营公司决定医疗保险是否应当为处方药标签之外的用途付费。尽管制药公司不能在FDA批准的用途之外推广药物,但是医生可以将处方药用于他认为可以用的任何疾病。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保险公司是否应当为这些用途付费——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大约有一半的处方药都是用于标签之外的用途。这一问题对医疗保险计划尤其重要,该计划是美国最大的为门诊病人药物付费的政府计划。1997年,议会授权给Drugdex信息服务公司,使其成为能够决定医疗保险计划将为标签之外的哪些用途付费的三个组织之一。Drugdex公司将药物及其用途列示在一个大目录里,它将这个目录卖给制药公司以及所有支付3 823美元年费的人。如果一种用途被列入其中,那么医疗保险就不得不为用于该用途的处方药付费。Drugdex公司的股东是汤姆森公司(Thomson Corporation)。这个数十亿美元的大公司旗下有一些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以及许多分支机构。这就导致了一种“混乱”的关系,汤姆森公司为制药公司进行后续医药教育来赚钱,而制药公司通过将自己的药物列示在汤姆森公司的Drugdex目录上赚钱。此外,这些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教育”医生如何将这些药物用于标签之外的用途。鉴于Drugdex公司与制药业的关系,Drugdex公司授权的标签之外的用途是其他两个非营利组织的目录的两倍,也就不足为怪了。2003年,据《华尔街杂志》报道,Drugdex公司对美国最畅销的12种药物共列示了203种标签之外的用途。例如,其中对Neurontin(一种治疗癫痫症的药物)就有48种标签之外的用途。这样,Neurontin就可以用于打嗝、戒烟、偏头痛和许多其他疾病,医疗保险都需要为其付费。因为Drugdex的目录比其他目录列示的标签之外的用途多很多,实际上它就是规则制定者。它引用文章来支持它的目录,但是这些文章并不需要符合任何科学标准。最近甚至还有一个制药公司建议委员会来检查Drugdex公司的目录。《华尔街杂志》的记者大卫·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写道,当他为写作一篇关于Drugdex的文章而向该委员会调查的时候,该委员会突然解散了。总之,Drugdex是一家与制药业关系密切的公司,它控制着医疗保险受益者的处方药福利。而花费的全部是纳税人的钱。这着实是一项大礼。另外,由于这种安排不需要FDA的批准,使得FDA科学审查的职能几乎丧失殆尽。显然,Drugdex公司把任何东西放进目录里,制药公司会都同意。国际性的尴尬当第三世界国家抱怨大型制药公司将艾滋病药物定价过高时,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都袒护了制药业。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时候,其成员要求药物享有20年的专利期(当时,许多国家甚至都不懂得药物是可以申请专利的)。当出现公共卫生紧急情况时,可以有例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们可以发布“强制授权书”,让其他制造商生产需要的药物。贫穷国家可以在2005年之后再执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后期,急需控制艾滋病疫情的南非,威胁说要生产或进口通用名药。制药业强硬地抵制这种行为。克林顿政府(无疑受到了制药业在华盛顿的影响)警告说要进行贸易制裁。随后,政府由于人们的愤怒而退缩了。几家制药公司走投无路,宣布降低在几个非洲国家的药物价格,但即使是打折后的药物也没有印度制造的通用名药便宜,并且很难获得。后来,布什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的143个成员国中独树一帜地反对放松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专利保护。美国只允许贫穷国家为几种有限的疾病制造它们自己的通用名药,而不能进口。由于那些最需要药物的最贫穷的国家根本没有能力建立生产工厂,这实际上是一个空头承诺。而像印度和巴西这样稍微发达一些的国家,虽然更有可能生产通用名药,但它们不能冒犯美国而招致经济制裁。布什政府于是又说,可以允许几个国家在特殊情况下进口通用名药,但是这项建议又由于官僚程序而未付诸实施。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制药公司的利益,无视第三世界国家中数百万艾滋病患者的痛苦。似乎是为了让人们加深这种印象,布什政府在2004年初拒绝将原定的150亿用于第三世界艾滋病治疗的联邦资金用于通用名药生产。2003年底,南非的竞争委员会裁定葛兰素史克公司(艾滋病药物的主要制造商)和另外一家公司违反了该国家的竞争法案。这两家公司的药物定价过高,而且即使有合理的专利权使用费也拒绝将专利授权给通用名药制造商。此后,葛兰素史克公司同意南非的4家通用名药公司生产它的3种艾滋病药物,并且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所有47个国家中销售。艾滋病治疗在非洲现在一年需要300美元,而在美国则需花费10 000美元。然而,没有人相信该公司在非洲市场上是赔钱的,那么足以知道它在美国市场上该是多么赚钱。将FDA送到制药业的手上议会同样将FDA列到了制药业的薪水册上。1992年,它推行了《处方药用户收费法》( Prescription Drug User Fee Act),要求制药公司向FDA支付用户费用。这项规定只在加速批准药物时才生效。这些费用最初是每种新药大约31万美元,很快就占了FDA药物评估中心总预算的一半。这就使得FDA受制于它所监管的行业。对于制药公司来说,用户费用算不了什么,很快就会被上市销售所带来的收益弥补了。该法案应当是五年修订一次。2002年版的该法案被添加到了一项防止生物恐怖活动法案中,获得议会的一致通过,使用户费用增至每申请一种新药支付576万美元。这样用户费用加起来就是一年2亿6千万美元。其中的一小部分被用于一些有限的安全监管,绝大部分被用于加速药物的批准。由于该项法案的通过,FDA又新增了一千多名员工来处理新的药物申请,而且2002年还要新招500人。这样,有制药业付费的员工就占据了FDA参与药物批准的员工总数的一半。然而现实是批准的过程越快,危险药物上市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处方药用户收费法》通过后的十几年,已经有13种处方药不得不从市场上撤销——这是以数百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我在第二章中提到过,FDA曾经在批准药物的时候被认为是过于缓慢和复杂。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回了。它现在批准药物的速度要比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同类机构快得多。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匆忙的批准,使得它对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放松了要求。尽管对于那些确实创新的药物有时可以走捷径,但是现在捷径走得过于频繁了吧。而且,批准药物上市很快,但是一旦药物被证明是危险的,将它们从市场上撤销的动作却很慢。例如,Warner-Lambert公司的糖尿病药物Rezulin,1997年在英国市场上被撤下来,因为它导致肝功能衰竭,但是它在美国却是两年半之后才从市场上撤销,那时它已经导致了至少63人死亡。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用户费用在FDA内部产生了一种不平衡的关系。既然大部分资金都用在加速批准上,因此这个部门增长很快,而其他部门的人员和资源都萎缩了。由于药物进入市场的速度加快,这使得FDA越来越难以履行它在其他方面的职能了——包括对药物安全性的监管、保证生产标准和规范市场等。该机构还有直接的利益动机去满足制药业的要求,这正是议会希望的事情。如果FDA惹制药业不高兴了,用户费用可能就没有了,这样该机构的许多员工就会失业。由于有从高层政治人物那里来的有利于制药业的压力,以及一向讨厌行业监管的政府做后盾,《处方药用户收费法》毫无疑问地限制了FDA的独立性并影响了它的决策。此外,FDA的18个药物批准建议委员会也受到了制药业压力的影响。这些委员会包括在各个特殊领域里的专家,他们的报酬是根据他们审查的新药申请和给FDA关于批准新药的意见来确定的。FDA对他们几乎总是言听计从。许多委员与有关公司都有财务联系。尽管利益冲突的原则禁止这些关联委员参与某种药物的批准,该机构总是会重视某人的意见而放弃遵守规定。《今日美国报》检查了FDA2000年的听证会记录,发现“92%的会议中至少有一名委员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并且“55%的会议中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委员存在利益冲突问题。”据说FDA的委员们能从制药公司获得巨额的咨询费。他们当然有强烈的动机这样做。他们可能都不需要说:“如果你想让你的药物获得批准,就得给我钱。”根据《华盛顿时报》记者奥格斯特·格雷宾(August Gribbin)的报道:“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制药公司管理人员说,这些建议委员会的成员获得咨询工作的方法简直就是‘敲诈’,因为如果公司拒绝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话,就可能使已经花费了上千万美元开发的药物毁于一旦。”政府改革委员会的主席众议院议员丹·伯顿[Dan Burton(R-Ind.)]认为这些委员会中充斥着与制药公司“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人。”精心挑选FDA的委员——选对人布什政府与制药业之间如此紧密的联系,可能与2002年阿拉斯泰尔·伍德(Alastair Wood)任FDA委员的提名在最后时刻被撤销之事有关。伍德博士是位于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临床药理学的一位广受人们尊重的教授(也是我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位前同事),据说他受到参议员比尔·福斯特及卫生与公共事务部秘书汤米·汤普森的极力推荐。但是,他还是一位主张对FDA加强监管的改革的支持者,而且显然是制药业高管和其他的药物“自由市场”拥护者(包括《华尔街杂志》的编辑)比较讨厌的人物。根据《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故事的结局是由于背后来自白宫的压力,才使得事情出现戏剧性的转变。用参议员福斯特的话说,“很多人担心他(伍德)会过于强调(药物的)安全性。”想象一下吧,雷蒙德·胡斯理(Raymond Woosley)博士也是一位著名的临床药理学家,而且也是该职位的一位早期的候选人(他后来选择了一个重要的学院职位),他说:“很明显,任何人只要说了该行业不爱听的话就都不可能得到这个职位。”最终被任命的FDA新委员们实在是太合制药业的胃口了。马克·麦克莱伦(Mark McClellan)博士是白宫新闻秘书斯科特·麦克莱伦(Scott McClellan)的兄弟,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审计官和奥斯汀市前市长的儿子,而且他一贯地支持制药公司。2003年墨西哥,在他所谓的他的“第一次国际演讲”中,针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药物价格之间的差距,他的建议不是降低美国的价格,而是提高其他地方的价格。他批评其他富裕国家实行了“过于严格的价格管制”,而 “这样无异于直接侵犯了专利权”。他似乎轻信了高昂的药物价格是为了弥补研究和开发成本的谎言。他说:“事实上,药物价格如此之高,是因为我们国家在开发新药上花费了巨额成本。”实际上,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价格与研发费用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与利润有关罢了。尽管没有任何证据,麦克莱伦接着说,“对研究开发费用的过多的价格管制将会影响到新产品的开发。”他在演讲中一次也没有提到 “超额利润”这个词。他对巨额的销售预算也是只字不提,只是毫无根据地说了一句,直接面向顾客的广告“有利于公众健康”。简言之,这个演讲稿就像是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写的。我们当然希望FDA的委员们不只是充当大型制药公司的雇佣骗子。而且我从他的职位角度看,根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讨论药物的定价问题,因为这并不是FDA的职责。2004年初,麦克莱伦博士又升任了布什政府的另一个更重要的职位——医疗保险和公共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主任。我不想对FDA吹毛求疵。它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很多尽职的公务员和杰出的科学家全心全意工作着。但是,他们被议会的强制规定束缚了手脚,并被他们的委员带错了方向。他们也受到了华盛顿越来越浓厚的反监管氛围的影响,在这种氛围里,似乎“市场”就可以决定哪种药物是安全有效的而哪种药物不是。我曾听说过,FDA的某些部门的员工士气很低落,我很清楚为什么会这样。虽然需要机构监管的行业有时好像掌控着他们的机构,但仍有很多职员想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他们是值得大家感激的英雄。正是他们阻止了更多的Rezulins荼毒生灵。没什么新花样的计划

2003年夏天,《纽约时报》获得了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绝密文件,该文件是关于下一个财政年如何购买影响力的计划。根据这篇报道,在这方面的花费将增加23%——升至1亿5千万美元。其中,7千3百万用于联邦政府的游说, 4千9百万用于州政府的游说(制药业贸易组织逐渐将注意力转移至州政府,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了解到,现在州政府比联邦政府更与该行业息息相关)。费用中还包括用来游说FDA的5百万美元(我不由地想这对该机构委员们的演讲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超过1千2百万美元会用于资助“志趣相投的”医生、病人、学术机构和有影响力的少数族裔组织。另外1百万将用于“那些杰出的雇佣经济学家——他们及其思想领袖通过发表文章和论文来反对联邦价格管制,并且是制药业的快速反应团队。”还有给“第三团队的文章和贡献的补偿”50万美元。另外,还有1千8百万美元将用于在国外抵制价格管制和保护专利权。也许最为傲慢的一条是“为了改变加拿大的卫生保健系统”的1百万美元(加拿大人是否也认为他们能够如此廉价地被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收买呢?),还有50万美元将用于阻止药物从加拿大流入国内。《华盛顿邮报》在2003年的一篇社论中总结得很好。它警告说:“任何想要讨论制药公司的人,不论其学术观点和立场看起来多么中立,都应当接受关于他们收入来源的仔细调查。”通常记者们并不这么做。一个大报的两位记者告诉我,他们不问这方面问题的原因是,如果问了只会使他们的采访写作更难完成。如果他们发现消息来源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编辑可能会要求他们寻找新的消息来源。或者消息来源会因为被问及这些问题而十分恼火。因此这里有一条潜规则——“别问也别说”。但是如果记者只确认消息来源的学术地位,而不告诉读者与其相关的利益冲突,那分明是在误导读者。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蓝图听上去只不过是一份危机四伏的计划书而已。一份该组织的委员会备忘录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份备忘录认为,制药业现在正面临着一场“完美风暴”,这是由于“政府在国外越来越多的价格管制,导致了得不到政治支持的国际间的价格差异;通过互联网可以从国外得到越来越多的药物;各州主动投票要求降低美国的药物价格;各州强烈要求在公共医疗补助计划中给予药物折扣;以及‘人们错误地认为药物价格在以每年20%的速度上涨’。”尽管我可能对上述原因稍有微词,但是确实正在刮起一场“完美风暴”。我们能看的第一个迹象就是,原先铁杆支持该行业的议会在近期弥补了《哈奇—维克斯曼法案》中的若干漏洞,并且同意从加拿大再进口较便宜的药物。但是尽管出现了这些迹象,该行业还是拥有政治支持。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主席艾伦·霍尔默(Alan F. Holmer)在该组织2002年年会上说,“我们的咒语就是,无论政治环境是否可以掌控,我们将永远不允许失败发生。”而且它一直都掌控得很好。正如众议院议员伯纳德·桑德斯[Bernard Sanders (I-Vr.)]所说的那样,“即使是纽约扬基队(New York Yankees)(一个著名的棒球队——译者注)有时也会输,而洛杉矶湖人队(Los Angeles Lakers)(一个著名的篮球队——译者注)偶尔也会输掉一场球赛。但是有一个组织从来没有输过,它在议会保持了数百次胜利而无一次失败的记录。这就是制药业。”在下一章中,我将会质疑这样战无不胜的记录是否还能保持下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