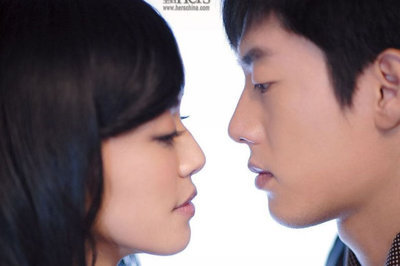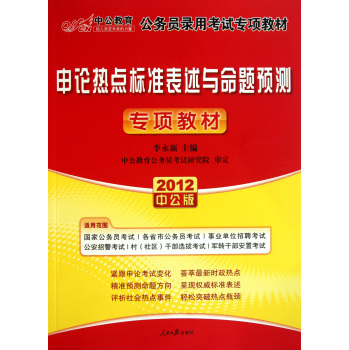宋艳刚先生拍佛多年,我也读佛多年,一天也没拉下。盖因他赠我的一年一册的《释家》挂历就年复一年地挂在我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多年看下来,《释家》系列作品便或深或浅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佛的照片需用佛心禅意去读之,解之,悟之,道之。于是,我诚惶诚恐地写成这篇小文。 西方一位哲人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没人能逃离苦难,所以就产生了宗教,是为人的精神的皈依。对此,我并不完全苟同。起码就东方文化的精髓讲,我更赞同台湾佛光山主持星云大师的观点,即:人们学佛的最大利益,就是认识宇宙与人生的真谛。人要懂得谦卑,和自然和谐相处,建立“同体共生”的关系。 星云大师之言,也是我对宋艳刚先生作品的感受之一。 纵观《释家》系列,大量作品以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角度再融入大体相同的主人(僧人),反复在阐述同一主题:佛与自然美丽的和谐。无论是在春天桃花红、菜花黄的媚人风光里,在夏日翻滚的麦浪中与硕果累累的杏树上,在红叶烂漫的秋林小径中,还是在白雪皑皑银装素裹的三九寒冬,佛的弟子们或劳作,或休憩,或诵经,或行走与其间,你顿会有一种“天人合一”与“万法归一”的顿悟。作者在创作这些作品时,采用了与之主题相适应的影像语言,即多用广角镜头以使空间更阔大,这也有佛心包容万物的意思。 影像语言的多样与强调视觉的节奏感,是我的第二个直观感受。 多年来拍摄同一题材,而镜头中从主体到背景都是大同小异的表现对象,这对一名摄影家的创作能力是一个考验。其难度首先是同中求异,即美学中常说的“熟悉的陌生人”,是说从创作立意上能否逐年深入即往更深的层次挖掘。在这一点上,如果说宋艳刚先生早期的作品还停留在“寺庙加僧人”以及肖像式的描摹上,那一路走来,作者已明显地将镜头从人物表象到人物内心延展,从“实”(复原物象)到“虚”(表现物象)延展。在《释家》系列中,有多幅主人公背对镜头的作品,这种“反打”镜头是一般摄影家极易忽视的。被摄者背对镜头,从构图理论上讲,要表现的一般是背景,即人物面前的景或物。在这些作品中,人物面对的全是自然界的美景,或是绵延的终南山,或是秋日红叶,也传达与强调作者对 “天人合一”的和谐与宁静的向往与追求。这些不同景别,不同角度甚至不同方向的作品,使作品有了视觉上的节奏感及旋律的变化。 作者借作品告诉人们:佛性即人性。“众生皆有佛性”,只要我们每个人都有“我就是佛”的认知与担当,那么你便能顶天立地生存于自然之中。在宏大的自然与渺小的僧人之间有感而发,作者用影像搭起了一座沟通僧众之间的桥梁。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繁奢浮华的社会里,宋艳刚这些作品把我们带入一个朴素、宁静的世界之中,犹如生命行旅中出现的一股清泉,尽管是涓涓细流,但多少可以滋润人们那颗焦躁的心。

宋艳刚先生在业界已是榜上有名,人称“儒商”,但为人谦和,行事低调,不显山露水。因为他把山水全溶入胸中继而又表现在摄影作品中了。 从摄影创作的分类上讲,宋艳刚先生的《释家》系列属于“表现” 一类的,具体到佛僧个象,我以为作品中“写意”即“以虚映实”的成分似乎少了一些。“以意传情”的空灵之感因画面中过分逼真的人物及背景关系而遭到削弱。从技术上看,其焦点、曝光、色彩以及人物情绪乃至体态都无懈可击,但反复咀嚼,仍觉得缺欠了点什么。佛禅之道,许多境界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这是用机械照相方式获取影像的一大难点。相对而言,绘画似乎更好表现一些。这一点也是我自己在创作中的一大弱项。如何将照相机写实功能转化为写“心”的意象,化实景为心像,追求画外之意,都是我与宋艳刚先生应努力去探索的方向。作为宋艳刚先生多年挚友,以上这段文字,写出来也有与其共勉之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