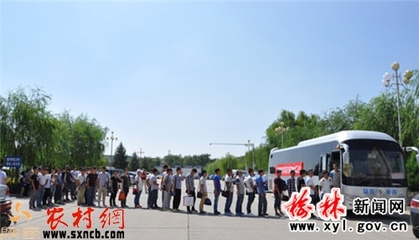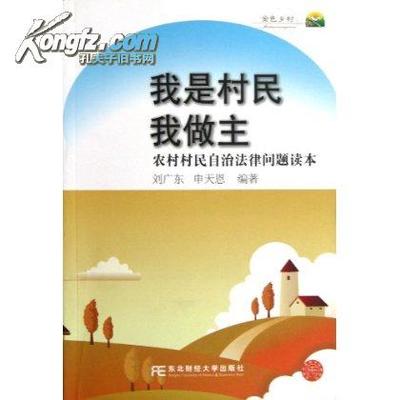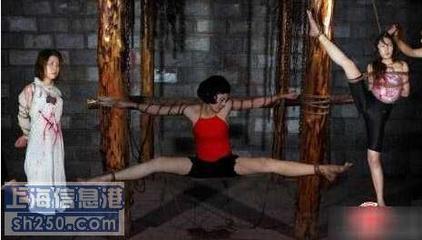中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非均衡性分析李贤利(南京政治学院理论二系,江苏南京,210003)Analysis on the Problems of Institutional Disequilibrium. of China’s Current Farmland Property LI XIANLIThe Second Theoretical Departments of Nanjing Institute Politics of PLA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通讯地址:南京市中山北路307号南京政治学院研究生大队十六队邮政编码:210003联系电话:(025)83341201 13953186829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作者简介:李贤利(1975-),男,山东沂南人,南京政治学院理论二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新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中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非均衡性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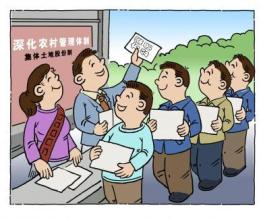
摘要:制度非均衡是由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不一致引起的,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过剩。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等有可能促使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宪法秩序、现存制度安排、制度设计成本、现有知识积累、实施新安排的预期成本、制度变迁方式等外部因素可能会使制度非均衡长期存在。本文运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非均衡,认定我国既定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构明显存在着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度的非均衡性,制约农业的发展,而这恰恰是制度创新的诱致因素。关键词: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制度供给不足;制度供给过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Abstract: Institutional disequilibrium means that institutions supplied and institutions demanded are not in balance. It can be pided into institutional supply shortage and institutional supply excess. Changes in institutional cost, profit and the set of institutional choice may cause some institutions into disequilibrium .moreover,institutional disequilibria may be made to be persistent by the following factors such as constitution order, exist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nstitutional design cost, lack of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the expecting cost of practicing institution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method. This paper mainly uses theorie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o analysis problems of institutional disequilibrium. of China’s current farmland property and assure that China’s current farmland property institution in not in balance, which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our agriculture ,this is exactly the cause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Keyword: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Institutional Disequilibrium;Institutional Supply Shortage;Institutional Supply Excess;Farmland Property Institution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农业发展面临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严峻挑战的今天,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已难以继续为农业现代化、农业国际化和农村非农化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持,由于农村土地产权问题及其矛盾纠纷而引发的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进步等“三农”问题也愈演愈烈,事实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已处于一种典型的非均衡状态,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潜在利润或外部利润的出现。换句话说,尽管现行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可以增进许多农户个人及社会福利水平的潜在机会,却难以使之成为现实;而那些效率释放殆尽的制度依然是当前农业发展中制度供给的主流,这恰恰也就是农地制度产权制度创新的诱致因素。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诠释。一、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非均衡的一般理论解释所谓制度均衡是指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意状态或满足状态,因而无意也无力改变现行制度[1]。在此状态下,现存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的任何主体带来额外的净收益,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从总体上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均势状态,它表现为制度的供给适应制度的需求。所谓制度非均衡就是指人们对现存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不满意或不满足,欲意改变而又尚未改变的状态。[2]在此状态下,现存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任何改变有可能会使不同制度创新主体获得利益,也就是说,现行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之外出现了另一种可获得潜在最大利益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如果不及时创新制度安排,就容易导致制度供给不足或者制度供给过剩,使得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出现了不一致,容易引发制度非均衡。引起制度非均衡的因素很多。从内部矛盾来看,制度创新的潜在收益变化、制度创新的成本变化、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技术改变、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以及其他制度安排改变等因素都会引起制度非均衡。从外部因素看,外部环境的变化、资源条件的改变、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体制的变化等等,一方面会使原有的制度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不是净收益最大的制度,因而产生了制度创新的动机和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会改变可供选择的制度集合和选择范围,从而产生制度的有效供给。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之所以处在非均衡状态,主要表现为农村土地实际产权制度供给滞后于潜在的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对新制度的需求已远远早于实际制度供给,从而导致农地产权制度有效供给不足。例如对界定土地所有权制度的需求、对明晰土地使用权制度的需求、对健全土地流转制度的需求、对规范土地租赁制度的需求等潜在制度需求都早已产生,但实际制度供给至今尚未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另一方面,土地承包制度供给存在着严重“过剩”,一些现行制度供给相对于社会需求是多余的,如农民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农村住宅禁止向城镇居民出售,农民将户口迁入城镇后,其原宅基地不得再扩建和自行转让等政策,都极大束缚了土地和劳动力这两大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阻滞了农地市场化进程。当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度非均衡是一种“常态”,而制度均衡则是一种暂时的、理想的状态,即使“偶尔”出现也不会持续存在,影响制度供求的成千上万各“变量”在不断变化;另一方面,制度非均衡又成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正在不断出现的潜在利润促使人民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制度非均衡的轨迹就是制度变迁的轨迹。二、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内部性分析一是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供给不足。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呈现多元化发展,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应明确确定农地主体。我国宪法虽明确规定了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组织所有,在此规定下,现实的“集体所有”大多数为乡镇、村、村民小组所有,农民只是具有土地的经营权而无所有权。而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对土地充其量除了在农户之间进行调整一类的分配权力之外,并不拥有法律赋予所有权的全部权力。实际上,在我国中央政府代表全社会掌握最高的、宏观的农地支配权,造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或缺位。即使是集体组织享有的那一小部分所有权也缺乏真正的组织载体,使集体很难真正行使自己的所有权。二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供给不足。从经济学的角度,产权对它的拥有者来说,应当具有的权能是: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家庭承包制度虽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农户拥有了承包经营权,但农户的权利并不是充分和完备的,我国农民在土地的所有权上,只有占有权和使用权,而没有处置权和收益权。农民产权权利的不充分使之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变化和要求。例如,在现行制度下,农民缺乏抵押土地使用权以获取银行贷款的权利。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承包经营权又发生分化,演变成承包权与经营权两部分。而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国家通过出让、转让农村土地收益达2万亿元,但大部分农民却没有从中收益。三是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供给不足。我国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国家在1984年就确立土地使用权15年不变。1993年底,国家又确定将原有土地使用权再延长30年,并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同样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但在实践中,家庭承包制基本采取按人平均承包土地的办法,以保障农民平等的经济权利。特别是由于婚丧嫁娶、新生人口不断形成高速承包地的内在压力,不少地方不得不采取“三年小调整”、“五年大调整”的办法,不断重新分配承包地,这使稳定土地承包成为一句空话。土地承包权的不稳定直接导致土地所有权不确定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资,使得土地的粗放经营成为普遍的现象。四是农村土地经营制度供给不足。家庭承包经营在解决了农村温饱问题后,在继续发展上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随着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改革的深入,家庭分散经营表现出制度上的滞后性,一系列困扰农业经济的问题(如规模经营,农民增收,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一体化等问题)难以在封闭、凝固、分散的小生产经营体制框架内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所有这些都使得我国的农业难以像其它产业那样能够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这大大降低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目前我国已经加入了WTO,与其他行业相比,我国农业的比较优势最小,入世对农业的冲击也最大,如何提高我国农业的规模经济效益也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五是土地产权制度结构不完善。我国目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构严重失衡,土地产权制度的配套制度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1)农村用地保护制度缺乏,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在农村,则是擅自建房、建厂、建窑、建坟、采矿、采石、挖砂、取土,乱占滥用,破坏地力,改变用途;(2)农地市场制度发育不良,农地是不是资产,如果是资产,其市场如何建设等都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3)农地价格制度缺乏,现实农地经营中,没有系统的农地地价制度,农地资产显化缺乏依据;(4)农地金融制度尚待时日。农民缺乏利用农地使用权进行贷款的农业金融机制,导致部分缺失资金的农户无法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现代农业生产,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从土地使用权转让中获得资本积累丧失了发展非农产业的机会,种养大户不可能通过市场获得土地相对集中,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此外,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还存在部分供给过剩现象,突出表现在农村土地使用权限的封闭和凝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但在现实中,农地流转尚无相应配套的可供其具体操作的章程,农地转让进退两难:一方面是政府或集体强制性进行农地流转,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统计,1998年至今,全国土地违法案件达80万宗,中国现有失地农民在4000万人以上。[3];另外一方面就是全国许多地方已出现了农民之间无偿或低偿转包、转让土地,有的甚至转出方倒贴,严重违反了稀缺土地资源使用价值规律。此外,国家还规定农村土地流转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抑制了农村土地进入市场的积极性和可能性,束缚了土地和劳动力这两大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把9亿农民全都紧固在自己的承包田和口粮田上,影响了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小城镇的建设步伐。三、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非均衡延的外部成因1、制度创新成本高。制度不均衡产生了获利的机会能否实现制度的供给,还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面临着多种成本与收益的核算。一是个体成本-收益比较。新的农地制度创新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多收益(包括预期收益),例如更高的粮食产量,货币收入,以及股份分红增加等,同时也要为此付出相应的成本代价,譬如农民的土地转让会使转让农民丧失了土地,增加货币收入却丧失了粮食收入,承担的风险增大等。一般说来,只有在收益可能大于成本时,单个行为主体才会产生制度创新的要求从而对由政府设计安排的制度创新持赞同和支持的态度。二是社会成本-收益比较。新的农地制度变革可能会使部分设农、非农社会成员的利益受损,从而成为制度创新的阻碍,进而增加制度创新的机会成本。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土地对农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生产资料,而且承载着过多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职能。农村土地创新有可能使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导致社会不稳定,同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也会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三是政治成本-收益比较。毫无疑问,未来农地产权明晰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取向。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必定会提高资源市场配置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有可能增强政府可支配的经济力量——主要体现为能增加财政收入,从而使权力中心获得更广泛的国内政治支持和加强在国际政治经济谈判中的力量,达到巩固权力之目的。但经济市场化、自由化所诱发的多元化政治力量可能会弱化权力中心的权威性。2、“搭便车”问题。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制诱致性制度变迁本身所具有的外部性容易导致“搭便车”问题,这就意味着一旦制度被创新和安排,每一个受这种制度安排约束的个体,不管他是否分摊了制度创新的成本,他都能得到同样的制度服务。由于这个缘故,经济主体都希望别人分摊制度创新成本,其结果是制度供给不足。这就使得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矛盾表现更为突出。因而,在“搭便车”问题困扰下,制度供给不足的非均衡状态将可能较长时间内持续下去。既然诱致性制度创新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那么国家强制性制度供给是否会弥补制度供给不足吗?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只有在预期收益高于其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时才会提供新制度供给。如果创新损害具体制度提供者集团的利益,它们就不会为制度创新提供服务,甚至会以国家的名义阻碍制度创新的实现,维持一种低效率的制度。“经济增长时会出现制度不均衡。有些制度不均衡可以由诱致性创新来消除。然而,有些制度不均衡将由于私人和社会在收益、费用之间有分歧而继续存在下去。只要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他将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4](P396-397)(3)制度变迁时滞。所谓制度安排的时滞性,是指在新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之间存在一个时间间隔。即新的制度供给要滞后于新的制度需求的出现。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和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所以,适应某一阶段或某一社会情境的制度安排必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失去作用,新的社会情境便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而由于人的认知能力、制度“发明”需要时间及新制度的启动存在时间间隔等因素,新制度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同步调适,因此,制度安排的时滞性是必然的。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于没有重要的社会变革,所以制度的安排会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而展开,时滞性问题表现得不是很明显,而在一个多变的社会如目前我国的转型社会中,由于整个社会结构都需要调整,因此旧有制度明显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新制度的产生和有效施行又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当前我国制度安排中的时滞性便显得更为明显。这一点对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而言,也同样适用。(4)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制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如当科学和技术知识进步时,技术变迁的供给曲线会右移一样,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的商业、计划、法律和社会服务专业的知识进步时,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也会右移。进而言之,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正如自然科学及工程知识的进步降低了技术变迁的成本一样”[50][P336]。这就是说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知识就是认识社会现象的阶梯,并决定着改造社会的成本。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方向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在改革过程中面临的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阐释的是土的地社会所有,而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另一方面,西方有比较成熟的土地产权制度理论和模式,但这些理论和模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个别基础之上的。因此,如何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建立和完善现代土地产权制度并没有现场的模式可供借鉴,只能靠摸索和创新。因而使得制度非均衡的状态得以较长时间延续。(5)意识形态刚性。制度创新是经济主体追求外部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结果。只有当经济主体对一项制度的安排和结构的预期成本少于预期收益时,一项制度安排才会被创新。而经济主体对制度的成本-收益的看法,则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人们是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获得最大化收益的,而意识形态通过改变经济主体的偏好体系,对成本和收益的值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从随机观察中可以发现,个人在成本-收益计算中仅以获得更多的尊严作为利益取向的行为模式是广泛存在的”[6][P60]。我国漫长封建小农社会经济形成的平均主义观念、家族和家庭观念、公私观念等潜移默化的从各个层面影响着农民主体对农地制度创新成本-收益分析。任何违背农民意愿的制度创新方式都不会得到农民支持和理解,也是难以实施的。2004年,因为首创”家庭联产承包制”而常被作为“中国农村符号”的安徽省,对全省15个市、60个县(区)、219个乡(镇)共2070个农户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摸底调查,46.09%的农民对土地产权私有化持反对意见,赞成的只有28.7%,其余农户说“无所谓”或回答“拿不准”。农民认为:“家庭承包制”适合我国的实际,不能动摇[7]。四、结论我国目前非均衡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格局已进入不可持续的状态,由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非均衡而引发的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进步等“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各个土地所有权“上级”以所有者的名义来侵蚀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严重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土地随意的调整以及不得转让、继承、自由种植等限制,造成土地资源不能自由流转、不能形成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弃农务工,使得相当大一部分土地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稀缺的土地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种非均衡的农地产权制度格局已成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进步的“瓶颈”;体现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农地制度,已经成为经济社会中的“稀缺资源”,而在这种非均衡中又恰恰是推动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的需求因素,这也正是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进一步展开和深化的基本条件,其结果必然是加速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力度和频率,实现制度均衡发展。参考文献:[1]张曙光.论制度均衡与制度变迁.经济研究[J],1992,(6)[2]张曙光.论制度均衡与制度变迁.经济研究[J],1992,(6)[3]李兆清.国家重策出击“三农” 农业税赋拟5年降至2.4%,财经时报电子版[N],BUSINESS.SOHU.COM,2004年2月14日[4]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A],载科斯、阿尔钦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5]V8226;W8226;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A].载科斯、阿尔钦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6]诺思(著).陈郁.罗华平(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7]安徽一份调查表明:多数农民不赞成土地私有化.www.xinhuanet.com,2004年12月28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