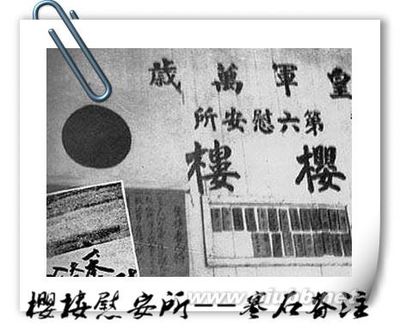“组织意见”、知情权利与档案功能
众所周知,“组织意见”对于中国单位人来说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和不可挑战性,它在评价个人思想品德和工作业绩方面具有“不容置疑”的专断性。在单位中国时代里,人们始终抱有对组织的高度信仰与虔诚,因此造就了“组织叫我干啥就干啥”、“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的信任政治格局。那个年代里,组织关心着个人的一切——衣食住行、吃喝拉撒,连找对象组织也会周密考虑。的确,组织的形象来自于组织的领导者,许多解放初期基层党的领导者“他们从战争中来,有经血与火洗礼过的纯粹和透明,都有很强的党性和原则性,对同志如亲人,没有物欲,没有私心,让人从心底里信得过。那时,心里有什么事尽可以对组织讲,组织会想方设法帮助你,替你排忧解难。”[1]档案是“组织”对我们成长过程的鉴定和评价,“组织”是我们档案及其话语的制造者,而“组织意见”是对我们生命历程中的最具权威的政治话语,它影响着个人的升迁荣辱甚至命运沉浮:有人因为“组织意见”中的“此人可堪重用”而平步青云,有人因为“组织意见”中的“此人不可重用”而终生郁郁不得志。
同为汤国基乡党和前辈的杜高先生就感受到了“组织意见”的无比威力:“在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漫长年月里,它的威力在于迫使我不再是真实的‘我’,而变成一个被政治运动塑造成‘敌人’、‘罪人’”,“它像一个可怖的暗影紧紧地跟随了我二十四年,目睹了我从一个活泼的青年变成衰颓的老人,目睹了我作为一个人的最美好的人生岁月的毁灭。”[2]从中国迄今为止散落民间的一份最完整的个人政治档案中了解到:在1955年5月发动的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肃反运动中,“组织”通过收集和制造各种材料,证明杜高从建国前的十多岁就是一个“反共分子”,建国后和胡风集团一起成为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组织意见”证明为杜高是一个思想反动、道德败坏、生活腐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1958年4月到1969年11月,杜高被囚禁在劳改单位实行强制改造整整十一年零六个月。“组织意见”像是一个无形又无影的紧箍咒,主宰着个人生命的沉浮,而且会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如同影子一样始终缠绕着每一个“组织人”——杜高和汤国基的案例就是明证。
毫无疑问,“组织意见”是组织经过慎重讨论通过的意见、决定和评价。然而,“组织意见”更多的是个别掌握着印章的领导人的意见,表现在档案评语中有时仅仅为一行字或一句话,但往往就是这一行字或一句话决定着一个人的否泰。这种非民主化的主观评定无疑掺杂着组织领导者的个人喜好甚至“恩怨情仇”,你能说它是公正的吗?在毕业鉴定中,由班主任老师对学生下“结论”,在缺乏充分的讨论和沟通的情况下,这种“结论”可靠吗?我们的疑问有三:一是班主任老师对学生的了解到底有多少?二是不经过学生本人的确认,评定能不能符合基本事实?三是对学生的一些负面评价,该不该给学生以申辩的权利?再者,这种“结论”科学吗?实际上,有资格鉴定汤国基“精神反常”的组织是医学组织,准确地讲是精神医学组织,不是教育组织,更不是班主任。
如果“组织意见”加大透明度,向当事人公开、让当事人知情,不搞暗箱操作,那么,正确的“组织意见”确实能以组织纪律教育当事人,并能让当事人弘扬优点、改正错误。而错误的“组织意见”能够公开“商榷”和质询,至少它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那个时候的汤国基是不幸的,连他对学校处分他的决定不仅不“知情”更毋庸说“申辩”了。2005年3月29日,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新《规定》根据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规定,第一次将学生的权利义务引入学生管理规定之中,为学生规定了权利救济机制即申诉程序。学生如对处分决定有异议,可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如对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复查决定仍有异议,可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同时,新《规定》还要求学校处分学生严格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足、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恰当”。如果当时的管理规定向今天的新规定一样表现得更为人性化,如果学校老师表现得更为宽容,如果当初他就能看到自己的档案,并能对导致他坎坷命运的评语提出疑义,使他能有机会以医学鉴定证明自己并非“有时有精神反常现象”,那么这句让他受苦20年的话进入档案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如果毕业鉴定和处分决定能够按照新《规定》要求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足,也许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汤国基档案事件”了。
显然,传统人事档案管理制度的纪律要求“组织意见”和整个人事档案必须是“封闭”的,人事档案的当事人是无权“介入”的。当初实行封闭式的管理模式,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密和安全的需要;二是防止人为地篡改人事档案;三是避免产生纠纷和矛盾。[3]然而,正是这种高度保密性反而降低了人事档案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因为“信息垄断”而使“组织意见”主观随意性增强,因为缺乏认同而使“组织意见”流于形式,因为得不到监督而造成了杜高们刻骨铭心式的“冤假错案”。因而,增强人事档案的相对透明度成为现实的必然选择。除了档案中的一些干部考查材料、群众意见汇总等涉及保密的仍需继续保密之外,有关一般性的评定材料必须对本人开放。因为透明度越大,科学性也就越强,公民个人的权益无端受到损害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如果个人的基本信息有误,个人可以通过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加以更正;如果“组织意见”有出入,个人可以通过事实和证据申请更改。在公共事务管理日益民主和开放的今天,实现人事档案的“阳光化”既是自我了解和社会认知的需要,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要求,同时也是维护公平公正社会准则的保证。此外,实现有条件开放和阳光化操作,更能彰显人事档案的生存价值。
说到底,“组织意见”的公正公开和人事档案的有条件开放是以转换人事档案制度功能为前提的。传统人事档案制度过分侧重于“组织意见”,以组织评价为标杆衡量个人的品行和业绩,对个人形成凝固化的主观性定论,从而导致档案功能的异化。在异化了的档案文本里,“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等阶级斗争话语充斥着组织对个人的定性,没有经过组织介绍或者婚姻资源的组织配置而展开自由恋爱被认定为“思想品德不够端正”;因为对病号没有吃掉的两个窝头产生了“私心”而暴露了“反人民的,个人主义的贪婪本性”,致使杜高遭到了没完没了的批判;[4]对汤国基所形成“个性强,多疑善嫉”的人格诊断和“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的医疗诊断,只能使他屈从于由这种人格评价所主导的命运安排之中。一种片面化的治疗性话语垄断着档案文本,并把每一个单位人作为理疗的对象,从而显现“组织意见”的话语霸权,进而神圣化单位统治的政治符号。由此,由“组织意见”主导的评价功能已经远离了人事档案的原初功能——记录功能,组织评价中的“定性”远比工作业绩中的“定量”重要,直到今天这种荒诞的逻辑仍然在“档案人”身上延续。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管理的失范从一定程度上否定着这种档案功能的错位和紊乱,注重能力和表现的“行动中的事实”已经取代了“字面上的文字”,“双向选择”性的市场就业政策冲击着固化的用人观念,“组织意见”在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上已经不再成为限制个人自由发展的“紧箍咒”了。
实际上,人事档案是个人的信用标志,是个人的信息记录。说实在的,在档案文本里,只须说明一个人的学历、经历,干过哪些工作,有什么样的专长,取得过哪些成绩,对社会有过什么贡献及公开受过什么奖惩等等,就可以了。如今,市场经济下的人才观和价值观颠覆着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所养成的旧有思维:
时代发展到今天,整个用人机制不能再墨守成规了,应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完全按鉴定中的“组织意见”作为用人的标准已不合时宜。当年,一纸“此人是右派”的“组织意见”,曾将50万精英人才埋没地下,22年的悲剧记忆犹新,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惨痛的教训不堪回首。现在早已不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已不再搞政治运动,那些政治评语已失去特有的效应。人才观和价值观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认为很不听话的人,现在表现得非常自觉;过去认为有问题的人,原来十分忠诚老实;计划经济时代认为经常犯错误的人,今天市场经济中表现得成绩斐然非常出色;甚至对一些让人头痛三年两年就跳槽的人,据一位教授告诉我,国外有一些企业家对这类人竟然表示欢迎,因为这类人见多识广,可以将许多国家企业中好的东西带到自己企业中来,只要对企业发展有利,即便三两年再跳槽也无所谓。[5]
[1]黄东成:《且质疑“不容置疑”的“组织意见”》,《太原日报》2004-06-16。
[2] 李辉、杜高:《关于á杜高档案ñ的问答》,《书屋》2001年第4期。1998年,《人民日报》主任记者李辉从北京潘家园市场的地摊上意外淘来一堆旧文件,其中就有杜高的档案。杜高,湖南长沙人,著名戏剧理论家,曾任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杜高档案”成为出版界2004年度热门词汇,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的两本著作《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和《又见昨天——对“杜高档案”的诠释》分别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前者为李辉编著,后者由杜高自己所著。能造成相当的社会反响是因为它记述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历史和杜高个人的悲惨遭遇,同时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所有干部,无论职务高低,能看到自己完整档案的,恐怕绝无仅有了”。参见这方面的介绍文章,刘锡诚:《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死亡档案》,《中华读书报》2004-06-18;罗雪挥:《中国人直面“档案之痛” 民间出现解密档案》,《新闻周刊》2004-09-08;郭慕岳:《“杜高档案”和我经历的往事》,《湘声报》2005-01-28;浣官生:《“杜高档案”和á又见昨天ñ》,《湘声报》2005-04-21等。

[3] 参见王英玮:《信息时代人事档案管理变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内部刊物《档案聚焦》2003年第4期。
[4] 参见罗雪挥:《中国人直面“档案之痛” 民间出现解密档案》,《新闻周刊》2004-09-08。
[5]黄东成:《且质疑“不容置疑”的“组织意见”》,《太原日报》2004-06-16。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