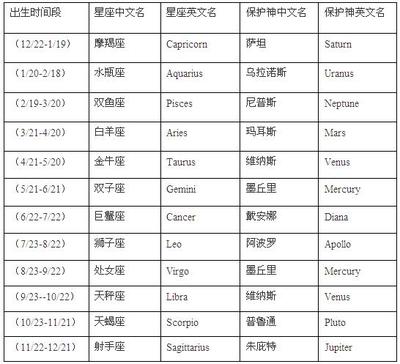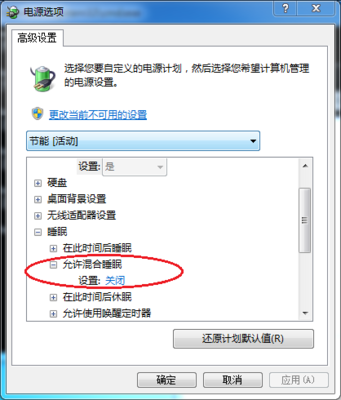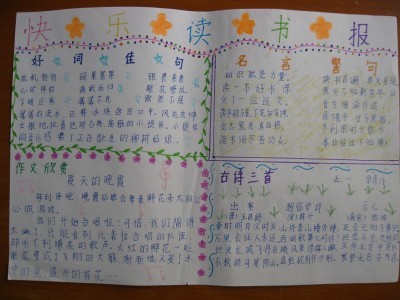1、学界有个说法——回到马克思。即把文本的解读,建立在它的发生学基础之上。以历史本身的时间与空间的结构,让马克思的文本原初语境呈现出来,从而获得一种全新的理解结果。 而目下中国哲学的使命却要求我们:根据中国后现代所面临的历史时空,解决好如何在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之下,按中国的观念方式,开创一种如同马克思哲学初创期具有发生学性质的、活的出场路径:即站在当下历史的高度,在经由资本主义后现代拓展的全球化视域,构划中国的现代性图景。 2、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把人类结合为一个整体,构成全球文化村。而它的‘村民’(所有民族国家)却在运用各自的历史文化和哲学——我心文化——相互对话。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谁拥有综合实力谁就争得话语权。于是,在全球经济秩序的建立上,和在履行国际法、国际公约、国家行为准则的责任和义务上,都可以实行双重标准。于是,人类之间的这种‘对话’,总是具有某种霸权性质和文化冲突的味道。 3、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时间的连续性被打破了,在他们面前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在场。当下不是理性的当下,而是伴随人们突发创意的重组、拼接、折衷与调和。 然而,在宏观上,这种重组、拼接、折衷、调和,一方面受着知识文化的多元性支配(实用知识、形象知识、宗教知识等),另方面受到企业对消费文化在多元素提供能力方面的限制和在社会技术上受到宏观指引能力方面的限制。以至人们无法把技术及其开发的系列产品,看作有人的生命活动媾和其中、有人的社会一般要素凝结其上的功能整体。进而人们无法把经由这类技术拓展的一切可能的知识领域作为整合人类精神的物在摹本。 这个严酷的发展现实警示我们:当人类个体——这个自羽天赋神权的尤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荡涤的体无完肤,当我心和我思被无序的在场性所扰乱,哲学家心灵还会栖息在哪里呢?

4、全球化与边缘化同在,全球经济安全与恐怖主义并行,环境污染、资源匮乏日益对人类生存空间造成更大的挤压,复杂混乱的政治派别、无法扶平的宗教冲突正在形成滋生恐怖主义的新的土壤。。。。这一切的一切,使得大规模杀伤武器和核扩散的历史肇因时隐时现——人类和自然的各种矛盾冲突,愈发受到人类自身固有矛盾的历史束缚! 这就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哲学是否需要重新组装‘哲思’的头脑,是否需要重新确定一条合乎历史本身进程、最能化解从前各种矛盾的人伦界限?!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