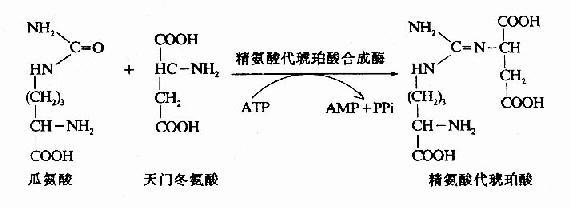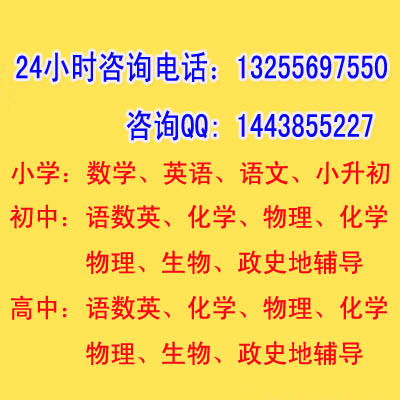福建是近代中国翻译家的故乡。这里有1702年就旅居法国,后来获法国皇家文库中文翻译家称号的译坛先驱黄加略;有“倡西学之始,开新学之路”,最早组织翻译班子译“夷书”的林则徐;有操五国语言,应对如流,让碧眼虬髯者,自惭不及的外交翻译家罗丰禄;有东学西渐第一人陈季同;有译界之王林纾,他译介的西洋小说之多至今无人出其右;有译界楷模严复,一百多年前他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一直影响着中国的译学研究;有掀起凡尔纳热潮的译坛伉俪陈寿彭与薛绍徽,薛绍徽还是中国第一位女翻译家;有学贯中西,被西方人尊为东方文化“圣哲”的辜鸿铭;有“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毕生致力于传播中华文化的文学、翻译大师林语堂;有著名的文学家兼翻译家郑振铎、谢冰心、许地山、杨骚、梁遇春等;有首次把毛泽东的 《论持久战》等多篇著作译成英文的许孟雄教授;有将中国现代散文译成英文的著名翻译家张培基教授,他的两册《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是汉译英的典范,他编写的《英汉翻译教程》至今还在各高校使用;有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东亚语文教授兼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郁正,他的《葵晔集》和《待麟集》是译介中国古典诗词的力作,在西方有广泛的影响;有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翻译家凌青和五、六十年代外交部翻译“五朵金花”之一罗旭;有集作者、学者、译者于一身的文学、翻译大师余光中教授;有《英语世界》的创始人、主编并翻译过福尔摩斯探案等西方名著的陈羽纶;有《中国翻译》原主编、翻译家林煌天先生,他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是介绍翻译的百科全书,为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有《译林》的创始人和主编、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翻译出版家李景端教授,近年他在翻译打假维权方面所做的贡献,译界有口皆碑;有著名普希金翻译家并获得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发的普希金奖章的冯春先生;可谓译才济济,群英荟萃。
福建之所以出这么多翻译家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地缘原因的。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倚山临海,早在汉武帝时期就有海上交通。唐五代时期,福建贸易港兴起,福州、泉州成为当时外贸的主要港口。日本、朝鲜、印度等国的商人和僧人,纷至沓来,成为福建与这些国家沟通的使者。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都在福建逗留,进一步拓展了福建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明中叶以后,福建与日本的海上交通和贸易进一步拓展,沿海人民纷纷到日本经商致富。到明末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入闽,这是殖民主义对中国侵略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福建与西方的交往。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闽活动近一个世纪,紧接着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来到福建。后来福建又通过菲律宾——美洲的海上丝绸之路,与美洲国家建立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参见林金水《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
总之,福建自古以来就有以“海上丝绸之路”为基本途径的对外商贸和文化交流。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翻译的存在,这些交流活动是很难进行的。翻译是国际间沟通的桥梁。鸦片战争以后,福州、厦门成为通商口岸,在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下,造就了福建一批走向世界的先驱,如林则徐、徐继畲、丁拱辰等。林则徐既没有被夷人的船坚炮利所吓倒,也不否认或排斥夷人的先进技术,率先提出学习西方长技的主张。他组织人员翻译和收集外国报刊上的资料,编写《澳门新闻纸》,还把英国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汇编成《四洲志》,较全面、详尽地介绍了30多个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地理概况,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地理著作。曾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畲汇编的《瀛寰志略》是当时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知识水平最高的一部著作。19世纪60年代,这部著作成了中国人了解世界概况的必读书,书中对人名、地名、国名的译法,后来成为总理衙门翻译外文书籍的标准,而且不断被翻刻,传到日本。西方传教士到福建以后,为了传教就必须学习地方方言,因此,福建方言的汉英词典和《圣经》就应运而生。这些都是翻译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通过翻译也使外国人能更好了解福建,进而向世界介绍福建,使福建走向世界。宋元时期,与泉州通商的国家有40余个,通过阿拉伯人将中国的指南针、火药传到国外,今天阿拉伯语中表示罗经方位的kham,就是闽南方言罗针的“针”字。元代马可波罗从泉州出洋,他撰写的《马可波罗行记》中,就有关于福建的相当多的记载。明代朱熹理学在日本传播,以及后来西方传教士通过翻译《四书》将朱熹理学传到西方,都跟翻译有关系。除朱熹理学外,许多闽人著述也被译成西方文字传入西方,如赵汝适的《诸蕃志》、张燮的《东西洋考》、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梁章钜的《浪迹丛谈》、宋慈的《洗冤录》以及冯梦龙的“三言”,都被译成英、法、德、荷、拉丁等各种文字,深受西方读者欢迎。(林金水1997)福建悠久的对外交往历史,频繁的译事活动,为翻译人才的成长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更是福建能涌现出众多翻译家的重要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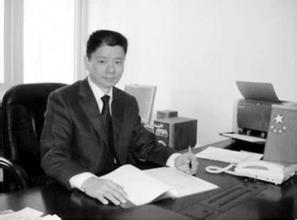
福建之所以能涌现出众多翻译家还得益于闽人较早出国留学。福建最早的留欧学生是莆田人黄加略。他于1702年随巴黎外方传教士抵达伦敦,后往巴黎,不久被派到罗马深造学习。回巴黎后,在皇家文库任职,获法国皇家文库中文翻译家称号。他曾尝试将中国古典小说译成法文,并编撰了《汉语语法》和《汉法词典》,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乾隆时期还有5位福建信徒赴意大利那不勒斯留学,攻读神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1873年12月26日,沈葆帧向朝廷呈上《奏请分遣学生赴英法两国学习造船驶船折》,得到朝廷重视。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批留欧学生35人,于1877年3月31日,12月8日先后赴英、法学习。留学生经过了在大学理论课程学习、兵舰实习与厂房实践,曾随舰至非洲、美国、大西洋、印度洋及地中海等地。陈季同、严复就属于第一批留学生。1881年12月,第二批留学生8名赴英、法、德学习。1886年第三批24名留学生赴英、法学习。1897年第四批留学生14名赴英、法学习,另有10名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同往。此后福建船政学堂陆续派出留学生,截至辛亥革命前,共派送107人。民国时期,海军学校(原福建船政学堂分出来的学校之一)在1929年至1938年先后派出80人留英、日、法、德、意。(岳峰2002)这些留学生是近代中西文化的直接沟通者,他们把中国的风土人情介绍到西方,又把西方的科技、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译介到中国。可以说福建船政学堂是近代中国翻译家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了罗丰禄、严复、陈季同、陈寿彭、马建忠、魏瀚、李荣芳等一大批学贯中西的英才,为中西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福建第一位出国留学的女子是福州人许金訇,她于1883年到美国学医,回国后在福州创办医院救死扶伤并培养医生、护士。随后有谢冰心、林徽因、黄衣青、李君璎等一批勇敢的女子走出国门,到西方和日本留学。她们不仅是近代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女性,而且也是著名的翻译家。1904年,福建留日学生还创设了翻译团体闽学会,组织翻译出版《闽学会丛书》。该会出版的第一部日文译书为《西方东侵史》,其中报道已译刊的书目已有16种,内容多属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例如:《哲学原理》、《国家政府界说》、《国际法精义》、《史学原理》等。已知该会的翻译人员有高凤谦、林长民、林楷青、王学来、萨瑞、林藏文、杨允昌等。(见《中国翻译词典》)如果不是福建比较早对外交往,如果不是有这么多闽人出国留学,福建也不可能产生出这么多的翻译家。仅《中国翻译家辞典》所列四十多位闽籍翻译家中,就有一半以上是在国外学习深造过的。严复、罗丰禄、陈季同、陈寿彭、辜鸿铭、王寿昌、唐钺、许地山、林语堂、郑振铎、谢冰心、杨骚、郑超麟、许孟雄、林同济、黄嘉德、陈彪如、林林、高名凯、林疑今、张培基、罗郁正、余光中等都是早年到欧美、日本留学的。由于他们学贯中西,后来都成为翻译大家。另一方面, 从福建船政学堂到教会学校,授课基本上是用外语,许多闽籍翻译家虽然没有留洋,但由于他们在这些学校里打下了扎实的外文基础,使他们有可能从事翻译工作,并经过自己努力成为优秀的翻译家。
不论是留学还是从事翻译活动,福建翻译家都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黄加略作为中国第一个定居巴黎的留学生引起诸多法国学者的莫大兴趣。1713年10月至12月在黄加略的巴黎寓所,他与孟德斯鸠多次谈论中国的宗教、刑法、服饰、墓葬,家产观念、文学、科举、妇女地位、国家性质等等。孟德斯鸠多次笔录并将对话内容将谈话内容整理成三次记录,最长的长达20页,后均装订成册,定题为“关于中国问题与黄先生的对话”。(岳峰2004)罗丰禄凭借娴熟的外语和杰出的外交才能,进行外交活动,以亲善友好、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准确、得体、敏捷的翻译风格,得到各国领导人的赞赏,为中外交流留下了精彩的一笔。林纾和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开了中国翻译西方小说的先河, 是林纾首次把外国文学名著大量介绍进来,开阔了我国文人的眼界,因而又促进了我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和发展。陈季同用法文写的《中国人自画像》、《中国戏剧》、《中国人的快乐》、《黄衫客传奇》、《中国人笔下的巴黎》与《我的祖国》等,辜鸿铭用英文写的《尊王篇》、《中国人的精神》,以及林语堂用英文写的《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都深受西方读者欢迎,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极好的教科书。许地山、郑振铎、谢冰心都对印度文学深感兴趣,而且与印度文坛泰斗泰戈尔都有深厚的友谊。许地山的专著《印度文学》以及他翻译的印度故事《太阳底下降》、《二十夜问》等;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诗歌以及印度古代寓言,如《飞鸟集》、《新月集》、《印度寓言》等;冰心译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诗剧《暗室之王》、《齐德拉》,书信《孟加拉风光》,小说《喀布尔人》、《弃绝》,印度的穆·拉·安纳德的《石榴女王》,印度萨洛季妮·奈都的诗选;他们为中印文化交流所做的突出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林林、凌青更是长期活跃在外交战线上的翻译家,他们为维护祖国的尊严,为新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立下了汗马功劳。
福建不仅翻译家多,而且译才多样,涵盖各个领域。有林纾、郑振铎、谢冰心、许地山、杨骚、梁遇春、林同济、林疑今、许崇信、余光中、杨仁敬、朱纯深等文学翻译家;有严复、陈衍、严群、陈彪如、陈珪如、黄为葳等哲学、社会科学翻译家;有罗丰禄、凌青、罗旭等外交翻译家;有电影翻译家郑雪来、蓝馥心等;有心理学家兼翻译家唐钺;有儿童文学作家兼翻译家黄衣青,有语言学家兼翻译家高名凯,有科技翻译家,如傅子祯、李君璎、蔡国栋、吴伯泽、吴忠超等;有总编辑、翻译出版家,如陈羽纶、林煌天、李景端等;有日语、西班牙语、俄语等其他语种翻译家,如林林、林光、林煌天、冯春、蔡毅等。福建翻译家不仅在外译中,而且在中译外方面也是硕果累累,充分体现了他们深厚的国学修养和扎实的外文功底,如陈季同、辜鸿铭、林语堂、许孟雄、张培基、罗郁正等,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除了翻译实践外,福建翻译家还在译学理论研究方面也卓有建树,一百多年前,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三字翻译标准,至今还有指导意义。林语堂在一篇近万言的《论翻译》中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从而成为中国翻译史上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学派的代表人物。郑振铎在《译学的三个问题》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翻译观。他首次向中国翻译界介绍了英国翻译学家泰特勒(A.F.Tytler)《论翻译的原则》一书,在分析了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后,他提出翻译应该在“忠实”(信)的前提下,把原文的风格与态度重新表现在译文里,而且“良好的译者应贵得于中道,忠实而不失于流利,流利而不流于放纵。” 冰心在《译书之我见》、《我也谈谈翻译》、《我和外国文学》等数篇短文中站在一个作家、文学家的立场来看待翻译,提出为民译书,为读者着想的翻译观。许崇信教授在分析了前人提出“信达雅”、“形似与神似”、“化境”等翻译标准和方法之后提出了“模仿与创造”的翻译观。张培基教授认为从汉语翻译到英语的工作未必只能由以英语为本族语的人来完成才能表达得地道,许多英文功底好的中国人把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一样可以翻译得很地道。而且他还认为语言问题才是翻译的根本问题。中、英文都能掌握得很好,运用得很好才能事半功倍。他强调学习翻译要多进行翻译实践,以实践为主,而不是整天纠缠于“信、达、雅”,那是本末倒置。凌青对翻译的重要性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从中国来讲,没有翻译工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近代的革命运动,就没有中国成功的对外开放和四个现代化;从世界范围来讲,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和平,就没有各种国际交往,就没有一个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的未来。蔡毅教授的专著《苏联翻译理论》以及他译介的苏联翻译理论,都为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余光中谈翻译》更是集中了余光中教授几十年在翻译教学、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中积累的真知灼见。他在《作者、学者、译者》一文中提出:“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也就是说,译者必定相当饱学,也必定擅于运用语文,并且不止一种,而是两种以上:其一他要能尽窥其妙;其二他要能运用自如。造就一位译者,实非易事, 所以译者虽然满街走,真正够格的译家并不多见。” 以广义来说,余光中认为创作本身也是一种“翻译”,因为“作者要‘翻译’自己的经验成文字”,这经历跟译者“翻译”时的心路历程相仿。不过,作家创作时,须全心捕捉虚无缥缈的感受,将一纵即逝的灵感定型落实,其过程是由“混沌趋向明确,由芜杂趋向清纯”,换句话说,创作式的“翻译”可说是无中生有,化虚为实;而译者的“翻译”,却早已有范本在侧,任凭一己才情卓越,也无法如天马行空,恣意发挥。“不过,译者动心运笔之际,也不无与创作相通之处。”因为译者在原文的理解与译文的表达之间,在取舍辞藻、斟酌句序之际,还有极大的空间,足以调度驱遣,善加选择。因此,翻译与创作,在某一层意义上,是息息相关,彼此相通的。正因为如此,余光中认为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金圣华1999)朱纯深认为中国翻译研究中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以历史观点看,中国翻译成一开放而非封闭的体系。当今世界,作为一个学科,与领域内其它体系互动,可以更有效地发展其理论个性。他提出不能将语言文化间的不同之处看作是互动的障碍,或者是对所声称的中国翻译独一无二的特色的支持。超国界的中文翻译研究过去是,将来也永远会是全球翻译研究大系的一部分。因此,他主张要下功夫强化中国翻译的哲学基础,扩大其研究视野,改善其研究方法,以利于国际间的互动。(岳峰2002)从严复开始,闽籍翻译家薪火相传,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为中国译学理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资源。
闽籍译家不仅在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硕果累累,而且十分重视翻译职业道德。他们在恪守译德方面的风范,更是一项值得传承的珍贵传统。“严复所译的书都是他精心研究过的。凡与原书有关系的著作,他都涉猎过。因此他在所译作品的按语中能够旁征博引,详明解说。”(马祖毅1984)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一名之立,旬月蜘躇。” 这种认真的态度,决不胡译乱译的严谨作风,仍然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冰心的翻译宗旨自然地反映了她认真、严谨的翻译态度。冰心在翻译中处处为读者着想,对自己负责、对译文及原著者负责。她在《译书之我见》中说:“译者对于难字最好能因时制宜,参看上下文取那最相近的字眼……若是嫌其词不达意,尽可用括号将原字圈起来,附在下面,以备参考。”除了认真地推敲译文中的每一个词语外,冰心还经常会在翻译每一篇作品之前为译本写一篇前记或后记之类的简介性文章。这些短文使读者更容易了解作者写作的意图,也充分地体现了她认真、严谨的翻译态度。此外,在转译的问题上,冰心一向都很谨慎,她声明她尽可能避免转译,因为“怕转译万一有误,在把误译的译了出来,就太对不起原作者了。”所以她译的作品几乎都是原作家用英文写的。余光中虽然一再谦称翻译只是自己“写作之馀的别业”,但是他从事“别业”的态度却是十分认真与审慎的。翻译,在这位文坛巨子的心目当中,绝非微不足道的小技,而是传播文化的大道。在写于一九八五年的《翻译乃大道》一文中,余先生曾经剖白过:“我这一生对翻译的态度,是认真追求,而非逢场作戏。迄今我已译过十本书……。其实,我的‘译绩’也不限于那十本书,因为在我的论文里,每逢引用英文的译文,几乎都是自己动手来译。”由此可见,翻译之于余光中,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工作,全神贯注的经营。(金升华1999)李景端教授曾先后在报刊发表《外国文学出版要治散治滥》、《翻译也要打假》、《呼唤职业翻译家》、《透视劣质翻译症结》等20多篇文章,呼吁重视翻译工作,改进翻译教学,加强翻译出版管理,规范翻译市场, 同时针对翻译质量下降的现状,协助《光明日报》,组织以“构建与世界通道”为题的翻译质量系列讨论。他公开批评翻译中的抄袭、剽窃、盗版等侵权现象,大力呼唤重视翻译职业道德建设。目前,他正筹划发起制订《翻译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实施要求》,争取报批后成为行业的道德规范。闽籍翻译家的译作中有许多精品,这不仅和他们深厚的中外文功底有关,而且和他们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有关。他们的高尚译德和敬业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一百多年来闽籍翻译家不仅为开启民智,振兴中华,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译学理论的建设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今天回顾他们的生平译事,弘扬他们的高尚译德和敬业精神,对于促使翻译事业与时俱进,激发闽籍人士对乡梓及祖国的热爱,促进福建乃至国家的对外开放,增进中外交流,以及加强译学建设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