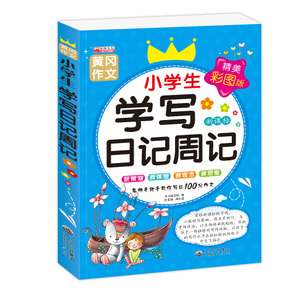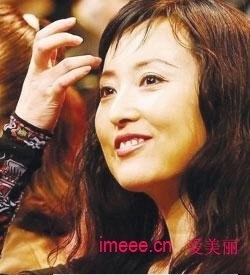关于对话的平等与自由
——评郎咸平的“蝴蝶效应”顾自安(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361005)交流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典型标志。对话则是人类社会交流的的重要载体形式之一。历史发展的进程明确显示了:不同阶段,交流方式和手段的改变,都与群体地位、权力和阶级等级结构直接相关。自从人类伦理学进入以平等、自由、博爱为主题的时代以来,平等和自由就开始被当作人权的重要内容。关于对话的平等和自由问题,群体心理学给予了探索性的研究。对话从形式上来讲是对话双方的一种思想交流,从内容上来讲,则是对话双方关于某一具体问题的探讨,并含有试图达成共识和互相说服的目的。群体心理学用“暗示”、“影响”和“催眠”等范畴来概括交流的主要特征。尽管存在学科领域上的隔阂,但这并不绝对的影响我们对交流和对话的理解。在对话中,我们和他人交谈的目的可以是为了让对方感兴趣和使对方感受交流的愉悦,但这往往是出于交谈本身的乐趣;也可以是出于一种明显的目的,这种动机多半会超出对方的愉悦之外。前者如朋友或是亲人之间的交流,后者则如政治外交、军事、商务谈判或者合法的盘查以及学术争论。我在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是后者。就对话本身而言,必然存在两个相互对立的主体,而这两个主体在权力和地位以及话语权上必须是平等的,在对话内容上必须是自由开放,的。否则并不符合“对话”的基本规则。如果我这样概括还不够明确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对话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以下两点:第一是主体平等原则;第二是言论自由原则。主体平等在对话中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一直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紧密相关。这一点自从人本主义复兴以来,甚至在今天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对话的主体除了个人之间,其形式的多样性和目前社会主体的多样化有直接关系。主要包括国家之间的对话、政党之间的对话、组织之间的对话、或者社会关系中对立的两极之间的对话,也包括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对话。后者较多的反映的是群体中的个人自由和平等问题。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动物,都不可避免的隶属于某个群体。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我们既是一个分子,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前者在本质上要求平等,而后者在本质上要求自由。群体的意志和个体意志之间的协调和冲突,从实质上讲是社会关系的真正内涵。按照霍布斯的观点,群体的产生源自于在丛林中的生存需要,于是人们达成契约,将至高无上的权力授予君主,而面对群体的个体选择服从。现代政治哲学大师罗尔斯则将处于自然状态的个体的人置于无知之幕的背后,论证了权力的必要性和公平与正义的基本伦理原则。在我看来,罗尔斯和霍布斯在主体平等的问题上并不存在分歧,只是在主体平等的实现方式上意见相左。既然在主体平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我们重新回到对话的问题上来。对话的平等存在形式平等和实质两种。形式上的平等极为容易实现,只要双方可以面对,形式平等的对话就可以展开,但实质平等的对话则远非如此。实质平等的对话需要明确的平等原则给予保护,否则平等的对话必然是一种形式化的结果。形式平等的对话既无实质的内容,也不是理想的对话结果,一切都取决于对话中在实质上拥有话语权和决定权的一方。由此我认为,确保平等对话的前提在于以下两点:第一话语权的平等,其实质就是实际的言论自由;第二确保除主体平等自由权力之外的一切权力不得干涉对话。唯此,对话的平等和自由才可以获得保障。在今天的中国,对话平等和自由的问题严重到何种地步,很难准确概括。但我们几乎习以为常,甚至有些无动于衷的一些常见的情景,让我无法回避这个话题。我们不妨浏览一下这样一副“幻灯片”:全国各地方政府门前静坐的群众;报纸上频频报出的各地遣返的进京告“御状”,上访的农民;因为土地被征用而跳楼自杀的失地农民;外出打工却无法获得应付工资的民工;那些怀抱着因为喝了毒奶粉而脑袋畸形的婴儿,却求告无门的母亲们………这一幕幕在今天的中国有些太平常了。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是社会主义的光荣的公民,可是面对政府他们都在企求,眼神里除了企盼连愤怒都丝毫难以察觉。他们是顺从的,他们也都曾经是,而且仍然是社会主义信仰者群体中的成员,可是他们除了顺从和企盼之外并没有实质的行使他们的平等的对话权力(尽管这些自社会主义之初就被写入了宪法)。进入我们视野的“对话”却是:大批的农民带着被子和褥子,抱着孩子,跪在政府门口,而他们却经常被武装警察或是进出政府大院的各类高级小轿车驱散,然后又重新跪下……这是对话吗?恐怕连形式平等的对话都算不上!平等的对话首先要求主体在人格和尊严上的平等,其次才是话语权的平等,而这些他们从来没有使用过。在太多的中国人眼里,尤其是那些朴实的农民眼里,舆论所宣传的“公仆”和官老爷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是得罪不起的。目前全国各地积压的各类“民告官”案件,案件一拖再拖,久久不能宣判,迟迟无法执行实在让人无法相信这些事实可以推翻我的观点。如果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和争论来看,问题同样存在。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最近经济学界正在针对香港公司财务专家郎咸平教授指责TCL、海尔和格林柯尔三家国内知名企业在改制中有“侵吞或稀释国有资产”的事情争论不休。在我看来,郎咸平的观点所引起的争论多少有些“蝴蝶效应”。国企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难题,但至少在是否要改的问题上理论界并不存在争论。大家有一个一致的声音:必须改。但是如何改是分歧的直接的根源和焦点。郎咸平的指责和置疑,是基于他领导研究的对三家公司财务的研究报告。尽管报告中有些言词从学术角度判断缺乏严谨,其推测性的结论也更接近和符合关心国有资产改革问题的民众心声,支持率较高。但国内以张维迎、周其仁、赵晓等人为代表的反对派,纷纷就朗文发表评论和批评,一场关于国企改革中国资流失的争论由此展开。严格的说,这次争论只能界定为一次学术争论,本质上应该是对学术观点的交流和探讨。蹊跷的是争论中反对者多半似乎都有些“顾左右而言他”的迹象。如赵晓在一篇题为《不要冒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情绪——兼评郎咸平国企改革言论》的针对性文章中指责郎咸平时,明确指出了一个“谁有发言权”的问题;此后不久,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也在《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关于“说话资格”和“背后的目的”的问题。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在发表于《外滩画报》上的《学术的边界》一文中也指出:“如果是纯粹出于学术的目的的话,那么研究的方式和论文的表达方式就应该是不包含价值判断的,在涉及一些具体的被研究对象时,也应谨慎处理,如不使用公司的真名等。”看似争论,在本文中应该列为“学术对话”,但似乎名不副实。以上争论并不是就观点和内容本身,而是更多的纠缠于郎教授的行为。我本人同样是研究经济学的,但我无意在这里去趟这趟混水。我只是想谈谈关于对话的平等与自由问题。郎咸平有无发言权呢?这一点根本就无需指出,赵晓的文章发表不久就在网上遭到围攻的结果,不难看出答案。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和从事公司财务问题研究的学者,郎咸平的发言权首先是不容置疑的。我们都无需惶论什么学术职责和学者良知甚至社会正义感了。从对话本身来看,引起对话者和加入对话者之间,后者根本就不可能去怀疑前者的发言资格问题。无疑后者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点,就是“我才是更应该就此发表观点的人,而不是引起对话的人。”这种看法其实刚一入场就“犯规”了。后面的对话又如何在平等和自由的的原则下进行呢?其次,郎咸平关于讨论国有企业改革的“资格问题”和“背后目的”的问题同样不是周其仁教授个人可以或是有资格置疑的一个问题。从他的文章题目《我为什么回应郎咸平?》可看出,他显然没有打算就观点上正面进行对话,而是试图就“回应”行为本身的原因做一个解释。从对话的实质来看,这只是一个附加的注释性的说明,并不是对话的正式内容,即使在文章中涉及了问题本身,那也只能算作评论甚至是先入为主的观点,而非争论或是探讨。再次,从对话的目的来看,根据行为心理学的解释是指:“让某人参与到交流中来,就意味着控制他的注意力并对他的思想施加影响,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渗透。”(《群氓的时代》,【法】赛奇·莫斯科维奇,2002,P239)周教授在文章中指责郎咸平教授的“背后目的”显然有些妄测之嫌了。何况就如张维迎在《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一文中所言:“不要动辄说这个学者有“良知”,那个学者没有“良知”,因为这样只会扼杀科学的学术争论,而无助于社会的进步。可能你们认为有良知的人正是最缺乏良知的人。中国有那么多的学者20多年来冒着政治风险探索改革的道路,献计献策,怎么能说他们都是没有良知呢?真正的良知不在于批评谁,而是批评的是否有道理,是否对社会有一颗善良的心。”如果周教授不反对张维迎的观点,那么是否可以推论他在怀疑郎咸平教授的人品问题了?这让我突然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过的一个词语“坏心恶意”,当然我是有些浮想联翩了。总体来看,我隐约觉得这次的所谓争论甚至有些“战风车”的嫌疑。自郎咸平的文章和言论公开(8月6日)以来,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随之而来,相比与此前国内就国企改革和国资流失问题的争论,这次郎咸平引发的争论不亚于一次“蝴蝶效应”。争论开始不久(8月28日),国内就有一位关心国企改革问题的邵振伟先生,出于对国有资产流失的痛惜和义愤,发起组织了一场经济学家集体回应郎咸平的学术研讨会。郎咸平事先与主办方谈了条件,那就是必须邀请国内各个门派的经济学家,尤其是骂过他或者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尽管此举有些要“华山论剑”的感觉,但被邀的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林毅夫、茅于轼等学者缺席,研讨会实际变成为由左大培、杨帆、韩德强、杨斌等人“一边倒”的郎咸平声援会,仅张文魁一人孤军奋战,他在题为《中国是否应该停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演讲中强调,国企改革势在必行,而国有资产的流失可以防止。(李健,2004)我本人不太理解目前国内经济学界的此类现象,既然是学术对话,何以只是借助媒体造势,而回避直接对话和交流的机会呢?如果所争论的问题,真的是个学术问题,为什么就不可以面对面的争论,而要回避呢?难道很多专家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就是彼此回避,息事宁人,借助媒体互相批评?那么郎咸平指出的问题不是学术问题吗?我想这个问题更不必要回答。国企改革在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位置、重要性和影响本来就是转型时期经济学界亟待研究的紧迫课题。那么为什么无法就问题本身进行争论或是正面的对话呢?我以为,主要的原因是:一、此类问题的开放性争论,实在难有是非对错之分,既使如郎咸平指出的“侵吞和稀释国有资产”的罪名,在法律上也很难确定。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国并没有正式通过具有法律权威的《国有企业改革法》,自然国企改革中何种方式是侵吞国有资产尚且是个无法界定的行为。二、关于我国国企改革中“国退民进”的观点并非官方正式的表述,争论可能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转化为如何实现民营或是私有化的问题,而这是涉及改革方向的问题。总体来讲,学界基本认同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观点,此观点也为政府接纳,但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研究,究其实质来看无非就是股份化和私有化,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股份制其实也是一种“公有制”。邵振伟先生对他组织的学术“交流会”必然有些意外。国内持反对意见的经济学家所采取的态度多少似乎让人有些失望。我想这种失望不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一种好事者的遗憾,我觉得在中国有太多的人希望这些影响政府决策的专家和学者们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解释和说明,然而对话的平等和自由显然在目前仍然是个很大的问题。熟悉经济学朋友大概对几年前张曙光与何清莲引起的争论不会没有印象。何清莲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以大量的事实记录了我国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以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振臂疾呼。然而何清莲女士的著作和观点却引来了张曙光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以“正统经济学家”自居者的批评。本人无意在这里评价二者争论中的谁是谁非。这里仅就争论本身所反映出的关于“对话的平等与自由”问题做一分析,因为我并不具有评论谁是经济学家或者谁不是经济学家的资格。张曙光教授在《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一文对何清莲的批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著作本身。“《陷阱》是一本什么样的著作?笔者认为,是一本大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从大众读物来看,作者针对当前时弊和大家关注的问题,搜集了大量报刊资料,加以系统的归纳,再加上比较流畅的文笔,的确是一本不错的东西。这也是该书畅销的一个原因。但是作为学术著作,严格来说,不要说不够格,可以说还没有入门。这也许是学界(包括经济学界和其他学界)不愿理采的原因,笔者开始不想涉及就是这样。”“《陷阱》的基本写法是,列举一大堆资料和案例,然后下一个简单的概括性断语,再加以情绪化的宣染,仅此而已。其所使用的概念不是学术概念,如什么“光环市场”和“环上市场”及其所作的简单运算(第65页);其分析也不符合学术规范,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前进,没有什么深度,也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信息量。就是其从报刊上引用和自己计算的数据,也有很多是错误的,只要觉得它合自己的口味,而根本没有想一想,它是否符合实际。”二是何清莲本人。“象李实教授这样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功底非常扎实,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又相当熟练的经济学家在国内的确不多,且又长期从事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与之合作的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对其研究和著述的水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但在何女士的眼里却是一堆垃圾,粪土不如。写到这里,像何女士这样狂妄、自负、自不量力之人,笔者实在少见。”“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何女士在《陷阱》中引用了很多文献,在发表的文章中也是如此,但在很多地方是曲解的,与文献的原意是相反的。”“为了抬高自己,作者及其拥护者对整个经济学界大加贬斥,如认为“整个中国当代经济学的活动,基本上是一种“屠龙术”的表演”。”(以上文字引自天则所内部文稿资料《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张曙光教授在《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一文中,在评价何清莲著作与何本人的同时,论述了学术批评应有的规则,严格来说学术批评的规则与对话的规则并无本质差别,其特殊性就在于对话的内容是就学术问题本身的争论,是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然而我之所以在上文中大量罗列了张教授文章的许多文字,只是希望读者来判断其是否符合交往理性。张教授甚至在文章末尾明确指出:“学者要有独立的人格,在相互的交往中,要实而不虚,卑而不亢,要恪守两条基本规则:一是对亲近者要少一点吹捧,多一点批评,对疏远者要多一些尊重,少一点轻视。”但从他的用词和语言本身来看,实在看不出对何的尊重,当然此类带有人身攻击性的语言在张教授而言或许也是“交往理性”和“学术良知”使然吧。平衡起见,我们看看何清莲在《什么是真正的批评规则——对张曙光先生《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一文有关事实的澄清与回答》一文中是否遵循了对话本身的基本规则。在这篇回应文章中,何清莲女士主要就张曙光教授文章中的诸多用语进行了逐个的解释和澄清,但澄清中不乏一些让读者读来觉得“热闹”的言词。当然事出有因,本人申明:在此仅借其语言来说明“对话的平等与自由”问题。当然,作为一篇就某事进行澄清和说明的文章,何清莲女士在文章中做出详细的说明是道理也是有必要的。“我在一九九八年三月份就已听到传闻:张曙光先生要发表一篇对我进行摧毁性打击的批评文章。”此处相比于张文所述何清莲在北京风入松书店对某社会学家的反驳以及在香港评价李实的研究,多少都有些以讹传讹之嫌。“以张先生堂堂经济学研究员兼“博导”身份,想来应该能够区分出批评某种改革举措的实际后果及治学风气与批评经济学家的能力及人格是两回事。在此还请张先生从我的任何文章中挑出“冒牌货”与“低能儿”两个词,哪怕不是形容经济学家的也行。”“当然张先生也可以再次凭借中国经济学界权威的身份(这一身份在他的文章中用语言表达得非常明显)断言世界上关于社会公正只有一种解释,否则就是“变戏法”。”此类给对方定位的推测,在张与何的文章中都有和很多。“张先生义愤填膺地指责我的地方当然不止上述几处,他那巨笔扫荡之处,还有秦晖与姚新勇先生,以及“《陷阱》及其拥护者”们,最后他以中国经济学界(包括其他学界)权威的身份与不容置疑的口气判定陷阱“作为学术著作,严格说来,不要说不够格,可以说还没入门。这也许是经济学界(包括其他学界)不愿理睬的原因,笔者开始不想涉及就是这样。”写这话的时候,张先生仿佛他是“中国经济学家资格兼学术著作资格认定委员会”现任主席,我正在战战兢兢在等待主席大人进行资格认定。这点倒没什么争辩的必要,因为实际上张先生只不过是上百万中外读者中的一位,而且也不是众多读者中惟一的学者,他的意见固然重要,但也并不一定是一言九鼎的意见。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张先生具有的“经济学家认定资格”的资格从何而来,至今也没见张先生在这篇文章的三个版本中讲明其合法性来源。”“张先生自居为“掌门人”的“过渡经济学派”从他们那个角度对中国经济审视以后,认为效率至上,腐败有利于促进社会转轨,不能提倡“公正至上,效率自在其中”,你就不能根据经验现象来谈反腐败,一谈就是没有“经济学的纯粹性”,你的经济学著作就连学术的门都没入,经济学家资格也就被他们立马取消。”“另一处让人费解之处是,张先生提出“清除知识界内的宗派与山头”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又该由谁来承担?难道是天降大任于以张先生为“掌门人”的“过渡经济学派”?我远处南国,至今连职业都是记者,没能力找到钱为自己成立一个研究中心,也没有能力负责一个由自己话事的杂志,也没有体制内给我的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荣耀,我的“山头”在哪里?所以张先生即便要“替天行道”铲平宗派与山头,也无法找到发“铲平功”的对象。但如张先生认为我个人即“山头”,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么张先生现在正在进行这项“一统江湖”的千秋伟业,只管继续努力就是。”“呜呼,人与人的不平等到了这一步,夫复何言!张先生给人家定规矩,但往往将自己置于“规则”之上,其行为往往破坏他自己为经济学界(包括学术界)辛辛苦苦立的“规则”。仔细看来,他批评的那些行为怎样看都像张先生行为方式的自我写照。写至此,不自主地想起金庸先生小说中那些以“名门正派”自居者为诛除异己不遗余力的情节,方悟出金庸先生小说的魅力在于写的虽是武侠世界,但其实却画出了一幅鲜活的人间图景。”“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心生恐惧:是什么力量驱使张先生为了诛杀异己而不惜臆造历史?”……(以上文字引自何清莲《什么是批评规则?》一文,原文发表于《书屋》2000年第一期)我之所以在此详细罗列了大量何清莲回应张曙光教授的文字,目的仅仅是希望读者可以通过对比,去发现在这次特定的对话中,张、何二人是进行“对话”的。我们不会相信张曙光教授与何清莲女士在私下里还会在学术上彼此以良师益友相待。张文中的大量用语和某些所谓真实的“事件”在何清莲那里都是捏造的事实,我估计读者同样难以判断何清莲女士澄清的事实是否就是真相,但结果却是:再无争论的必要。何著《现代化的陷阱》是否是学术著作,我想自会有公论,张曙光教授的文章中的观点以及他认为“学界”对何著的态度多少让人觉得对何是不公正的。何况这种“以己代人”和“代言学界”的做法本身就是很不严谨的。何清莲在她的回应文章中用词激昂以及言词中流露出的那种反抗和拒绝是一种对话精神的真实反映。真正的交流是拒绝权威的。张曙光教授关于何清莲著作的评价几次版本的修改,显然是在对话方式上向对话规则的接近,包括此后张教授对何的《什么是批评规则》一文的沉默也说明:如果对话在主题上不是统一的,或者对话双方彼此不是平等的看待对方,并给对方以足够的尊重的话,那么对话是难以进行的,相反取而代之的则是对话主题之外的相互攻击和指责。两次学术争论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平等的话语权对于学术争论是必要的前提,相反绝对权力和地位则是平等对话的死敌。轻视每一个对话者本身就已经破坏了对话的基本规则。关于学术交流,加尔布雷思在《不确定的年代》一书里说过一句:有一万个经济学家就有一万种经济学,学术生态的多样性决定了学术争论从来不可避免,更何况中国现在已进入了价值多元化社会。容忍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学术研究存在,尊重对方的学术研究成果,本来就是在学术界生存的基本常识。我们已经太习惯活在领袖和权威的环境中了,以至于在转向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个人主义复活的阶段,我们都保持着崇拜权威和恐惧领袖的惯性。在科技进步决定时代发展的今天,平等的学术对话和自由的学术讨论对于我们实在太重要的了,或许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听听那些不同的声音,那些非权威和非官方的声音,并试着去尊重它们,去呵护和鼓励它们,并且正确的引导它们……记得北大的孔庆东曾经说过一句话:“虽然‘我们认为’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认为’的年代却远没有到来……”但是我想,这个时代距离我们应该不远了。参考文献:【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电子版,来自www.eshunet.com。【法】赛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版。郎咸平:《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复旦大学中美财经媒体高级研修班毕业典礼发言稿。张军:《学术的边界》,载《外滩画报》,2004年8月23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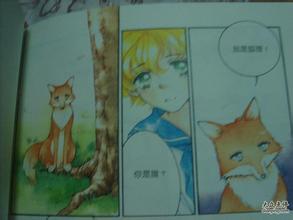
张维迎在《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载《经济观察报》,2004年8月24日。赵晓:《不要冒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情绪——兼评郎咸平国企改革言论》,中国金融网www.zgjrw.com。2004年8月26日。周其仁:《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载《经济观察报》,2004年9月13日。李健:《是是非非郎咸平》,原文见:经济学俱乐部www.jingjixue.com。李健:《就周其仁、张维迎发言如是说》,原文见:经济学俱乐部www.jingjixue.com。 何清莲:《什么是真正的批评规则——对张曙光先生《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一文有关事实的澄清与回答》,载《书屋》,2000年第1期。张曙光:《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天则所内部文稿。张曙光:《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载《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9月10日。张曙光:《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载《读书》2000年第3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