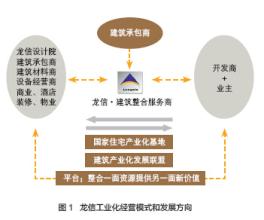马克思曾经说过,“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农业收成的分割在农村社会具有根本性的建构意义,甚至是农村中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根本特征。[16]农民与国家的联系主要是纳税关系。从2002年国家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到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我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由“汲取”到“给予”的本质性改变。税费改革规范了乡村两级的征税行为,堵住了基层政府向农民乱收费的口子,免除农业税则让农民告别了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我国正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它标志着以农业税为主要支撑的农业财政时代的终结,国家进入到一个主要由工商业为支撑的公共财政时代。[17]
农村税费改革引起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重新调整,乡镇财政体制步入向公共财政转型的过渡时期。这种调整对乡镇财政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乡镇财政开始呈现“空壳化”的形式,转移支付的相当一部分变成了“养廉银”来保障基层官员的工资发放,从而防止聚敛和农民负担的反弹,[18]二是农村税费改革通过规范乡镇财政的预算管理,以及国家对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和加强,乡镇财政被完全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体系之中,乡镇政府因此而整合到国家的政治体系之中,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元件”。税费改革前,乡镇财政收入主要由国家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和乡镇自筹资金三部分组成。乡镇财政在税费改革之前就难保收支平衡,其收支缺口主要依赖预算外收入和自筹资金弥补。过去的乱集资、乱摊派和乱收费主要发生在预算外和自筹资金部分,由于其非规范性,一些研究者称其为“非正规收入”、“制度外收入”、“非预算收入”等。农村税费改革将国家政策内的收费并入农业税收之中合并征收,将乡镇的非预算收入、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原由乡统筹费开支的乡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及乡村道路支出等纳入预算管理。乡镇财政收支的规范化堵住了乡镇财政制度外收入,也给乡镇财政套上了“紧箍咒”,乡镇财政尤其是农业型乡镇的增收空间非常有限,基本上没有任何合法性增收途径——这就意味着乡镇财政体制外的部分自主性的也完全丧失,乡镇财政呈现收入“空壳化”与结构模式化的特点,基层政府由过去自保型的“吃饭财政”转化为无能自保的“讨饭财政”。
在规范化财政的约束下,乡镇政府为了缓解“空壳化”的财政压力,就只能仰赖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和上级财政的资金支付,乡镇财政体制由过去主要依赖制度外收入的非规范型财政蜕化为完全依赖上级转移支付的依附型财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乡镇财政自主性的丧失导致了乡镇行政自主性“迷失”,乡镇政府行为模式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特点。

其一,在财政上对国家和上级政府资金的过度依赖,使乡镇政府形式进一步“官僚化”,基层组织被完全统合到国家官僚体系之中,成为名符其实的“守夜人”和“敲钟者”。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政府由于存在制度外财政,至少具有体制外的部分自主性。这种自主性虽然是乡镇政权赢利化、加重农民负担的导火索,但在执政过程中,基层政权也不得不顾及农民的需求和感受,也会根据农民的偏好适当举办一些乡村公益事业,在扮演赢利型经纪人的同时也扮演起保护型经纪人。这种“中介”角色,对于缓解、调节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非税收入的取消和乡镇财政的“空壳化”,过去由乡镇承担的许多公共服务职能正在上移到县级政府,政府权力和职能进一步“虚置化”。乡镇对上级资金的依附性生存,使乡镇政府行动价值取向发生了由过去的上下兼顾到“两眼向上”的转化。中央及省市财政支农的资金有相当大的比重是以项目的形式下达的,由于制度的不完善,这些项目资金在分配上有很大的弹性空间,这使得基层政府越来越重视“跑项目”,越来越注重主宰着他们生存资源的上级政府的政治偏好,甚至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也会做出违背农民意愿和偏好的各种“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马路工程”来刻意迎合上级意图。由于农民不再成为乡镇财政的主要来源,乡镇与农民的关系由过去与农民面对面的治理形式,变为与农民关系更为松散的“悬浮型”。[19]乡镇职能形式化为韦伯说的“自动售货机”角色,上级政府投入硬币(政治偏好),基层政府自动输出货物(政府行为)。
其二,由于上级转移支付收入难以平衡基层政府刚性支出缺口,乡镇政府普遍陷入了生存困境之中,乡镇权力运行机制表现出一种“保障干部团体生存安全”的“生存伦理”②——生存而不是发展——构成了乡镇政府的行动逻辑。一是“借债生存”。在不能把手伸进农民口袋的情况下,要保证乡镇政府的正常运转,办法之一就是借钱。私人企业、民间的富人和富裕阶层越来越成为乡村两级政府组织所依赖的对象。第二种生存之道是“盘活资产”,变卖乡镇政府的固定资产或者一次性出让固定资产的承包权,变卖倒闭的乡镇企业的厂房、土地,出卖山林经营权、水电站、水库的承包权等等不一而足,处理公有资产往往是“能变卖的不出租,能出租的不入股”的竭泽而渔方式,有的把租金都收到了几十年以后,把后届政府的资源都提前透支完了。基层政府由过去要钱、要粮、要命的“三要政府”,变成跑借贷、跑项目、跑变卖的“三跑政府”。
由此可见,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规范乡镇财政管理的同时,产生的一个意外后果是乡镇政府行为的“迷失”。丧失财政自主性的乡镇政府蜕变为一种依附型政权,一方面,对上级资金的仰赖使其越来越依附于“上位”的国家,另一方面,借债运转的生存伦理使其越来越依附于“下位”的乡村富人阶层。这种“双向依附”改变了基层政权的运作基础,基层组织与作为乡村社会主体的普通农民之间的关系出现“断裂”。这种“断裂”的严重后果之一是,破坏了缔造乡村基层组织合法性权威的“权力文化网络”,消解基层政权政的治整合能力和乡村社会治理的权威基础,基层组织面临“政权软化”的政治危机。
财政是政府存在和运作的物质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财政不仅是经济范畴,也是政治范畴;财政制度不仅是经济制度,也是政治制度。财政压力是国家推动改革的直接原因,财政体制的变迁直接推动了基层政府行为模式和角色的转化。在乡镇政权每一次“角色换幕”的背后,我们几乎都能从财政体制的“蛛丝马迹”中寻找到问题的答案。从乡镇政权的成长历程来看,它的设置基于国家意志的需要而得以确立,是国家改造乡村社会的工具,同时能得以依靠乡村社会中的经济与社会资源而维持正常的运转。但是在另一方面,自设立之时开始,乡镇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自我利益倾向的行动主体,并会围绕自我利益展开行动,当作为国家工具失去自主运作空间,或者社会资源不足时,它就会在制度之外寻找生存空间与资源,这构成了乡镇角色变迁的财政逻辑。
农村税费改革与农业税的取消使中国乡村社会进入了“后农业税时代”,也将乡镇政府推向了改革的风口浪尖。当前学术界为乡镇改革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但无论那种改革方案,都无法回避“人往哪里去、钱往哪里来”的问题,换句话说,乡镇改革的问题最终必然要还原到财政问题上来。任何一级政权的运作都离不开财政资源的消耗。税费改革通过取消税费和加强政府间转移支付来实现基层政府财政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力图将国家—农民的“汲取型”关系转变为一种“服务型”关系。但基层政府由于财政自主性缺失和“生存伦理”所导致的依附性质,事实上已经与农民的关系越来越遥远。当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联系越来越松散,甚至成为对农民而言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一级政府组织时,除了撤销,任何其它关于乡镇改革的方案设计似乎显得毫无意义了。
在这个意义上,乡镇公共财政体制的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它影响甚至决定着乡镇政府改革的成功与否。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集权传统的单一制国家,任何关于集权与分权的改革,在各级政府的层层操作中都容易陷入“一放则乱、一统则死”的怪圈之中。乡镇制度外财政的存在及其扩张,实际上就是乡镇政府自主性要求的一种异态反映。而财政体制的演变又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密切相连,它自身不可避免的带有政治、经济体制的时代特点和历史痕迹。因此,下一步的乡镇公共财政改革,应该财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双管齐下,在县乡政治体制上由“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转变,在财政体制上要消除县乡之间偏重的财政承包制度,在上层控制与地方自主之间寻求最佳均衡点,将乡镇财政建设成为一级自主规范的公共财政,使乡镇政府从消极的依附型“敲钟者”回归到积极的自主型“服务者”,真正担负起本社区内的公共产品生产和服务职能。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