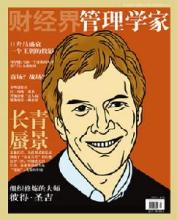主持人高希均教授:在学习型组织里,可以说真话,可以反省及深度汇谈,可以接受别人批评,可以改进自己,可以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不只是一个人的学习,而是团体的学习以及团体的实践。
圣吉常常强调:1990年代以来,最成功的企业是“学习型组织”,因为企业惟一最持久的优势就是要有持久的能力,比对手学习得更快。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先生的参与对谈,更证明了“比对手学习得更快”是多么重要!但我不得不先做预警:学习没有快捷方式。一场演讲不可能提供所有的答案,但会激发你迈向学习型组织。只要起步,就有可能。
圣吉:我今天不谈太多基本的东西,而是要带大家一起来思考学习型组织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对我们个人、组织、社会,甚至全球所代表的意义。
系统设置了成长的瓶颈
我常想,我真的不了解世界怎么能有持续的工业成长,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我们怎么会有这种宗教式的信念,想要不断成长呢?成长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一般人指的是经济成长或是社会发展。政治人物在国家成长出现瓶颈时,会比较紧张。很多人想讨论这个问题,也是因为他们没有成长。对商人来说,则是因为没有看到利润。这些关于成长的概念似乎和现实有所区别。
我在洛杉矶长大,成长经验或许和许多中国人不同。我四岁半时,父母搬到洛杉矶,我们住在圣伯纳第诺山谷。我记得当时开几个小时的车,沿途看到的都是整片的柳橙树和柠檬树。但是12年后,这些都不见了,果园被暴增的人口所取代。过去那里是小孩子的天堂,到处都可以打棒球,但是现在,学校甚至会建议小孩子在某些时段不要离开家或者学校,因为外面的污染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知道,成长不只代表利润,不只代表GNP,事实上,实际的生活经验或许更重要。在1980年,我父母搬离洛杉矶,那时住宅区的房子每户都要加上铁窗。我记得有一次我家后院的墙被小偷用大铁锤整个打垮。你可以看到,一个从我小时候可以自由自在骑着脚踏车到处跑的地方,变成一个危险的场所,这样的改变是非常大的,这对我来说又是什么意义呢?
当然,没有人故意要把世界变成这个样子,没有人想把柳橙树和柠檬树砍掉,没有人想生活在铁窗后面,没有人预期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就像没有人想让全世界产生温室效应或是让全球贫富分配不均一样。事实上,根本找不到一个人会刻意去这么去做。所以,我们都存活在整个“系统”的现实当中,系统创造了这样的社会。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创造这种互相倚赖的模式与系统。比如说,从小受虐的孩童长大后很可能成为施暴的父母,这不是计算机系统,也不是管理系统,而是一种互相依赖的模式。文化就是一种互动的系统,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小孩和100年前的小孩仍有某些相似的地方。
通过学习缩短智能的差距
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每天相处就会创造出许多互相依赖的模式,这就是所谓的系统。这并非新观念,从人类有史以来就是如此。过去我们用文化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现在有了一种新文化,叫做“工业文化”;这也许是第一种全球文化,它深深地影响着人们思考和行为的模式,也用共同的观点统合了全世界的人。
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是在很多年以前,我认为我们生存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当中。对我来说,没有办法真正地了解和影响别人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世世代代形成了这样的文化,如果大家都能体认到这个问题,或许情况就不会那么严重了。
我曾经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一个会议,研究系统思考的学者共聚一堂。会上有人说,许多饥饿与贫穷的问题背后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过去100年内,“人类力量”成长的速度超出想象的范围,但是我们的“智能”却没有随着“人类力量”而成长,所以如果我们的科技能力和智能间的差距无法缩短,我们的未来就不值得期待。
因此,至少对我而言,这是我不断思考的问题,而我所创办的学习组织中心,所要处理的就是这些根本的核心问题。不管从个人、组织或是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大的组织当中,会有一些重要的团队是需要学习的,同样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也要不断学习。
特别是在过去25年当中,我有机会和很多跨国企业合作,一开始我并不认为我思考的问题和企业界相同,但是在一个现代社会中,企业是最有权力的。
过去我们认为企业界在社会中最重要的功能是创造财富,可是对我来说,创造财富不是企业成立的原因,而是企业发展的结果。我认为企业最重要的功能是创新,包括科技的创新。要改变学校和政府是很困难的,相形之下,企业却很容易创新,不断有新公司成立,有潜力开创新的商业模式。
几年前我有机会碰到一些企业界人士,他们在社会上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不只重视企业的获利,思考的也是非常深入而根本的问题。我还记得和当时摩托罗拉的执行长葛理芬(Christopher Galvin)吃午饭的时候,聊到小孩子的学习过程,他非常重视小孩子的教育,所以让我了解到企业界还是有些有远见的人,或许只占企业界的5%到10%,会去思考企业根本的核心问题。
就这样,我对企业界渐渐有了兴趣。遗憾的是,我无法找到很多对系统思考感兴趣的企业高管,但我要再次强调,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社会公民,也会关心社会议题。
什么是真正的成长?
六年前,我们举办了一场会议,参加者都是企业执行长,我们成立了组织学习集团,后来发展成为MIT(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组织学习中心,现在已有15年的经验。
我们和很多个人或组织合作,希望透过合作带动系统性的变革。当时我们特别重视永续发展的问题,开会讨论的议题包括产品所使用的材料以及全球温室效应等问题。
2001年6月,我们邀请许多跨国企业的高级主管到波士顿开会,讨论组织学习的问题。壳牌石油、英特尔、惠普、联合利华等公司都曾派人参加,那时联合利华还不是我们学会的会员。很快,我发现企业界有了一些根本的变化,我说的并不是全部企业,也许只有5%到10%,而且每个产业的改变情况也有所不同,像石油和自然资源这类型的产业受到的影响是最深的,它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工业生产活动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
我们所讨论的都是全球性的问题:如社会贫富差距,全球经济依存度等等。当时有一位来自英国石油公司的人提到,我们不应该只讨论数字落差的问题,还应该讨论社会落差。五分钟之后,一位壳牌石油公司的代表发言说,他们公司的经理人看到世界和社会现状时,都很害怕。与会人士在听到一个跨国公司的高级经理人使用“害怕”这个字眼时,都感到十分惊讶。惠普的代表接下来又说,也许我们迟早都要重新定义,什么叫“成长”。
经济成长使我们耗用了太多原料,产生过多废弃物,既然天然资源有限,这种情况势必无法继续下去。部分跨国企业确实看到了这样的问题,联合利华的策略目标之一,就是让他们的农业、渔业和消费产品永续发展,即使不赚钱也必须追求策略,因为重点不在赚不赚钱,而是要继续生存下去。如果有一天天然资源耗尽,联合利华就没有产品可卖。
我们必须看到整个系统的运作方式。例如前一阵子网络的泡沫化,对于美国和全球经济都有很大的影响,经济学家用泡沫这个字眼可以让我们了解问题出在哪里。生活在泡沫里的人,观念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投资是不切实际,而且迟早会有破灭的一天。那么,如果工业时代是个泡沫结果会如何呢?如果工业文化是个泡沫又会如何呢?
一切看起来如此合理,大家都知道同样的经济原理,说同样的语言,我们知道如何创造利润、管理现金流量,但是,这都是在泡沫中看到的情景。自然系统不会产生废弃物,但身为一个美国人,要维持理想的生活,每周就要用掉一吨原料,其中95%在使用过程中都会成为废弃物,例如二氧化碳,结果造成全球平均气温每年增加一度,这种情况还在持续恶化中,因为废气排放的速度,是二氧化碳分解速度的两倍。
这些都不是新闻,但面临这种情况,我们能做些什么?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掌握科技的能力不断增加,但同时又有强烈的无力感。事实上,这也正是我们学习所面临的问题,学习不只是有新的想法,还包括了行动,大家都有这样的义务和责任,去正视这些问题,我们都是地球的公民,如果我们不关心,还有谁来关心这些问题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