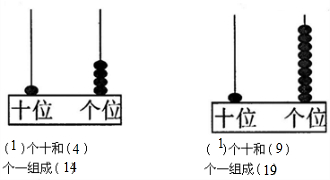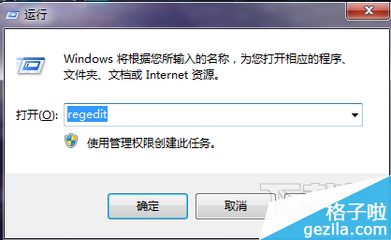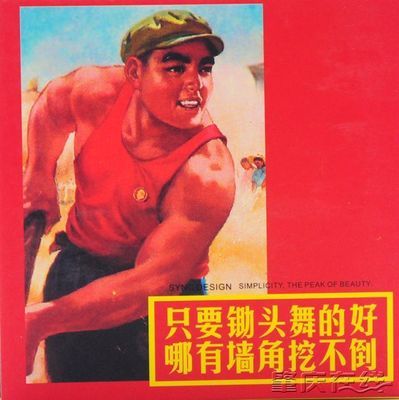中国学界有一种“去工业化”的思潮,这很不好。
即使是大名鼎鼎的凡尼尔·贝尔,也仅仅使用了“后工业社会”的说法,而不是“去工业化”。
贝尔把经济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农业,第二类是制造业或工业,第三类是服务业。按照这个标准,后工业社会第一个、也是最简单的特点,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等等。
今天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后工业社会”国家:它的服务业部门雇用的劳动力占就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可见,贝尔是以“职业分类”的标准,来划分当今社会的各种类型,而中国学者所谓的“去工业化”,则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概念:“毛估估”式的概念游戏,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那位提倡“去工业化”的学者这样说:“我们的答案是:“去工业化”。去工业化,不是说不要工业了,而是要抛弃仅仅倚赖工业制造获利的简单商业模式。中国制造业应该以工业为基础与平台,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依靠管理、技术、品牌、渠道、信息化等与工业水乳交合的共生优势,来实现中国企业从“市场发现型”向“市场创新型”的进化”。
可见,这位学者口中的“去工业化”,仅仅代表着“管理升级”的意思,而且这个“管理升级”,依旧是在工业企业体系内完成的,与“去工业化”丝毫没有联系。
事实上,假如这位学者的口号是“去农业化”,才是恰如其分的说法。
我猜想:毛泽东之所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是工业革命,是源自于他的亲身经历,那就是:他是生活在一个封建专制的时代,而他体会到的“专制”的恶劣和残酷,是来自于他的家庭和父亲,所以,推翻那个专制的家庭和父亲,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毛泽东在文章的正式表述,就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但实际上,“官僚体系”不仅不是那三座大山,相反的是,官僚体系是当今最有效率的管理体系,至少,在没有新的管理体系取代官僚管理体系之前,是这样的。关于这一点,韦伯早已说得非常清楚,不再累赘重复。
只能这样说:毛泽东是看准了问题,却抓错了药方,而那个“正确的药方”,就是:工业革命必将取代农业时代,而所谓的阶级压迫等等问题,都会在工业革命中迎刃而解,因为工业革命的前提,是私人产权、公平分配制度等等。
“文化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间的冲突,就在于整个社会的历史性演进,是生产力的演进、而不是文化的或精神上的演进,这也正应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
毛泽东至死也没能说清楚:(假如)“文化大革命”成功之后的那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我猜想: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人人公平、财富共巷”的社会,这其中,“公平”概念大于“财富”概念,可惜的是,它只能是幻想中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
因此,不是“去工业化”、而是应该一步加深对于工业化的理解,才中国企业的唯一正途。至少,在中国80%以上的农民成为工人之前,不要奢谈“去工业化”的话题。
怎样加深对于工业化的理解?工业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专业性”----专业本身是由于分工造成的,越专一、越会获得成功,显然的,它与中国人常常雾认为的宏大或多元化,是背道而驰的。
在“专业性”的方向下,质量和效率才会发挥威力。我们常常说,质量是生命、效率是金钱,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相同的产业或产品的前提下,质量才会是生命、效率才会是金钱,而这个所谓的“相同的产业”,其实就是“专业性”的同意词。

所以,中国制造业的管理升级,至少,包含了如下的三层的依次递进关系。
第一步,质量和效率。
在制造业的初期,确实是“质量是生命、效率是金钱”,它既是制造业的基础,也是制造业竞争的法宝,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中国的制造业,似乎整体上已经开始摆脱了这个制造业的原始阶段,也是告别了小作坊时代的“粗制烂造”的原始阶段,而淘汰那些“粗制烂造”的企业,恰恰是“质量和效率”。
第二步,品牌和核心技术
仅仅较好的质量和效率,并不足以在市场上取胜,这时,中国的制造业才发现了一个秘密:品牌要大于质量。本来,“品牌”本身并不是什么秘密武器,只不过,处在初期的中国制造业对它却十分陌生,甚至当初连一个独立的商标都没有,更不要说“商标”是如何转化为“品牌”的了,可见中国的制造业是在模仿和学习中慢慢成长起来的。
第三步,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
这也是当下中国最流行的词语。假如没有前面的前两步,要想实现这个第三步,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制造”和“创造”的不同,是本质的,因为前者还处于“生产”环境下,而后者则处于“知识”的环境下,显然的,它们是分属于不同时代的管理体系,而不同的时代则需要匹配不同的管理体系。
更麻烦的是,由于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处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知识时代的这样一个混杂时代,所以,要想分清它们之间的区别,显得难上加难,正所谓“鱼目混珠”。我这里只是就“去工业化”这个话题感慨一下,所以,无法就三个不同时代的管理体系,做明确的论述和区分,只能是另外再论述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