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就我们现在所建立的所有理论,无论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绝大部分是建立在笛卡尔式唯理主义基础之上的“无机社会理论”或者是“无机自然理论”。自然科学尽管研究过一些“有机物”或者是有机现象,但是,由于基本上是如对待“无机自然”一样地,对待这些“有机自然”现象的研究,所进行的也是肢解式的、零敲碎打的“分析”研究,所以只能算是“无机自然理论”。——当然,这种肢解式的、“分解主义”的研究,对于人类深刻认识有机自然现象,是必不可少的,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为“有机自然理论”的提出与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准备。没有“无机自然理论”对“有机自然”的“分解”研究,“有机自然理论”恐怕永远只能停留在“理论”上,达不到令人信服的和可接受的深度。然而,也不能不看到,因为“无机自然理论”恐怕只能用来处理如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所说的“细节性复杂”,而不能有效地用以对治“动态性复杂”,似乎只能称之为“科技”,尚不能戴上“科学”桂冠。——在我们看来,只有“有机自然理论”(包括“有机社会理论”)进入实验和实践,才能真正算得上是“科学”。
至于社会科学,如西方的社会学,尽管在“理论预设上是在个人主义的对立面上建立起来的”,就是在最早提出建立社会物理学的圣西门主义者那里,也已经把社会假定为一个有机实体,而且是一个“超有机体”;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方向有着持久影响的马克斯?韦伯,也完全懂得:“所谓‘有机’社会学的方法,就是试图从‘整体’出发来解释社会的共同行为,然后在共同行动里,对单个的人和他的举止作出阐释,类似于生理学对待身体‘器官’在整个机体的‘家庭’里的位置”。然而,尽管如纳什所说,在西方也的确是有一种“微弱但绵延不绝”的观念,即“组成这个世界的所有存在物,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但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这种观念毕竟只是一种“微弱”的声音。总体上说,由于西方二元对立的文化传统,个人与社会、精神与肉体、部分与整体等的关系上始终是得不到调和的,个人主义、唯理主义、分解主义始终是主流,始终唱着主角。如韦伯便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来谈论“有机社会学”的,甚至在临终前还坚持:“社会学理论本身的产生只能根据一个或更多的独立个人的行动,因此必须严格采用个人主义的方法”;强调“实证精神”的孔德,虽然认为实证的就永远是社会的,但也认为个体心理对社会现象有着重要作用;而斯宾塞“一方面把社会当作一个有机的实体来研究,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回到社会是由个体相加组成的原子论上面去”。即便是“反唯理主义”的,从孟德维尔、孟德斯鸠、大卫?休谟、塔克、亚当?福格森和亚当?斯密等直到卡尔?门格尔,以及我们在前文反复提到的,今天的冯?哈耶克,虽然在“有机社会理论”上有所觉察,但他们的思路是不清晰的,且所涉也不深。——至多就是象哈耶克那样,指出了“自生自发的秩序”的存在。所以,他们所建构的始终只能是“无机社会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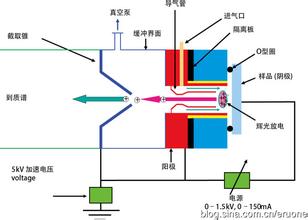
当代西方的主流文化,正是一种建立在无机社会理论基础上的“分解主义”的文化。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退休教授贝克特(JohnBecket)提出要“检视思维”,就是直接针对西方“分解主义”的,也正体现了西方文化对于“有机社会理论”的一种期盼。他强调,要区分“整体过程思考与事件式的片断思考两者之间的差异”,主张要“以整体性系统思考的哲理,替代今日几乎风行所有领域的分解主义——将复杂问题以简约的方式不断切割、愈分愈细的当代主流的西方文化”。曾仁强、刘君政教授在其合著的《管理思维》一书中也指出,“现代知识愈分愈专精,到了支离破碎的地步”。在西方社会,由于没有对“无机社会理论”和“有机社会理论”进行思路清晰的界分,导致了在理论构建时不能“自觉”,不能准确地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甚至如费夫尔所说的会搞错对象,在错误的场合错误地运用自己所建构的理论;或者是如哈耶克所说的,法律实证义者竟然“否定它拥有一个研究对象”,进而还导致了理论界长期的“争吵”、争执不休。在我们看来,现在则应该是到了“自觉”地去建构“有机理论”,包括“有机自然理论”与“有机社会理论”的时候了,并进而来突破“无机自然理论”在分析、解构“有机自然”问题时碰到的困难,来解救“无机社会理论”在研究“有机社会”时遭遇的窘境。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