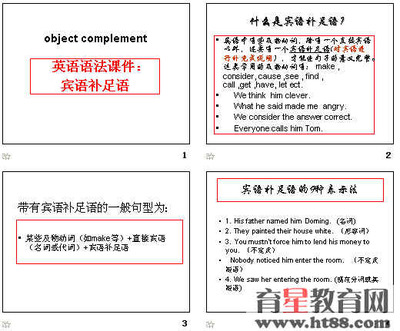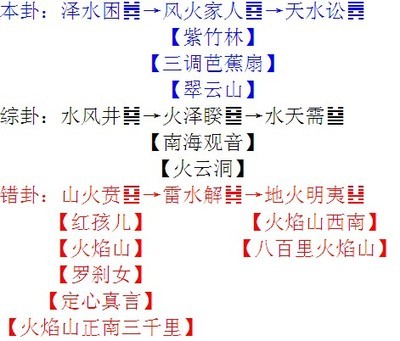在哈耶克以及一般文化论者看来,“文化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为的,既不是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也不是经由理性设计出来的。”文化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是“自生自发”地进化的。万般淫巧的人脑,在文化面前,只能是“一个能够使我们吸收文化而不是设计文化的器官”。因而,人们是无法对自己的文化着手设计或者是管理的,对于文化进行质量管理当然更是无从谈起。文化是一匹不可驯服的野马,似乎只能任其处于一种“失控”状态。
不仅如此,人们还被文化所控制而常常不能自知。“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learntrulesofconduct)构成的传统,因此,这些规则绝不是‘发明出来的’,而且它们的作用也往往是那些作为行为者的个人所不理解的。”由于我们根本不可能获得,对于我们“作为行为者个人所不理解的”行为的充分知识,所以,我们所能做的是,“像园丁培植其植物那样,经由提供适宜的环境去促成社会的发展,而决不能像手工艺人打造手工艺品那样刻意地塑造其产品。”由此看来,我们事实上遇到了一件棘手的工作,一个“烫手的山芋”。要对包括文化在内的“自生自发”的秩序展开有效的质量管理,看来还不能不去呼吸一些新鲜空气,换一换思路,看看有没有更有力的理由、基据与方法。

哈耶克在《自生自发秩序与第三范畴》中,详细地阐述了渊源于古希腊先哲们提出的,“自然”与“人为”这种二分观的错误与误导性,认为这种认识进路不能把独特且大量的现象(如文化、经济制度、萨维尼的“自然法”等自生自发的秩序)纳入其中。于是,他进一步认为,“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的“自生自发秩序”,应该作为新的且极为重要的“第三范畴”,据此提出了渊源于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的“三分法”。在哈耶克看来,“第三范畴”的研究是社会理论研究的核心对象。
然而,尽管哈耶克找出了“第三范畴”,并有点苦口婆心地祈请社会科学家们去重视对这个“核心对象”的研究,但是,一方面是因为他所说的这种“三分法”以及“自生自发秩序”的存在,一直是有争议的。翟学伟在《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一书中指出:“即使在哈耶克(F.A.Hayek)看来,社会理论探讨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中那些自生自发的秩序,但我认为如果一种社会理论的建立一旦被社会成员接受,就会导致社会的再建构。……任何看似客观的社会构成在其历史长河中都已经被多次地建构过了,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文明社会都是被某种理论或观点再建构的结果。”翟学伟说的当然也是事实。然而,在我们看来,他在有一点上是没有界定清楚的:即当一种社会理论或观点的提出和被社会大众接受的初始,这种理论或者是观点往往只是表现为“显在制度”(即“显规则”),只有当其真正被大众全面、深入地“接受”后,才可望沉淀成为一种“潜在制度”(即“潜规则”),并成为一种潜意识的行动准则;此时,社会在被该理论或观点“再建构”的过程中,就会演生出“自生自发的秩序”,并沉积为一种“文化”。所以我们把文化定义为“显规则与潜规则互动的和”(关于这一点,请详见上卷:第一章“文化是什么”),道理正在这里。或许也正因为此,翟学伟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当然在这种再建构的过程中又会有一些自生自发的秩序出现,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理论也不停地被变更的原因。”也即是说,哈耶克所说的“自生自发的秩序”始终是存在的;而且,如“文化”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则全然便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并在“自生自发”的进程中,担负起了推动社会理论“不停地被变更”的重任。
 爱华网
爱华网